

如【公司法修订草案下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制度商榷(上篇)】所述,在有限责任公司日常治理中,“人合性”已经不仅是股东们极为看重的关键因素,更俨然已经成为了“强势股东借以合纵连横、杀伐决断的利器,抑或是蜕变为股东彼此间相互制衡的手段”。从表现形式上看,即为股东们通过公司章程的约定对于部分股东进行不同形式的处罚。在当下的公司治理实务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处罚主要分为股东财产性权利限制、股东罚款、股东除名三种手段,且其严厉程度依次增加。
限制、暂缓、乃至剥夺股东的公司盈利分配权,以及股东罚款,相对股东除名这一釜底抽薪式的处罚对于股东的权利侵害程度较轻,且司法实践中也已有较为明确的规制倾向。然而,对于股东除名,却始终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本次《公司法》修订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并没有如刘胜军老师、刘凯湘老师等学者建议的一般增设有关规定,股东除名制度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着种种繁杂而困难的实务问题。在该等情况下,本文下篇尝试从司法实践分析和比较法借鉴的角度,为公司的股东除名制度构建和实际操作提供实务参考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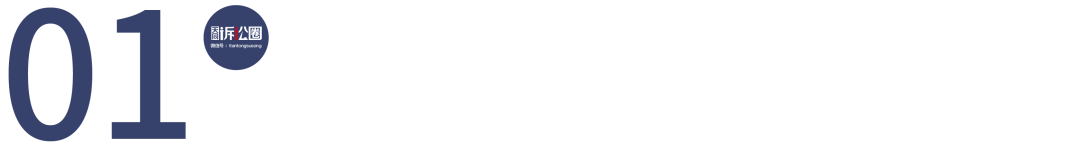
股东除名规则应于公司章程中明确约定
虽然缺乏具体规范,但根据《公司法》第20条关于股东须遵守章程规定且禁止股东滥用权利的规定,第11条关于章程效力的规定,以及法定事由之外公司章程保有意定空间的原理,司法实践对于股东除名事由的约定形成了两个基本共识:非经章程授权,股东会无权除名任一股东。
在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鹃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股东会可以对股东施加处罚,但是必须事先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明确的处罚标准和幅度,否则股东会作出的处罚决议无效,连股东罚款这一权益伤害较轻的处罚手段都必须经章程明确规定,也充分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于无章程依据的股东除名予以无效认定的统一思路。[1]
因此,公司在实务中若要保留股东除名的空间,必须在章程中明确约定,而不可通过临时股东会等程序直接依据决议除名股东,跳过章程约定的决议无效。
章程约定整体可分为两种情况,即公司设立时的原始章程即已进行约定,和公司通过章程修订程序新增股东除名条款,分述如下。
1. 建议公司设立时即在章程设定股东除名条款
公司章程约定股东除名条款之所以有效,正是基于公司法强制规定之下留给公司的意定空间,因此,个案中具体条款是否有效,首先即须审查其是否可以体现公司股东的合意。而公司设立时的章程须所有股东一致同意,因此该等原始章程设定的股东除名条款有效。
例如,在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第96 号“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的规定,有限公司章程系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产生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宋文军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前述规定的认可和同意,该章程对大华公司及宋文军均产生约束力”,在说理部分特别强调了案涉《章程》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并据此认定有关条款有效。[2]
诚然,公司可能出现在设立之后通过增资扩股、股权转让等方式加入公司的新股东,但是该等股东加入公司本就须修改章程并由新股东签字确认,因此也不存在合意认定上的障碍。
2. 章程修订案中的股东除名条款,若未经拟除名股东同意,须经股东会决议除名后,面对股东会决议无效之诉,通过实质理由争取支持
就章程修订案中的除名条款而言,若本身章程约定修订必须经过全体股东同意,或并非除名事由出现后的临时“补订”,可以获得拟除名股东的同意,则其效力也不存在合意障碍。
但由于实务中,公司往往并没有提前约定除名条款的意识,当除名事由事实上已经出现,股东关系已经破裂,公司才试图通过章程修订案的形式进行约定,则通常难以获得被除名股东的支持,并且带有明显的针对性。该种情形下,修订案效力就可能具有极大争议。
在有关的诉讼中,公司可以争取的答辩理由可以围绕以下两点展开:
(1)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系基于章程的自治约定,只要章程经约定程序修订,并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要求,即至少绝对多数决,则符合自治要求,效力不存在瑕疵;
(2)就股东除名的目的而言,若公司须保障章程修订案的通过若该等章程修正案无被除名股东同意即无效,则其将完全丧失其存在的意义,也根本无法达成动态调节公司治理情况,处罚伤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的异议股东,解决公司僵局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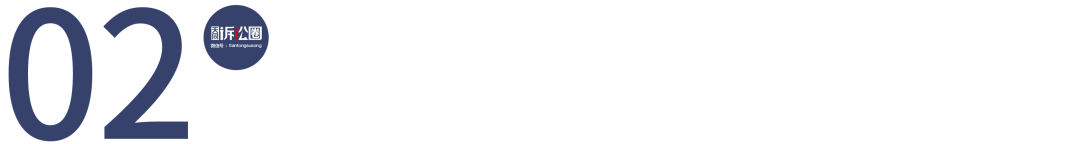
可以约定的除名事由
就公司可以约定的具体除名事由,参考国内的司法实践和比较法情况,典型的事由有:(1)财产关系不规范以及资金往来的不正常;(2)拒绝履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义务,如协作义务、竞业禁止义务、忠实义务;(3)不正当地执行公司业务或越权干预业务执行;(4)严重地违反法律义务的行为,如违反、购股时对公司的欺诈行为、犯罪行为;(5)损害公司经营和妨害竞争的行为;(6)股权激励型股权的“人走股留”。[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公司不可就股东除名事由恣意约定,伤害股东权益。例如,(2021)京02民终11195号案中,四十人论坛以张家林存在基于股东身份损害公司利益和声誉的行为为由决议解除其股东资格,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认为双方就《张家林欠款议案》所涉相关债权债务已经通过仲裁解决,所以四十人论坛不得再以相同理由除名张家林,并明确:“虽然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公司就股东除名事项和事由进行约定,但相关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定,不得侵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否则该约定无效。”
此外,在上述事由中,前五项均系针对拟除名股东行为失范、股东关系破裂的情况,第六项较为特殊,属于股职绑定的情形,需要再作特别说明如下。
(一)“人走股留”条款有效
股权激励型股东除名,在实践中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将股权与员工身份挂钩,在公司章程里规定“人走股留”条款,即一旦股东离职(无论主动或被动),就将被除名,公司股东会决议强制收回其股权。
该等条款已经由司法实践明确认定为有效。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96号指导性案例“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大华餐饮有限公司系由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其初始《章程》第14条明确规定:“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购……”。针对该“人走股留”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大华公司章程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作为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继而作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亦系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由此可见,第96号指导性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股权激励型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
事实上,第96号指导案例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2015)民申字第2819号案中认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与股东约定《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之外的其他股权回购情形。约定公司回购的内容在不违背《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强行性规范的情形下,应属有效。”[4]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确实明确、稳定地认定该等除名理由是合法有效的。
(二)警惕“人走股留”条款可能导致的资本维持困境
由于约定了“人走股留”,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时,就可能出现离职员工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使公司处境雪上加霜的情况,也会导致公司陷入资本维持困境。“人走股留”纠纷裁判规则的本意系为公司强制收回离职员工股权扫除合法性障碍,然而,实务中却大量出现反过来,离职员工主动请求公司回购其股权,公司则以违反资本维持原则为由拒绝予以回购的情况。吴飞飞研究了88起该等情形的案例,发现:“尽管被告公司几乎均以违反资本维持原则作为抗辩理由,却有大量案例支持了离职员工的股权回购请求”。[5]例如,(2018)粤01民终19159号案中,法院认为:“公司既已通过公司章程确立了‘人走股留’的职工持股制度,则应当预见到职工离职退股可能影响公司资产缩减的不利后果。在公司章程确立的该项原则未变更的情况下,公司自应履行其回购义务并对符合退股条件的离职股东给予合理补偿。”事实上,离职员工诉诸人民法院时,裁判者基于法律的平等适用原则以及弱者权利倾斜性保护的裁判思维,一般会判令公司承担回购义务。在公司缺乏回购资金且陷入运营困境时,回购离职员工的股权,不仅会引发员工与公司、股东间的权利冲突,甚至还会引发员工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因此,公司在设置该等“人走股留”条款的时候,须警惕该等“反向操作”可能给公司带来的资本维持困境,在条款表述中进行设计,如约定“人走股留”的前置程序条件、特殊情况下的公司延迟回购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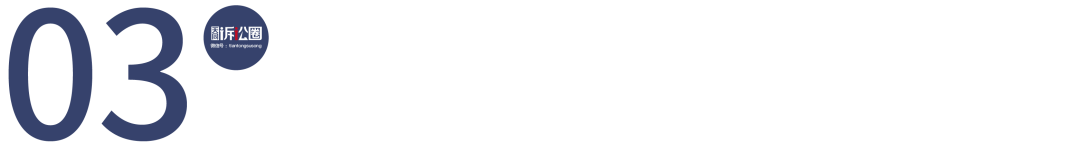
股东除名决议程序,拟除名股东没有表决权,但应保障其列席参加、自我辩护的权利
就股东除名的具体程序而言,股东会需在具体场景下作出股东除名决议。
法院的倾向性观点认为,拟除名股东没有投票权,因为若股东除名决议中,拟除名股东仍有投票权,则该等处罚的目的可能无法达成,故应当排除该等股东的投票权。例如,在(2019)藏01民终621号案中,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除名决议上被除名股东的表决权应被排除,但在章程并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被除名股东不需回避,其有权参与除名会议并在会议上进行申辩。[6](2018)苏01民终397号案中,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持类似观点。[7]在(2020)内04民终4756号案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仅排除被除名股东表决权后,经剩余股东同意并通过的决议视为代表100%表决权通过,该决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关于该等决议必须全体通过的规定。[8]
虽然拟除名股东没有表决权,但公司须保障其列席参加、自我辩护的权利,否则程序亦有瑕疵。比如,(2019)藏01民终621号、(2018)苏01民终397号等案中,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认定:在章程并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被除名股东不需回避,其有权参与除名会议并在会议上进行申辩。
该等实质认定在比较法上也有参照,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7条第4款规定,在强制性股权回购的情况下,所涉及的股东没有表决权;但是,其应当有机会发表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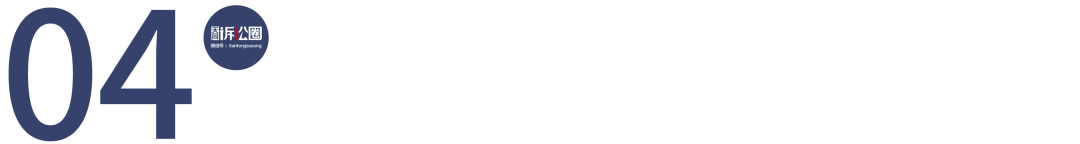
股东除名后,若其不配合工商登记,公司可通过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决议有效,或在被工商行政机关拒绝后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方式争取支持
如上篇所述,在股东除名这一级特殊场景下,在缺乏有关法律规范的当下,很多时候反而是公司需要救济且救济无方。
1. 司法裁判的倾向性观点认为公司不是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的适格原告,但可以考虑通过在诉讼请求中增加要求被除名股东配合的义务性请求,争取法院受理
实务中,大量公司选择起诉确认决议效力,但是司法裁判的主流观点认为该等诉讼中公司不具有诉的利益,一般直接作驳回起诉处理。
例如,(2019)最高法民再335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涉及公司决议效力的案件只有公司才是适格被告,而本案中建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其诉讼地位亦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建材公司不具有提起该诉的主体资格,建材公司提起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也不属人民法院审理范围”,且建材公司的股东并未提起相应诉讼,应视为案涉决议不存在争议,也就不具有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9](2021)渝04民终1441号案中,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也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公司提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无诉之利益,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对其起诉应予驳回。”[10]
不过实践中也存在支持公司以该等案由起诉的情况,如在(2022)闽08民终1019号案中,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认为,法律、司法解释等并不禁止公司或公司其它股东起诉股东,确认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及确认股东资格被解除,对此类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11](2019)苏02民终1020号案中,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受理了无锡锡晟建设有限公司起诉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并最终判决:“确认锡晟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一)》有效;朱晓夏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内协助锡晟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由此可见,对于公司是否有权提起决议效力确认之诉或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为严重,公司须积极证明自身具有诉的利益。而为了达致该目的,公司在起诉时的诉讼请求可作特别设计,不仅请求确认公司决议效力,还可增加请求被除名股东配合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等义务性请求,以争取法院受理。
2. 工商行政部门拒绝后的行政救济途径
在相关主管机关不予办理变更时,可以考虑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而在行政救济中,须特别注意诉讼请求的设计,请求撤销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等有关文件,不可直接请求工商行政部门配合变更登记。
例如,(2020)粤0606行初33号案中,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就认为:“原告申请的变更登记并不属于股东向其他股东转让全部股权,不涉及股权转让的问题,只是对未实际出资认缴股东的一种解除股东资格的除名,因此,《〈企业登记申请文书规范〉〈企业登记提交材料规范〉的通知》关于变更股东的要求与股东除名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并最终支持了原告撤销《不予受理通知书》的诉讼请求。但该案中,法院也驳回了原告请求工商行政部门配合进行公司变更备案登记的诉讼请求,因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司法行为,不能直接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
综上所述,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股东除名制度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着种种繁杂而困难的实务问题。在该等情况下,公司应尽早计划,在章程中明确股东除名的有关条款,明晰除名事由、除名程序、股权变更程序等事项,并注意除名事由的约定可能造成的具体后果,审慎评估再做决定。若最终在股东除名过程中,出现争议,则须参考相应实操建议,及时处理,争取法院支持。
注释:
[1] 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鹃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0期。
[2]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6号: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3] 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6版)》,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646 页;参见王保树主编:《最新日本公司法》,于敏、杨东译,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第70 页,第36条。
[4]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6号: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5] 吴飞飞:论“人走股留”纠纷裁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改进,《现代法学》2023年第1期,132页。
[6] 甘肃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西藏杰康酵母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1民终621号。
[7] 韩建民、张秀铭与曾奇夫、南京北交轨道交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397号。
[8] 罗海峰与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04民终4756号。
[9] 王华宣与付红雨等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35号
[10] 秀山县振鑫富锰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杨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4民终1441号。
[11] 福建启盛实验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吴保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08民终1019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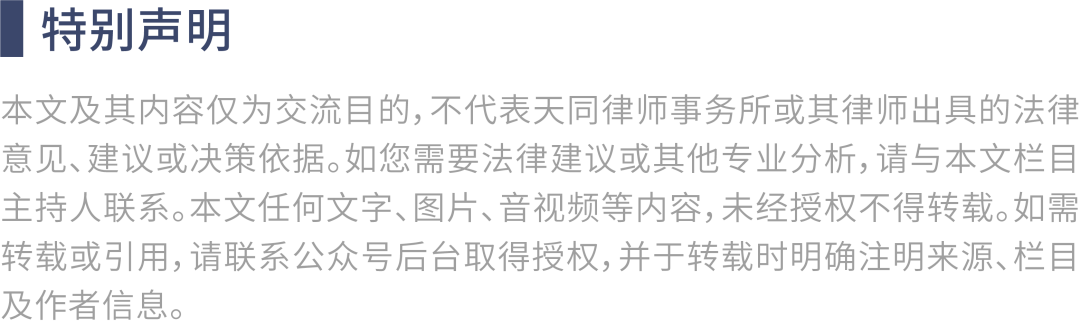
“公司法实务”栏目由庄喆律师主持,奋斗在公司法实务一线的天同律师们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公司法实务的相关思考。如您对“公司法实务”栏目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