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王宸宇,天同律师事务所深圳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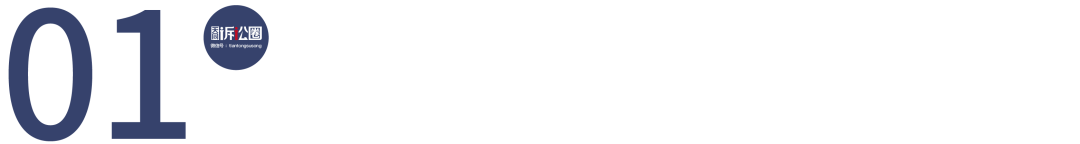
引言
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是现代商业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前瞻企业大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在册有限责任公司超4813万家。[1]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德国立法者最早在综合股份公司、人合公司各自优势的基础上经由“艺术创造”而来的公司形态,是经过改良、融入了人合性特征的资合性公司。[2]可以说,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股份公司的核心差别之一就在于其人合性。公司法中的诸多制度正体现了立法者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殊考量,如股东资格确认规则、股东人数限制规则、股权外部转让受限规则、重大事项共同决策规则等。更重要的是,公司法的诸多条款作为“示范文本”,在法定的“示范内容”之外进一步允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协议等形式在法定基础上对诸多事项进行约定,正是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基于维护人合性的个性化需求的尊重。
然而,在有限责任公司日常治理中,“人合性”已经不仅是股东们极为看重的关键因素,更俨然已经成为了“强势股东借以合纵连横、杀伐决断的利器,抑或是蜕变为股东彼此间相互制衡的手段”。[3]在当下的公司治理实务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处罚主要分为股东财产性权利限制、股东罚款、股东除名三种手段。限制、暂缓、乃至剥夺股东的公司盈利分配权,以及股东罚款,对于股东的权利侵害程度较轻,且司法实践中已有较为明确的规制倾向,因此本文将主要聚焦在股东除名这一釜底抽薪式的处罚有关问题讨论上。[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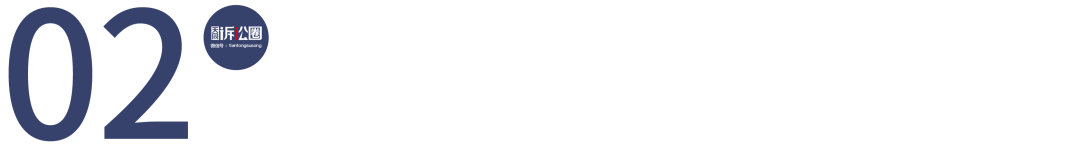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实务现状
股东除名是指出现特定事由时,公司按照特定程序剥夺部分股东的股东资格,并强制回购其所持股权。在实务中,公司对股东除名并不会征求被除名股东的意见,公司可以直接作出决定。
公司治理实务中,根据股东除名的原因及样态,股东除名也存在不同类型,有学者认为可根据股东除名的样态分为股权激励型、资本管制型、“清除异己”型三类基本模式;[5]有学者认为股东除名的原因可分为未履行出资义务、抽逃出资、实施不正当行为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等;[6]也有学者认为股东除名的现实情况错综复杂,在缺乏明确法律规制的情况下难以清晰分类。[7]本文部分赞同最后一种观点,且认为所谓资本管制型除名或任何与出资义务相关的除名都是以“除名”之名,行“失权”之实(于本文第三部分第(一)小节详述),但为便于实务参考,仍尝试抽丝剥茧,提炼两大最核心的股东除名类型,即股权激励型和异议剔除型。
(一)股权激励型
股权激励型股东除名,在实践中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将股权与员工身份挂钩,在公司章程里规定“人走股留”条款,即一旦股东离职(无论主动或被动),就将被除名,公司股东会决议强制收回其股权。
对于大量的中小型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资、治是不分家的。对于大型上市企业而言,股东主要履行出资义务,而公司治理依仗专业的管理团队。然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东往往就是公司的直接管理者或者管理层的选拔、指派者,且公司往往十分依赖股东们的“亲力亲为”,尤其是对于近几年大批量涌现的创新创业型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相对于静态的股东出资,公司对人力资本的依赖性反而更强,股东不仅仅要履行出资义务,更重要的是还要为公司治理决策贡献力量。因此,该等人力资本依赖程度较高的公司,多采用动态性的股权结构,施行股权激励政策,而股东除名通常被视作是满足其股权激励需求的最后规制手段。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96号指导性案例“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大华餐饮有限公司初始《章程》第14条明确规定:“持股人若辞职、调离或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走股留,所持股份由企业收购……”。针对该“人走股留”条款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大华公司章程将是否与公司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作为取得股东身份的依据继而作出‘人走股留’的规定,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封闭性和人合性的特点,亦系公司自治原则的体现,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8]由此可见,第96号指导性案例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股权激励型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也被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
(二)异议剔除型
如前文所述,在所有的股东处罚措施中,“除名罚”被认为是最后的终极手段,非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而正由于除名具有最后的强威慑功能,其一般被当作清除公司内部异己分子、维系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最终手段。
异议剔除型的股东除名,在程序上的典型体现是公司有关除名程序及事由的约定往往是在有关事项发生后,公司希望除名特定股东时,通过章程修订案等形式,“亡羊补牢”。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司成立之初的和睦氛围使得众股东未想到或不愿意进行该等预见性的约定,另一方面是由于该等约定可能在公司设立之初难以由全体股东一致通过。因而,往往是在公司治理经营期间,因股东之间积怨已久,由大股东将该等除名条款通过三分之二多数决的章程修订模式,补充约定。
可以说,该等股东除名作为公司或大股东针对异议股东的“武器”,方便趁手又无坚不摧,因此也频繁见诸于公司治理实务中,但是也恰恰是由于其该等属性,导致了相当多的权利滥用,也引发了相当大的司法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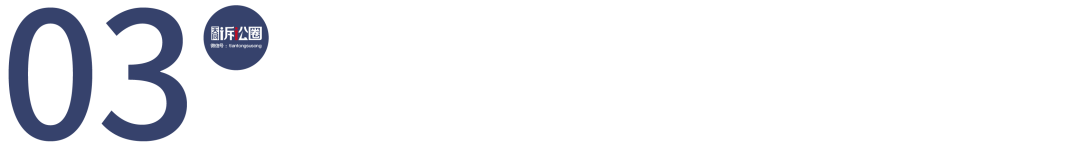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的司法困局
由于股东除名在实务中样态复杂,对被除名股东的权益伤害极大,加之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股东除名并无明确规制,甚至没有指引性条款,因此在司法实务中,造成了极多争议。股东除名的概念与实质、股东除名决议程序、公司及被除名股东的司法救济、股东除名决议的司法审查四个维度,是股东除名面临的司法困局。
(一)股东除名的概念与实质,股东失权与股东除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有学者提出第17条属于公司法上的“失权条款”而非“除名条款”。[9]但亦有学者认为“失权”与“除名”并无显著差别。[10]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实务界,无论是立法者、法院,还是广大法律共同体的从业人员们,在各大公众号文章、实务处理、案例说理中,均将该条认定为“股东除名的法定情形”。
诚然,概念之分不是为了无意义地抬高法律本身的门槛,而应当先实质,后概念,以概念区隔为实质分野服务。本文认为,股东失权与股东除名之间,有着极大的实质差异,不宜混为一谈,且本次公司法修订稿中对于股东失权的强化,不可被认定为对股东除名的规制,否则将掩盖实质问题,带来更大的麻烦。
股东失权与股东除名的根本差异有二:
1. 股东失权针对的是公司的资合性问题,而股东除名针对的是公司的人合性问题,这就决定了股东失权实质上并没有什么争议,而股东除名相关的争议颇多。由于股东权利的获取本身即以出资为基本前提条件,因此只要股东未如期按约完成其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即意味着其无法获得相应的股东权利,自然就“失权”了,并不具有惩罚属性。而股东除名则不同,其针对的是已经完成了自身出资义务的股东,由于特殊原因将其除名,具有惩罚属性。
2. 股东失权允许部分失权,而股东除名是对股东资格的完整剥夺,不存在部分除名的可能。例如,“黑龙江农垦完达山贸易有限公司与王斌力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中,公司股东会决议并非剥夺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黑龙江完达山公司的股东资格,而是解除黑龙江完达山公司未缴纳部分相对应的认缴资格,即按照实缴出资比例重新分配其所持股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明确:“股东享有权利的前提是承担股东义务,向公司缴纳出资是股东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股东应当向公司完全履行出资义务,该出资义务是股东取得股东权利的对价”,并最终认定,该决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侵犯股东固有权,体现了权利义务相对等原则,因此有效。[11]这种部分失权的处置,恰恰是股东失权与股东除名核心差异的体现,体现了权利结构的分离。
(二)股东除名决议程序的困局,从章程约定到决议作出
1. 约定股东除名事由的程序性要求
虽然缺乏具体规范,但根据《公司法》第20条关于股东须遵守章程规定且禁止股东滥用权利的规定,第11条关于章程效力的规定,以及法定事由之外公司章程保有意定空间的原理,司法实践对于股东除名事由的约定形成了两个基本共识:(1)非经章程授权,股东会无权除名任一股东;(2)公司设立时所有股东一致同意的章程设定的股东除名条款有效。
例如,在2018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第96 号“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依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的规定,有限公司章程系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并对公司及全体股东产生约束力的规则性文件,宋文军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的行为,应视为其对前述规定的认可和同意,该章程对大华公司及宋文军均产生约束力”,在说理部分特别强调了案涉《章程》系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通过,并据此认定有关条款有效。[12]而在2012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鹃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股东会可以对股东施加处罚,但是必须事先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明确的处罚标准和幅度,否则股东会作出的处罚决议无效,连股东罚款这一权益伤害较轻的处罚手段都必须经章程明确规定,也充分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于无章程依据的股东除名予以无效认定的统一思路。[13]
但是章程修订案中的除名条款,由于通常难以获得被除名股东的支持,并且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在实践中具有极大争议,而争议的核心焦点即为该等多数决的章程修正案是否必须获得被除名股东的事先同意方对其有效。一方面,若该等章程修正案无被除名股东同意即无效,则其将完全丧失其存在的意义,也根本无法达成动态调节公司治理情况,处罚伤害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的异议股东,解决公司僵局的目的。但另一方面,若该等章程修正案无须被除名股东同意即有效,则其亦可能走向大股东恣意欺压小股东的另一极端。
因此,本文认为,目前的司法困局亟需有关法律规定予以明确,并赋予法院对条款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的权利,以挣脱形式审查两头堵的泥淖。
例如,德国法律规定,如果公司在章程中事后加入授权条款,必须征得全体股东的事前同意(Einwilligung),但是,为了避免股东除名因异议股东的反对而丧失存在意义,德国法律提供了司法救济路径,即如果出于某种事宜将特定股东排除出公司,但公司章程并未将此事由列为股权回购事由时,公司可以申请法院进行除名判决(Ausschlussurteil),此时法院即可介入,对该等具体事宜进行实质审查,以判断异议股东是否具有过错并实质伤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其他救济途径是否已经穷尽等,并最终判决是否将异议股东除名。[14]
2. 股东除名决议的程序性要求
即便股东除名的约定有效,股东会仍需在具体场景下作出股东除名决议,但是由于缺乏具体规范,我国司法实践在该等决议被除名股东是否具有投票权、决议所需赞成票比例等问题上,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屡见不鲜。
有部分法院认为,若股东除名决议中,被除名股东仍有投票权,则该等处罚的目的可能无法达成,故应当排除该等股东的投票权。例如,在(2019)藏01民终621号案中,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除名决议上被除名股东的表决权应被排除,但在章程并无特别约定的情况下,被除名股东不需回避,其有权参与除名会议并在会议上进行申辩。[15](2018)苏01民终397号案中,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持类似观点。[16]在(2020)内04民终4756号案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仅排除被除名股东表决权后,经剩余股东同意并通过的决议视为代表100%表决权通过,该决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关于该等决议必须全体通过的规定。[17]
但最高人民法院对该问题的表态可谓含糊不清。(2018)最高法民再328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由于表决权来源于出资、股东除名权系形成权且如果认为被除名的大股东仍然享有表决权的话,那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七条的规定将会被虚置,因而被除名股东的表决权应被排除。[18]表面上看,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了,被除名股东的表决权应被排除,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如前所述,该案情形实为股东“自动”失权之情形,基础逻辑应为涉案股东未出资,则其当然不享有投票权。最高人民法院强调了“表决权来源于出资”,那么履行了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就意味着其投票权在没有特别规定的前提下不应被剥夺呢?毕竟,若被除名股东的投票权被完全排除,可能导致少数股东将多数股东排除出公司。因此,法律规定需要对该等问题予以明确。例如,根据《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47条第4款之规定,在强制性股权回购的情况下,所涉及的股东没有表决权;但是,其应当有机会发表意见。
此外,关于该等决议的多数决方式应为资本多数决还是人头多数决,一般多数决还是绝对多数决等问题,由于缺乏明确规范,事实上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三)公司及被除名股东的司法救济、股东除名决议的司法审查
1. 除名后的公司救济,登记障碍与起诉无门
股东除名是公司及部分股东对特定股东的处罚,是对特定股东权益的剥夺,照理说只有权益被剥夺一方才需要救济,但是在股东除名这一级特殊场景下,在缺乏有关法律规范的当下,很多时候反而是公司需要救济且救济无方。
这是由于即便股东会除名决议成立及生效,但根据商事外观主义原则,如公司对股东进行除名后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则公司无法履行减资手续,更无法吸纳新的股东或变更原股东之间的持股比例,给公司治理和经营带来极大的麻烦。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股东除名涉及的股东权益太过重大,且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实践中,在被除名股东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工商登记部门往往不会配合公司仅依据一纸决议便变更工商登记,而被除名股东又往往是不愿意配合的。
更可怕的是,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之下,公司没有明确的请求法院确认决议有效的权利。《公司法》第22 条规定了公司决议内容违法无效、程序违法可撤销的决议效力之诉的二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增加了公司决议不成立规则和决议瑕疵裁量驳回规则,但在生效稿中删除了原草案中关于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的规定。因此,目前我国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仍旧处于法律的空白地带,这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同案不同判。
例如,(2019)最高法民再335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涉及公司决议效力的案件只有公司才是适格被告,而本案中建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其诉讼地位亦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故建材公司不具有提起该诉的主体资格,建材公司提起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之诉也不属人民法院审理范围”,且建材公司的股东并未提起相应诉讼,应视为案涉决议不存在争议,也就不具有通过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19](2021)渝04民终1441号案中,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也认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公司提起股东资格消极确认之诉无诉之利益,其诉讼主体不适格,对其起诉应予驳回。”[20]
但是相反的,在(2022)闽08民终1019号案中,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认为,法律、司法解释等并不禁止公司或公司其它股东起诉股东,确认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及确认股东资格被解除,对此类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1]
由此可见,对于公司是否有权提起决议效力确认之诉或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较为严重,且在公司起诉因缺乏主体资格而被驳回,工商机关又不为其变更登记时,也容易陷入救济无门的窘境。实践中,很大一部分被除名股东的做法是对除名决议置之不理,继续要求行使各项股东权利,导致公司不仅无法将其除名,还要被其反复纠缠,不胜其烦。
2.被除名股东的救济困境,强制回购的定价迷局与股东身份的确认难题
股东除名并非决议作出后就一除了之,对于被除名股东的股权还需要进行妥善处置,其股东身份的丧失时点也可能带来救济困境。
首先,就股权定价问题而言,实务中,出现股东除名即意味着公司经营治理已经出现了较大问题,股东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极为紧张,此时若要求双方对股权回购的定价有商有量,达成一致恐怕也是奢望。因此,在缺乏明确法律规范的情况下,被除名股东的股权作价就成为了一大难题。参考德国法的规定,根据《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的规定,退出的股东针对公司享有以股权的足额交易值为标的的补偿请求权;该请求权随着股权的回购而即期。但是,如其他任何补偿规则一样,公司章程也可以规定一个较低的补偿额,如按照账面价值或者股权的名义值来确定,也可以对不同的股权回购情形进行区分,但是必须维护股东平等原则,即更低回购价格或者区别对待必须具有充分的实质理由。此外,章程也可以约定补偿额度由一个仲裁鉴定人来确定。
其次,股东除名决议作出后,被除名股东的身份也是具有争议的。按理说,一旦被除名,该股东即丧失了股东身份,但是一切针对股东会决议的救济都必须具有股东身份才可以提出,这就意味着,不仅如前文所述,公司无权作为原告提起决议效力确认之诉,被除名股东事实上也没有权利提起该等诉讼。[22]这一问题在国际上也普遍存在,例如,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一份判决中(BGHZ 192,236)涉及一家由原告和另一个股东R组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本案被告)。该公司股东会在2001年作出有效决议,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基于重大事由回购原告的股权。而原告直至2007年一直没有收到根据章程之规定应当于两年之内支付的补偿金。本案上诉法院认为,在无需考虑股权回购决议的情况下,由于股权回购补偿金尚未支付,原告依然是享有投票权的股东,从而也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相反,联邦最高法院则驳回原告的起诉,其理由是:对原告股权的回购已经通过股东决议公告的形式公布,从而对原告产生效力,导致其股东资格的丧失。
由此可见,对被除名股东而言,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其股权作价的实体权益和寻求救济的程序权益都岌岌可危,而这其实是源于除名决议的效力停留在成立即生效的一般决议效力层面,未经实质审视和规范。
(四)股东除名决议的形式审查,“人走股留”成恣意打压的避风港
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股东除名决议的司法审查,几乎全部停留在表面审查,即仅审查股东会决议的程序是否违法,这实质上是源于法律没有明确授权法院对该等决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因此法院出于尊重商业判断和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惯性,便也拒绝进行实质审查,认为只要章程有所约定,股东已经同意,有关决议便是有效的。例如,(2020)豫民申6236号案中,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如公司章程中约定的股东除名情形严格于《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但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则对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公司依据该章程约定,依法召开股东会并产生的决议有效。[23]无独有偶,(2020)湘11民终3050号案中,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认为,《公司法》未规定股东除名制度,但该法及其相关法律也并未禁止公司不能对股东除名事由另行规定,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公司即可以自治设立股东除名的事项和事由。[24]
但面对实践中确实存在的大股东恣意打压、处罚小股东的现象,也有法院选择进行变相的实质审查,即收紧股东除名的意定口袋,退回到《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规定的唯一除名(实为失权)条款中,以不允许法外意定除名事由的形式认定个案中的具体约定无效。例如,(2021)桂01民终4319号案中,虽然公司章程修正案已规定“凡非正常原因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包括离职、辞职、除名、开除等情形),其股权(包括股份、股东资格、股东地位及股东的相关权利等)自行丧失”,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投资公司该修正案对公司股东丧失股东资格的条件进行修正涉及股东合法利益,但未征得黄某延同意,也不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17条的法定条件,因此无效。[25]又如,在山东的一起案件中,案涉新公司章程规定了股东除名的几种情形,如“公司在办理银行融资等业务时不签字”、“年度内累计两次不参加股东会议”等,并对被除名股东的出资额是否退还进行了苛刻约定,人民法院认为,“公司以决议形式解除股东资格这种严厉措施,只应用于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情形”,兰陵某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新公司章程新增列举的股东除名情形,超出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解除股东资格的范围,该条款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因此该条款无效。[26]
该等表面审查的趋势不仅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更糟糕的是会实质影响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打击营商环境。
以前文列举的典型股东除名样态之一——股权激励型股东除名为例,表面上,该等股权激励条款都会以“人走股留”的形式在章程中予以明确,要求全体股东必须在公司任职,且以任何形式因任何原因离开公司时都必须强制退股。基于对公司人合性的尊重,只进行表面审查的法院便会对该等条款及依据该等条款作出的强制退股决议认定有效。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上海大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诉楼建华等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认为:公司章程规定,股东退休时必须退股,公司根据章程规定召开股东会表决通过退休股东退股的决议未被判决撤销,应为有效,自该项决议表决通过之日,退休股东丧失其股东身份,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事实查明及认定予以认可,最终也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27]
但是现实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治往往并不分离,大股东对于公司的管理层具有极强的控制,把控着董事任免的权利甚至自身兼任董事身份,因此对于异议股东,大股东完全可以首先通过公司董事会将该等异议股东踢出公司,再以其未继续于公司任职为由,启动股东除名。而关于公司的人事任免,法院就更加不会进行实质审查了。因此,在当下形式审查的大趋势下,以股权激励的形式在初始章程中明确“人走股留”的股东除名条款,再在后期经营管理中打压中小股东,成了实务中不少公司和大股东的常用手段。
综上所述,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本次《公司法》修订截至三审稿也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股东除名制度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着上述种种繁杂而困难的实务问题。在该等情况下,法律工作者如何从立法论和解释论的角度尽量予以完善,各公司的股东们又该如何夹缝里求生存,尽量在当下困难重重的环境中保护自身的利益,且听下篇分解。
注释:
[1] 见前瞻网:全国注册企业数量统计,https://x.qianzhan.com/datav/gongshang/,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11月4日。
[2] 参见《德国商事公司法》,胡晓静、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译者前言第5-6页。
[3] 参见吴飞飞: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裁判解释——基于22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6期,第140-156页。
[4] 就股东财产性权益的限制和剥夺而言, 主流司法观点是股东基于其身份并按出资比例享有分红的权利是股东重要的财产性权利,是股东重要的自益权,除股东本人主张或同意放弃外,公司章程或股东会决议不得随意剥夺或限制,但具有合理原因的部分限制可以通过个案审查有效,具体可参见开封和源燃气有限公司、邹其海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民申5190号;就股东罚款而言,最高法公报案例指明: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会对股东处以罚款的规定,系公司全体股东所预设的对违反公司章程股东的一种制裁措施,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体现了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征,不违反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但公司章程在赋予股东会对股东处以罚款职权时,应明确规定罚款的标准、幅度,股东会在没有明确标准、幅度的情况下处罚股东,属法定依据不足,相应决议无效,具体可参见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鹃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0期。
[5] 参见吴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规则之检讨与完善,《现代法学》2021年第2期,第106-118页。
[6] 参见刘凯湘:论股东除名的事由、程序与后果,载《中外法商评论》2021年第1期,第162-183页。
[7] 参见刘胜军:论股东除名的事由与程序再造,载《法学》2023年第3期,第99-113页。
[8]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6号: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9] 参见凤建军:公司股东的“除名”与“失权”:从概念到规范,《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2013年第2期,第151页。
[10] 参见吴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除名规则之检讨与完善,《现代法学》2021年第2期,第106-118页。
[11] 黑龙江农垦完达山贸易有限公司与王斌力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12476号。
[12]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6号:宋文军诉西安市大华餐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13] 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诉祝鹃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0期。
[14] 托马斯·莱赛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6版)》,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647页。
[15] 甘肃生物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与西藏杰康酵母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藏01民终621号。
[16] 韩建民、张秀铭与曾奇夫、南京北交轨道交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纠纷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397号。
[17] 罗海峰与翁牛特旗乾昌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内04民终4756号。
[18] 张雁萍、臧家存公司决议纠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28号。
[19] 王华宣与付红雨等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335号
[20] 秀山县振鑫富锰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杨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4民终1441号。
[21] 福建启盛实验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吴保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08民终1019号。
[22] 参见王彦明、焦锦璇:股东除名决议撤销之诉的立法障碍与对策———兼论我国强制除名之诉的确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 年第3期,第117-124 页。
[23] 杨广州、潢川县东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议纠纷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申6236号。
[24] 唐顺华与永州博成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11民终3050号。
[25] 黄某延诉投资公司公司决议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桂01民终4319号。
[26] 兰陵县人民法院:【法官说法】公司章程可否随意约定开除股东?,载兰陵县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aPQmjArpBT6dsqjyQyYDfg,最后访问于2023年11月4日。
[27] 上海大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诉楼建华等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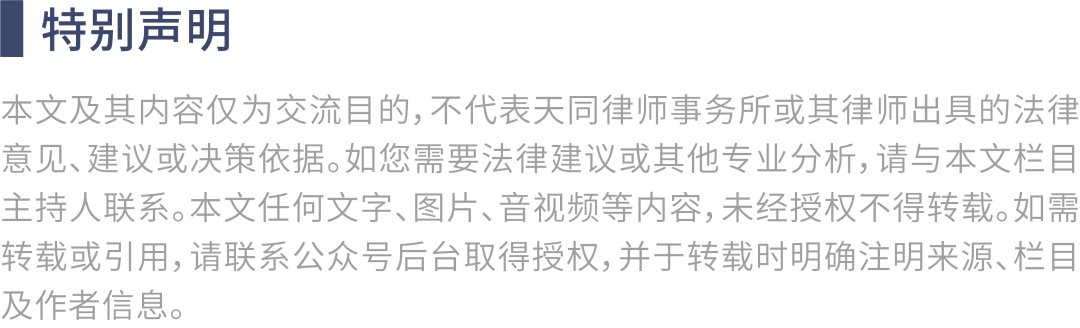
“公司法实务”栏目由庄喆律师主持,奋斗在公司法实务一线的天同律师们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公司法实务的相关思考。如您对“公司法实务”栏目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