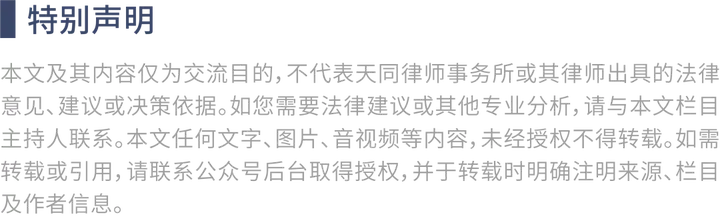文/王峰,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加赛,天同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俞雅琪,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佳颖、陆巧,天同律师事务所南京办公室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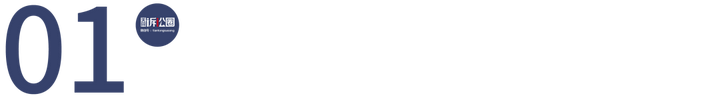
免责条款的解释规则——不利解释
关于免责条款的解释,我国现行法律已经确立了较为明确的规则。根据《民法典》第498条(原《合同法》第41条)、《保险法》第30条的规定,免责条款解释规则主要包括:(1)按照通常理解进行解释;(2)对免责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路径的,作对保险人不利解释。其中,“通常理解”主要指向《民法典》第142条、第466条(原《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的合同解释规则[1]。不利解释原则,又称保险合同的疑义利益解释规则,源自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被保险人利益的倾斜保护,系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而成的被保险人事后司法救济机制。[2]保险业务中,保险人作为条款提供者可能会使用意义不明确词语或文字损害投保人利益,或出于优势地位将不合理的解释强加于投保人,此时对条款提供者作不利解释,显然合理且必要。
司法实践中,《保险法》第30条的使用频率较高,在面临免责条款理解争议时,该条往往成为法院裁判的直接依据。但问题在于,需要避免不利解释原则成为庇护被保险人的“万能钥匙”,若裁判思路为价值衡量所主导,很容易导致滥用或误用不利解释原则,有损保险人权益。[3]
以车损险中“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负责赔偿”条款为例,实践中对于“实习期”的理解争议较大。原因在于,国务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2条第2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而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6修订)第74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4],二者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往往主张保险条款中的“实习期”既包括初次申领驾照的实习期,也包括增加准驾车型的实习期,进而主张增驾实习期内驾驶机动车牵引挂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免责范围。对此,司法实践中几乎半数法院直接适用《保险法》第30条,对“实习期”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认为“实习期”仅包括初次申领驾照的实习期,不包括增加准驾车型的实习期,进而不支持保险人的免责主张,如四川高院(2019)川民申4584号案、宿迁中院(2020)苏13民终2068号案、嘉兴中院(2020)浙04民终2427号案等。
有反对观点认为,上述裁判思路违反了一般合同解释进路。免责条款作为一般格式合同条款,其解释应首先遵循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方法[5],只有在运用其他解释原则仍无法解决争议的情况下,不利解释原则才有用武之地。换言之,不利解释原则系第二位合同解释方法[6],其适用条件应当受到明确限定,即仅当条款有歧义或语义不清时才需要解释,若无歧义或运用其他合同解释原则能够解决,则不能肆意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对被保险人作出倾斜保护甚至曲解条款本意。对于“实习期”免责条款,如果保险条款对“实习期”未作特别限定,则首先应对其进行文义解释。由于机动车驾驶证上往往会明确记载增驾车型及相应实习期,故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能力,增驾实习期属于广义的实习期概念,不应随意将其排除在实习期概念之外。况且《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2016修订)第74条明确规定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因此,该免责条款中的“实习期”包含增驾实习期,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路径,不具有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基础。相反,若将其限定为初次申领驾照的实习期,则相对牵强,与条款本意相悖。
单从合同解释角度,我们认可这一反对观点提出的解释进路。但如提示说明义务下篇中所述,因“实习期”免责条款系原文引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条文,法院难以通过司法裁判否认该法规重述免责条款效力,然而该类条款的实行与一般行为模式相冲突,所以法院通常选择运用不利解释原则保障实质公平。此外,《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确无增驾实习期的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又不属于法定范围内的法律法规,因此通过不利解释原则适用该类条款存在合理性。
以此为例旨在说明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路径。不利解释原则是为免责条款三重规制中相对灵活、原则化的保险栓,因此应当避免不利解释原则不当扩张。实践中,许多不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的原因在于未能理清免责条款三重规制的关系及效用。在许多应当通过订入限制和效力限制的场合,不利解释原则却仍然大行其道,并直接引发了法律适用问题向合同解释的逃逸。不利解释原则的灵活性及说理便捷性在带来司法裁量权及实质公正保护可能性的同时,亦应当存在适用路径上的严格限制。除前文所述的诸如以一般解释规则为前提外,还有部分法院将部分类型条款排除在不利解释之列。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专业术语不适用不利解释规则,但法律之外的专业术语或者其解释所体现的表面文义与实质含义有较大差别、不就该差别予以揭示将对投保人构成普遍性误导的,保险人应就上述差别予以揭示。保险人未就上述差别予以揭示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不利解释规则,作出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有利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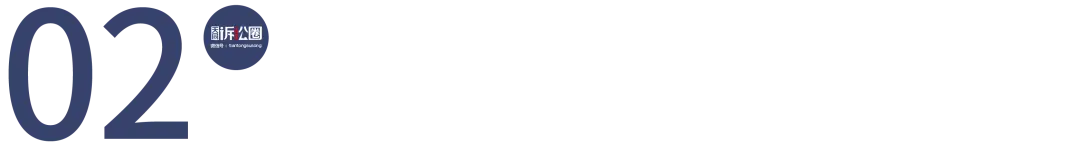
典型免责条款在实践中的适用
不利解释原则系免责条款在存在两种不同解释路径时采用的解释规则,也是免责条款规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对于通常情景下免责条款的适用,司法实践中亦存在不同尺度和认定标准。为尽可能全面展现免责条款在解释和适用中面临的各类困境,我们挑选出几类典型的免责条款,并剖析适用路径如下:
1.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免责条款
《保险法》第27条第2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法》第43条规定:“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法律之所以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规定为保险责任除外情形,原因在于保险事故的发生应当具有或然性,是意料之外偶然发生的,不是故意造成或必然发生的,否则将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的本质。[7]并且,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实际上系对保险人的欺诈,违背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若仍对其进行保护,将诱发道德风险。[8]保险实务中,除被保险人故意外,亦有保险合同将被保险人重大过失纳入保险人免责范畴,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基本险条款》第7条约定:“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
关于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免责条款,实践中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被保险人“故意”及“重大过失”的认定。一般而言,法院在认定被保险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保险事故发生时,往往优先考虑证据问题,如事故发生后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书、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责任书、公安部门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等第三方文件中是否查明事故发生原因,是否排除被保险人故意造成保险事故或存在重大过失的可能性等,如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6811号、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74民终211号、佛山中院(2022)粤06民终3866号、岳阳中院(2022)湘06民终2374号、广州中院(2021)粤01民终12996号、贵阳中院(2021)黔01民终1169号、深圳中院(2019)粤03民终13885号、烟台中院(2019)鲁06民终7497号等案。但通常情况下,仅依据第三方文件尚不能确定保险事故是否系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或保险合同双方仍会对该等文件载明的事故原因提出异议,法院仍需结合具体案情考虑被保险人主观心态。
关于被保险人故意的认定,法院在考察被保险人主观心态时一般考虑如下因素:被保险人有无骗保的动机、被保险人能否预见保险事故的发生、被保险人是否排斥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采取措施防止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事故的发生对被保险人而言有无获利空间、被保险人所追求的利益与保险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等,如岳阳中院(2022)湘06民终2374号、上海一中院(2011)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94号。比如,在岳阳中院(2022)湘06民终2374号案中,法院认为被保车辆购置时间不到三年,购置价11万元左右,车辆状况良好,若被保险人冒着生命危险故意制造落水事故,风险性过大,进而推定其主观上没有骗保的动机,客观上也没有骗保的必要。除前述主观因素外,法院在认定被保险人是否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还可能会考虑被保险人行为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在无人为因素干扰的自然情形下,案涉保险事故会否发生。仍以岳阳中院(2022)湘06民终2374号案为例,法院认为,即使案涉鉴定报告认为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明显人为操作痕迹,但结合事实发生经过,驾驶人往副驾驶上拿取电话时方向盘向右偏打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被保车辆自然落水的情形很大程度可能发生,故综合分析后排除了被保险人人为制造保险事故的可能性。
关于被保险人重大过失的认定,法院在考察被保险人主观心态时一般以被保险人是否尽到一般人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为判断标准。保险实务中,部分保险公司会在其财产基本险条款“释义”部分注明,重大过失行为是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苛以的较高要求,甚至连人们都应当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未达到的行为。至于一般人注意义务的来源,可能包括法律规范、行业规范、企业管理规范、保险标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操作习惯等。[9]一般而言,若被保险人或其他相关人员应当知悉相应规范而不知,或明知相应规范却未按照规范操作引发保险事故,应当被认定为未尽到一般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如在本溪中院(2022)辽05民终1193号案中,法院认为被保险人作为化工企业,理应知晓并严守相应法律规范,却在未取得相关资质的情况下违规生产引发保险事故,其对保险事故的发生负有重大过失。一般注意义务意味着不能超越一般人的认知能力,不应对被保险人苛以更高、更严的注意义务。如在苏州中院(2019)苏05民终4590号案中,法院认为操作手册仅要求被保险人关注每天傍晚的天气预报,并未要求其时刻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动态,故被保险人根据前一天傍晚获取的天气预报信息采取当天动作,尽到了一般注意义务,不构成重大过失。若要求被保险人根据当时当刻的天气预报采取相应动作,即苛以了被保险人更高、更严的注意义务,与一般人的认知能力不符。
2.被保险人未履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
《保险法》第49条、第52条规定,因保险标的转让或其他原因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此为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情形下被保险人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的法定免责规定。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意味着发生保险事故的可能性大幅增加,对保险人利益具有重大影响。[10]原因在于,保险人根据保险标的在特定情形下的危险程度核定费率并收取保险费,如果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相应费率不作调整,就会导致保险人以较低保险费承担较高保险责任,有失公允,与保险法对价平衡原则不符。因此,法律规定了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时应通知保险人,并赋予保险人增加保费或解除合同的权利;若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则因保险标的危险增加所引发的损失,保险人有权拒绝承担赔偿责任。[11]
为明确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4条列举了判断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时应综合考量的因素,包括保险标的用途、使用范围、所处环境、使用人或管理人是否改变及保险标的是否改装等。实践中,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认定情形多发生于车险领域,如将一般家庭用车用于运营网约车、货运车,或出租、转租给他人用于商业使用,导致投保车辆的用途、使用范围、使用环境、使用人等发生变化。[12]但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一般认为顺风车业务不同于网约快车、专车、出租车等业务,属于共享出行方式,没有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未增加车辆危险程度,如中山中院(2019)粤20民终830号案、嘉兴中院(2020)浙04民终2505号案、韶关中院(2020)粤02民终793号案。此外,保险人还可能主张驾驶人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情形属于危险程度增加。对此,法院普遍认为,在驾驶人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并驾驶与准驾车型相符的车辆时,其系合法驾驶人,即使其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也并未显著增加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不属于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形,如山东高院(2020)鲁民申10325号、衢州中院(2019)浙08民终679号、揭阳中院(2019)粤52民终90号案。可见,并非所有违规或违约操作均构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情形。
依据《保险法》第49条、第52条及《保险法司法解释(四)》第4条之规定,在判断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保险人是否可以据此减免保险责任时,应考虑危险变化的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所谓显著性,是指增加的危险对保险人的承保意愿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保险人在承保时知晓保险标的增加的危险,则其将会拒绝承保或以更高费率承保。[13]所谓持续性,则要求增加的危险必须具有持续状态,而非一时变化后恢复原状或危险增加后立即触发保险事故。原因在于,前者的危险状态已被消除,后者危险增加与保险事故发生的间隔时间较短,被保险人无法在短时间内通知保险人。由于保险人免责以被保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为前提,当被保险人并无履行通知义务的可能性时,保险人亦无据此免责之必要。[14]所谓不可预见性,是指增加的危险系保险合同订立时没有预见、无法预见,其内核在于保险人在计算保险费率时未将增加的危险作为精算定价因素予以考虑,其落脚点仍为保险法中的对价平衡原则。[15]实践中,因欠缺不可预见性而被法院认定危险程度并未增加的案例,如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终575号案、天津三中院(2020)津03民终137号案、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终301号案等。该等案件中,案涉保险单明确载明涉案车辆系营业货车,保险公司在承保时即对此知情,法院认为保险公司在评估承保风险、计算费率之时已将营运车辆可能带来的风险纳入考虑,案涉车辆用于营业运输可能引发的风险已被保险公司预见且评估,不属于风险增加。
除显著性、持续性、不可预见性以外,危险变化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亦属于保险人免责的重要条件。对此,我国保险法采近因原则,即保险事故的发生应当系因增加的危险所致,若保险事故主要由其他原因引起,则保险人不能据此要求免责。[16]近因原则系保险人依据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得以免责的必备条件,实践中保险人往往因危险增加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被阻断仍需按约承担保险责任。如前述提到将一般家庭用车变更为运营车辆会导致其危险程度增加,但在北京三中院(2019)京03民终8960号、中山中院(2019)粤20民终481号等案件中,法院认为,即使被保车辆注册了网约车业务、曾经从事过网约车运营,但事故发生之时被保车辆并非处于运营网约车状态,且事故发生原因与注册、运营网约车并无因果关系,保险公司据此主张免责,不予支持。又如对保险标的进行改装、改造,即使认为改装、改造行为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但保险公司仍应举证证明保险事故系因改装、改造行为而引发,否则危险增加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成立,保险人不能据此免责。[17]
3.被保险人未履行出险通知义务
《保险法》第21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此为我国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未履行出险通知义务的法定免责规定,其目的在于保证保险人在出险后能够及时对损失进行调查,防止因调查迟延导致证据灭失、影响责任确定。[18]
关于被保险人是否未及时通知保险人,是否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认定,实践中,需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何为“及时”?对此,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保险实务中,保险合同可能会在《保险法》第21条“及时通知”基础上作出明确约定,如保险事故发生后48小时、7日、30日、60日等。[19]若保险合同有约定的,则一般以约定为准。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约定均具有绝对效力。在判断被保险人是否在约定期限内通知保险人之前,应首先考察该等约定之合理性,即其是否限制了被保险人权利、加重了被保险人责任义务。若保险条款约定的通知期限过短,或直接约定被保险人未在一定期限内通知保险人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则无异于为被保险人索赔设置了行权障碍,依据《保险法》第19条,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20]若保险合同未约定被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时间,实践中法院一般根据被保险人通知保险人的时间、投保险种、保险事故性质、损害后果是否持续扩大等因素综合酌情认定被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是否及时、是否导致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21]至于被保险人履行通知义务的时间,保险人一般主张以其系统中登记或记载的被保险人正式报案时间为准,该时间有可能会与被保险人首次报案时间不一致。一般认为,若被保险人能够举证证明其在保险人登记的报案时间之前已经通知保险人或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知晓的,应以在先时间为准。[22]
其次,如何认定被保险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实践中,被保险人的主观状态并非认定要点,一般而言,似乎只要被保险人明知其应当及时通知被保险人,但客观上并未履行及时通知义务,且导致事故损失等定损因素无法确定,即推定被保险人具有可归责性,并未过多强调或关注被保险人主观意志。[23]
最后,只有当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并导致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无法确定时,保险人才可免于承担赔付责任。如何认定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践中主要考虑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阻断事由。正如前述,《保险法》第21条的目的在于保证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确定保险人赔付责任的定损因素能够及时得到固定,若有其他在案证据可以固定该等损失,如事故责任书、公估报告、鉴定报告、证人证言等,则即使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人,亦不会对其与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造成不利影响或导致其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此时因果关系不成立,保险人不能据此免责。[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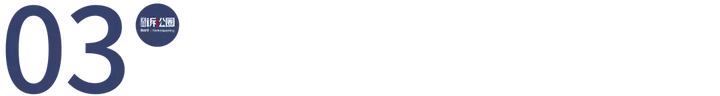
涉免责条款类案件的办理思路
在我们检索的两千余件案例中,部分案件为追求裁判的便捷性和结果的安定性,往往忽略了法律适用和说理部分的周延,导致免责条款各类规则常被错误混用。譬如,较多案例以保险人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为由认定免责条款无效;亦不乏在案材料能够盖然证明保险人已经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仅免责条款效力存在疑问时,仍以未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进行判决;还有免责条款效力不存在瑕疵,应当在条文解释规则上加以解决时,却以免责条款无效或保险人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为由直接判决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案例,等等。究其原因,多数案例混淆了免责条款的订入规则、效力规制和解释规则这三重规制,导致规范条件与法效果的匹配存在偏差。为此,我们尝试提出如下思路,以期理顺涉免责条款保险纠纷的审查进路:
首先,免责条款的识别,即明确具体案件中争议的“免责条款”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免责条款,是适用免责条款规制规则的基础和前提。对此,本系列文章之识别篇已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式进行了论述,此不赘言。值得强调的是,实践中,存在大量隐性免责条款,亦有不少披着免责条款外衣的一般格式条款,加之免责条款之识别与认定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具体标准可供参考,需在个案中综合考虑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保险合同的对价平衡、公平原则等因素进行认定。这也对办案人员的理论功底及保险实务经验均提出了较高要求。
其次,若经识别,个案中的争议条款属于免责条款,则需考察保险人是否对其尽到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这涉及免责条款是否构成合同条款、是否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发生效力的问题,即免责条款的订入控制。若保险人未尽提示、明确说明义务,依据《民法典》496条规定,该条款不属于合同内容;或依据《保险法》第17条规定,该条款对被保险人不发生效力。尽管二者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效果上无本质区别,均强调条款本身的拘束力。实践中普遍存在以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为由认定免责条款无效的案例[25],法律效果适用错误,应予注意。值得说明的是,实践中亦需格外警惕部分法院先行作出应对被保险人进行倾斜保护的利益衡量倾向,从而直接以裁判结果倒推的情形。
再次,与订入控制相对应的,是免责条款的效力控制,即判断免责条款是否具有无效事由。从逻辑进路而言,应先判断免责条款是否构成合同内容,再判断合同内容的效力,按照合同订立、效力环节依次推进。但从实际技术操作而言,免责条款的订入控制与效力控制并无严格先后顺序,既可先进行订入判断,若免责条款因未尽提示说明义务而不生效,则无需再对其进行效力判断,因其已丧失适用基础;反之,须进一步审查免责条款是否存在无效事由。同理,亦可先对免责条款进行效力判断,若免责条款存在无效事由,则无需考虑其是否发生效力;反之,应审查保险人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或存在提示说明义务减免等情形。在对免责条款进行效力判断时,既需考察其是否存在合同无效的一般事由,亦需要考察其是否存在《民法典》第497条、《保险法》第19条规定的明显限制被保险人权利、加重被保险人责任义务等格式条款无效事由,其本质在于判断保险条款约定的免责事由是否会不合理地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失衡,是否违反公平原则。除《民法典》第497条、《保险法》第19条列举情形外,还可考虑如下因素,如免责条款是否符合保险合同的合同目的及基本原则、是否与投保险种的保险范围存在冲突、是否客观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是否客观增加保险事故发生概率、免责条款对于保险事故风险的分配是否合理等。
最后,对于没有效力瑕疵的免责条款,在适用层面需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条款的解释,如前文所述,在理解免责条款时,应首先遵循一般合同条款的解释规则,警惕盲目扩大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实现对被保险人的过度倾斜保护,警惕价值衡量先行的裁判思路下由合同效力等问题向合同解释规则逃逸的思维惯性。二是免责条款适用时的因果关系考察,虽然我国保险立法与司法解释并未明确因果关系的认定标准,但近因原则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不言自明的选择。[26]一般认为,对损失的发生具有现实性、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可以被认定为近因,损失是近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延伸。[27]对因果关系的考察可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正向梳理风险事故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二是反向考察该链条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阻断事由,如果风险事故并非损失发生的决定性因素,则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注释:
[1] 王静:《保险类案裁判规则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160页。
[2] 吴庆宝:《商事审判实务难点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00-403页。
[3] 曹兴权,罗璨:“保险不利解释原则适用的二维视域”,载《现代法学》2013年4期。
[4]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于2021年12月17日进行了最新一次修订,修订后删除了关于增驾实习期的规定。目前检索到的案例均系此次修订前案例,故此处引用修订前条文。
[5] 包旭芳、吴庆宝:《保险诉讼原理与判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0-41页。
[6] 张雪楳:“保险法对格式条款规制内容的理解与适用”,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2010年第2辑(总第2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9页。
[7] 安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释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8] 奚晓明:《新保险法热点与疑难问题解答》,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184页。
[9] 苏州中院(2019)苏05民终4590号、本溪中院(2022)辽05民终1193号、无锡中院(2019)苏02民终431号、南通中院(2017)苏06民终1837号。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解与实用指南》,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4页。
[11] 唐德华、高圣平:《保险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
[12] 郑诗琦诉三星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载《人民法院公报》2022年第5期(总第309期)第40-42页;四川高院(2021)川民申679号、北京金融法院(2021)京74民终811号、江苏高院(2020)苏民申6557号、南京中院(2019)苏01民终3514号、宿迁中院(2019)苏13民终197号、北京三中院(2019)京03民终5776号、佛山中院(2019)粤06民终10757号、佛山中院(2019)粤06民终13006号、清远中院(2019)粤18民终786号、广州中院(2020)粤01民终1527号。
[13] 孙宏涛:“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完善之研究——以我国《保险法》第52条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6期。
[14] 张力毅:“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司法适用之检讨——基于277个案例的裁判文书之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6期。
[15] 孙宏涛:“我国《保险法》中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完善之研究——以我国《保险法》第52条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6期。
[16] 张力毅:“被保险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司法适用之检讨——基于277个案例的裁判文书之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6期。
[17] 因果关系阻断案例如连云港中院(2019)苏07民终1088号、宿迁中院(2019)苏13民终5410号、宿迁中院(2019)苏13民终5410号、北京二中院(2021)京02民终2318号、广州中院(2020)粤01民终25525号;因果关系成就案例如绍兴中院(2020)浙06民终1371号、佛山中院(2020)粤06民终4854号、云南高院(2020)云民申1310号。
[18] 唐德华、高圣平主编:《保险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19] 如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11条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及时(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20] 常州中院(2022)苏04民终920号、常州中院(2022)苏04民终1495号、威海中院(2022)鲁10民终1137号。
[21] 丽水中院(2021)浙11民终859号、南平中院(2021)闽07民终634号、佛山中院(2021)粤06民终3893号、南阳中院(2021)豫13民终1902号。
[22] 沈阳中院(2022)辽01民终10991号、抚顺中院(2022)辽04民终1149号。
[23] 桂林中院(2021)桂03民终2010号、保定中院(2021)冀06民终8755号、重庆五中院(2018)渝05民终4690号、常德中院(2021)湘07民终804号。
[24] 广州中院(2022)粤01民终1958号、日照中院(2022)鲁11民终3138号、威海中院(2022)鲁10民终1137号、商丘中院(2022)豫14民终1219号、青岛中院(2022)鲁02民终3559号。
[25] 天津三中院(2022)津03民终5451号、朝阳中院(2022)辽13民终2357号、湖南高院(2020)湘民申4442号、天津二中院(2019)津02民终4662号、杭州中院(2019)浙01民终7575号。
[26] 李玲、周立:“保险免责事由在认定保险因果关系中的应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16期。
[27] 陈萌、林晓君、黄宗琴:“保险责任中近因原则的适用”,载《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