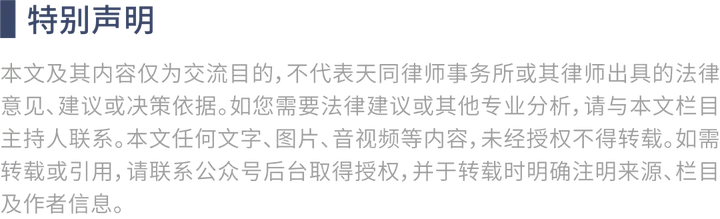转载来源:中外法学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作者按:本文发表于《中外法学》2023年第2期(第383-405页)。本次推送包括发表时因篇幅所限而删减的内容。北京大学纪海龙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吴香香教授,浙江大学钟瑞庆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生杨思佳、陈凯、马嘉骏、朱李圣、万桃源与硕士生汪庆、王仁君、江美茹、林艺、周涵、侯靖童、贾旭、张杨磊曾就本文初稿提出意见;责编贺剑教授细致审读并给出详细修改建议;在贺剑教授主持的2023年2月24日同名讲座中,南京大学叶金强教授、清华大学王洪亮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吴香香教授、北京大学葛云松教授、纪海龙教授诸位发表富有启发的评议。笔者于此一并致谢。文中疏误概由作者负责。
目录
引言
一、总则的名实之感:如何理解民法典总则编的形式逻辑与实质功能?
二、权利限制的隐忧:如何看待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关系?
三、权利能力的反思:如何应对自然人与团体权利能力概念及其突破?
四、行为能力相对化:如何设置未成年限制行为能力人自由行为界限?
五、权利变动的迷雾:如何解释法典关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立场?
六、分裂的错误规则:如何建构融贯的二元论或一元论错误规则体系?
结语
引言
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是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世纪之交的1900年8月8日,希尔伯特在巴黎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发表题为《数学问题》的演讲,提出23个最重要且迄未得到解决的数学问题,合称“希尔伯特问题”。贺剑教授雅意,以民法总则中的希尔伯特问题征稿于余。借希尔伯特之名,显然意在攀附。不过,即便明晓此点,依然难免惶恐。思之再三仍不揣冒昧敢于应承,是因为考虑到,若能借此创意就民法总则疑难问题再作追问,也许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自我思维测试。
攀附须有度。展开正文前,先就主题略加说明,以稍减唐突之意:
其一,法学固有其普世追求,诸如自由、正义、安全、秩序、效率等等无一不是,构成规范基础的市场交易结构亦大同小异,只不过所有这些追求与规范基础,均须在一国主权的实证法律秩序中实现。实证法律秩序各有不同,以实证法律规范为直接分析对象的法学因而兼具地方色彩,不同实证法框架下的概念体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提问方式亦相去甚远,在此意义上,欲要寻求适于所有法律样式的希尔伯特问题,恐怕本身就是一个希尔伯特问题。如此,本文将论域限缩为“中国”民法,也许有其正当性。
其二,进而,构成特定法律样式的学科基石概念与基本理念因其地方色彩较为淡薄,故本文不以之为直接讨论对象。申言之,权利、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法人、私法自治、信赖保护等概念与理念虽极具基础性,对于民法科学体系的建构亦至关重要,但至少在笔者个人理解中,中国法学整体上依然处于既有成果的吸收消化阶段,尚未达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创新的程度。因此,本文所论,仅限于实证法化的规范与规范体系,更为基础因而更为普世的概念与理念检讨则暂且存而不论。
其三,强调希尔伯特问题的“中国”属性,固在突出地方性,但若无一般意义,自无附会希尔伯特之必要,因而,本文将中国民法置于法律科学整体脉络下,目光流转于特殊性与普世性之间。
其四,在相同的公理系统内,数学具有逻辑唯一正确答案,此无关乎论者立场或视角,但法学并无类似公理系统,亦无如同数学般的唯一正确答案。任何人提出的任何法学问题或其解决方案均可能存在不同意见,本文所谓中国民法总则的希尔伯特问题同样如此。笔者以为复杂难解,在其他学者看来也许根本不是问题,或早已得到妥善解决,笔者以为扼腕之处,在其他学者看来也许堪称神来之笔,因而,本文纯属笔者一孔之见,于此合先叙明。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整理出笔者研习民法典及其总则编时颇觉困惑的六个问题,略作阐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六个问题涉及法典体例、权利、主体及法律行为四个领域,分别是总则的名实之惑、权利限制的隐忧、权利能力的反思、行为能力相对化、权利变动的迷雾与分裂的错误规则。困惑之所在,则或关乎立法者秉持的私法理念,或关乎较为单纯的规范技术,或兼而有之。除问题一稍指向法典理论外,其余问题均对应法典规范,以条文顺序排列先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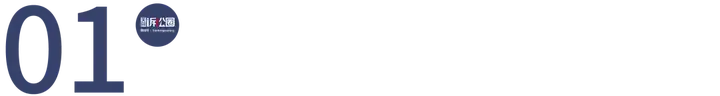
总则的名实之惑:如何理解民法典总则编的形式逻辑与实质功能?
德国民法典之前,法国民法典所代表的法学阶梯范式在法典家族一枝独秀。之后,德国民法典借助数学中最简单粗浅的提取公因式手法,将私法规范整合为一套逻辑色彩浓烈的体系,开创总分则编制的潘德克顿体例,与法学阶梯范式分庭抗礼。德国民法典总则编的条文数为240条,但并非全部条文皆具公因式地位。真正称得上是公因式的,不过是其中82条的法律行为。[1]换言之,为了独立设置总则编,立法者不惜调集近三分之二的条文用作陪衬。如此兴师动众,是否必要?
瑞士民法典的缔造者胡贝尔(Eugen Huber)对德国民法典的总分则编制即不以为然。胡贝尔虽然深受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影响,却有意舍弃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学术上最重要的理由在两方面:一是公因式辐射能力不足,导致分则编尤其是亲继两编与总则编各行其是;二是法典总则编过度抽象,导致分则编存在大量改变总则编一般规则的特别规定。[2]为了稍作弥补,瑞士民法典在第一编之前特设序编,规定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更以第7条(“债法有关契约成立、履行与废止之一般规定,亦适用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3])确立债法契约规则的实质公因式地位。德国民法典以法律行为为公因式,法律行为则奉契约原则,契约又以债法契约为原型。在此视角下,瑞士民法典虽未采纳德国民法典的总分则编制,但因着第7条的四两千斤功效,形式体例相去甚远的两部法典可谓各擅胜场。
民国编制法典,如梅仲协先生所言,取德例“十之六七”,瑞士“十之三四”。[4]此兼收众家之立法,若处理得当,自可博采其长而有所超越,但稍有不慎,则可能出现体系缺漏而事与愿违。民国民法典有关契约之规定颇具说明价值。民国民法典采德国五编制及总分则编制,总则编亦如德例以法律行为为核心,却将契约规则从总则编中抽出,置于债编。对此处置,梅仲协先生有过切中肯綮的评论:“我现行民法法典,既设有总则篇之规定,则关于契约上之通常原则,似宜订明于总则篇,方足以贯穿全部,前后呼应。乃民法起草者只认契约为债之发生原因之一种,规定于债篇通则中,编制稍欠斟酌。论者或谓此种编制,系师承瑞士债务法法典,未可厚非。殊不知瑞士民法,并不设总则篇,且于其第7条明定:债务法中关于契约之订立、效力及其消灭之普通规定,于民法事件,亦适用之。具徵其体制自与我不同。”[5]至于同属法律继受国的另一东亚国家日本,法典虽亦采德国五编制与总分则编制体例,但总则编法律行为不仅同样不含契约规则,通说更否认物权行为之存在,如此,以法律行为为核心构造总则编之意义何在,难免令人生疑。
瑞士、民国与日本从不同侧面揭示或暴露了法典总则编以及法律行为公因式地位的弱点,所有这些,我国《民法典》皆须面对。不止于此。关于总则编,我国《民法典》有其自身特性,因而另须在至少三个问题上再作斟酌:第一,法律行为是否依然可称各分编的公因式?第二,总则编是否依然属于德国提取公因式意义上的总则?第三,设置总则编是否合乎我国立法的目的理性?
瑞士民法指摘总则编规范公因式能力不足,此非空穴来风。且不论亲属继承二编中,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被大幅修正乃至排除,即便在财产法领域,不仅物权法定主义极大限缩私人形成自由,债法中真正贯通法律行为逻辑的,亦仅意定之债而已,侵权、不当得利乃至无因管理等法定之债,至少在债的发生上,几乎与法律行为无关。只不过,德国民法典的藏拙技巧高明,法律行为的公因式地位尚属稳固。德国民法典债编总则以债的效力尤其是意定之债的效力为原型提取公因式,侵权、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藏身于债编分则,成为众多债的类型之一,从而将法定因素对体例的影响降至最低;物编中的处分行为则因其效力在于处分既有权利,物权法定对于类型创设自由的限制亦隐而不现。如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分别贯通于债编与物编,共同呼应总则编法律行为一般规则,成为民事财产法的“任督二脉”(王泽鉴教授语)。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独立成编,释放了原本蜗居于债编分则的侵权规范,却也因其与合同编并立而消解了债的效力这一公因式。这一消解对于法律行为公因式地位的影响,好似将德国民法典覆盖于债编的遮掩物撤去,将侵权行为之债推至台前,法律行为规则之无法贯通因此直接暴露于外。同样,人格权脱离主体法与侵权法的禁锢而独立成编,亦极大丰富了人格权实证法规范,但法律行为在人格权领域的作为极为有限,故在体例上,总则编法律行为规则的贯通性亦因此受阻。除须面对传统公因式能力不足的质疑外,我国《民法典》又增加法律行为规则难以贯通的两编,法律行为规则是否依然可称各分编的公因式?
法律行为之为公因式,是以权利的动态变动为视角。但这不意味着,此系公因式提取的唯一手法。实际上,早在1811年颁布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即已尝试以权利本身为基准,在法典第一层级提取公因式。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前两编直接呼应罗马法上的经典权利分类,分别规定对人权(Von dem Personenrechte)与对物权(Von dem Sachenrechte),第三编则是对人权与对物权的共通规定(Von den gemeinschaftlichen Bestimmungen der Personen- und Sachenrechte)。[6]第三编含五章共162条,除第五章“自2013年2月1日起生效及过渡规定”仅包含1条关于施行法的规定外,其余四章均属对人权与对物权的实质“共通规定”。第一章“权利义务的强化”系关于担保的规定,另外三章依次为“权利义务的变更”、“权利义务的废止”与“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
我国《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名为“民事权利”,既然位列总则,所含内容理应属于权利的“共通规定”。但实际上,该章除少量条文(第128-132条)有着程度不一的共通性外,其他大部分条款(第109-127条)均仅关乎特定权利,基本属于各分则编或单行法所规定权利类型的单纯列举或立法定义,显然并非适用于各分则编的共通规则,主要功能在于充当活页环串起法典各分则编。[7]与之呼应,各分编第一条均规定本编调整范围,以维持单行法转化为各分编时的相对独立性。因此,我国《民法典》总则编民事权利章的体例功能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三编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2017年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宣称,《民法典》总则编“采取‘提取公因式’的办法,将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定写入草案”,但一方面,法律行为无法如同德国民法典般贯通分则编而成为真正的公因式,另一方面,民事权利章所含内容亦非适用于各分则编的共通规定,问题因而在于,我国《民法典》总则编是否依然在德国总分则编制的传统逻辑之下?如果回答是否定的,此总则编应如何理解?
新中国立法实践表明,追随德国式总分则立法体例未必合乎我国立法之目的理性。德国创立的总分则编制,将共通规范抽取至总则编,又采取相同的手法,在各分则编继续贯彻从一般到特殊的编纂技术,层层叠叠,法典结构因此变得空前复杂。外行面对迷宫般的法典,往往感觉手足无措。清末民律草案以及民国民法典均以德为师,未必经过多少思考权衡,更多恐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自然反应。然而,新中国的立法实践,向以通俗易懂为基本追求。通俗易懂的意思,是外行也能看懂。为此,法典应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最好避免文雅表达,当然也最好避免让外行陷入结构迷宫。数十年来,我国立法基本上已经把术语的专业性降到最低程度——《民法典》在百忙之中还把《合同法》规定多年但显得过于专业的“居间合同”改成日常用语“中介合同”,文雅表达也因为在立法者能力之外而不必多虑,唯一可虑的,是如何让外行迅速从法典中找到想要的条文。
《民法典》总则编的逻辑虽不同于德国,但中国式总分则编制体例下,规范依然遭到一定程度的分拆乃至割裂。例如,法律行为难以贯通各分则编,主要适用领域在合同编,却以总分则编制将法律行为与合同规范隔开,此于外行而言,恐怕不能说是福音;再如,物权法定主义作为物权法的核心原则,却被规定于总则编民事权利章,远离物权编,此无论于法律外行或法律适用,恐怕都谈不上理想;又如,民事责任在总则编单辟第八章作集中规定,但如同民事权利章,或者是不具有可适用性的宣示条款(第176条),或者是抽调分则编规范的简单拼装(第177-180、185、186条),唯有关于自力救济规范(第181-184条)勉强可称一般规则,但同属自力救济的自助行为却又归到侵权责任编(第1177条),而不可抗力规则,总则编民事责任章第180条与合同编第590条皆予以规定,区区十二条的民事责任章,拼装、割裂、重叠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如此充满逻辑迷雾的规范架构,其迷宫程度与德国相比恐怕犹有过之,专业性与体系性固然不必苛求,外行友好性又如何体现?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中国式总分则编制的民法典似乎未必便于法律外行查阅。令人困惑之处因而在于,如果外行友好真是立法的追求,为何对总分则编制如此执着、甚至即便无总则之实也要竭力维持总则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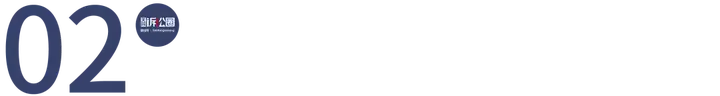
权利限制的隐忧:如何看待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关系?
民法向称权利之法。《民法典》第3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将颇具政治意味的宣言写入法典,以此表明对于权利保护的重视。体例上,法典第二编至第六编对应各类民事权利,第七编以作为权利救济法的侵权责任殿后。王利明教授指出:“我国民法典的整体框架思路因此是‘确权—救济’,这是民法典体系以权利为中心的具体体现。”[8]
权利意味着自由,此不言而喻;任何自由均有其边界,亦毋庸置疑。问题在于,如何为自由划界?《民法典》第130条确认:“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权利,不受干涉。”在此逻辑下,如何正当行使权利,法律不必置喙,所要关注的,只是权利的非正当行使。换言之,对于权利行使的限制必以消极规则的面目出现。《民法典》中,第6条公平原则、第7条诚信原则、第8条公序良俗原则、第9条绿色原则与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皆与权利限制有关,其中尤以诚信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最为醒目。与其他各项原则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第一章“基本规定”不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被规定于第五章“民事权利”,在划定权利界限方面,显然有着更为直接的相关性。不过,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迟至2017年始经《民法总则》进入制定法,在此之前,权利限制的规范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第4条的诚信原则。然则此等均具权利限制效力的法律规范如何发挥功能?尤其是,诚信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如何协调?这一问题的实质指向是,在此数项原则的共同作用下,如何把握权利自由及其限制之间的消长关系?
德国民法典亦有两项原则性规定可直接用于权利限制。一是第226条的恶意刁难之禁止:“权利之行使,不得仅以损害他人为目的。”[9]二是第242条的依诚实信用而给付:“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信用之要求,并参酌交易习惯而履行给付。”前者亦称权利滥用之禁止,乃是民国民法典及我国现行民法典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比较法来源;后者则为著名的诚信原则。表面上看,第226条位列总则编“权利的行使、自卫、自助”章,系权利限制的直接规范,第242条则属债编规范,并且仅以债务给付为其规范对象,但实际上,诚信原则适用范围得到极大扩张,远远越出债编范畴、更大大突破债务给付之文义限制,成为事实上的总则规范,一般性适用于所有权利的行使,反倒权利禁止滥用原则很少被适用。其原因,与第226条的苛刻要件有关。
德国民法典第226条系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首次制定法文本明确表述。在此之前,关于私权,各国普遍接受罗马法上“权利的行使对任何人都不意味着非正义”格言,不认为有必要通过实证法对权利行使作出一般限制。德国民法典尽管有此规定,但构成要件极为苛刻。根据第226条,权利行使行为仅在客观上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害,尚不足以构成恶意行使权利之滥用行为,即使权利行使具有损害他人的意图,仍无法适用该法条,唯在损害他人是行使权利的唯一目的时,始可称为恶意刁难的权利滥用行为。[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遵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立法者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自己的利益,公正的利益均衡状态将自然实现。[11]此意味着,为权利滥用之构成设置如此苛刻的条件,系立法者有意为之,目的在于尽可能维护私权自由理念。如今,权利行使不受限制之观念已被放弃,只不过限制主要不是来自于第226条,而是悖俗与诚信违反之禁止。[12]德国学说与判例普遍认为,几乎所有权利滥用的判断,均须借助诚信原则而落入其适用场域之内。[13]换言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为诚信原则所吸收。
法国亦属吸收模式,只不过与德国相反,系以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吸收诚信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3款与第1135条乃是诚信原则的实证法依据,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则未规定,不过,学者通过权利外在限制与内在限制的区分,为权利滥用理论找到生存空间。[14]如今,法国关于权利滥用的判例覆盖了从所有权、契约关系到家庭、集体劳动关系乃至诉权运用等几乎所有私法领域,[15]而诚信原则迄今仍只得到少量适用。[16]原因在于,基于对“意思自治”观念的尊奉,法国学者普遍相信“契约所约即为正义”(Qui dit contractuel dit juste),因而民法典关于诚信与公平之规定一直被指责为缺乏实际意义。[17]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兴起后,诚信原则的功能更是被吸收,处于不活跃状态。
瑞士在德国的基础上,将诚信与禁止权利滥用两项原则整合规定在同一条。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第1款)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须依诚实信用为之。(第2款)显属权利滥用者,不受法律保护。”前款为诚信原则,后款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二者同归一条,乃是因为有着相似的功能。对此,瑞士联邦法院一份判决书有过简要概括:“司法实践已把瑞民第2条认定为‘权利行使的界限’。”[18]至于两款之间的关系,联邦法院将第2款视为第1款的补充,并且往往两款合并适用。[19]不过,为了不至于完全重复,瑞士学理依然试图对二者作出区分。依其通说,两项原则在功能上有着某种递进关系,该递进关系所呈现的,正是第2款对第1款的补充意义。其中,诚信原则具有解释与填补功能(interpretative und ergänzende Funktion),法院在解释和补充私法关系时适用,权利滥用之禁止则进而发挥矫正功能(Berichtigungsfunktion),适用于矫正某项法律或合同规则的场合。[20]通过法律方法上的功能区分,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呈现分工合作的局面,瑞士模式因而可称分工模式。
无论吸收模式抑或分工模式,皆注意到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对于权利限制有着相近的功能,从而有意协调两项原则的适用关系。此协调,可防范两项原则因为各自蔓延而反噬权利自由。与之不同的是重叠模式,此存在于汉语法学。
关于诚信原则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台湾地区法学对我国大陆有着关键的影响。民国民法典原仿德例于债编第219条规定:“行使债权、履行债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1982年,台湾地区修正法典之总则部分,将其改列为总则编第148条第2款:“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1999年债编修正又增列第245-1条,借助诚信原则将缔约过失制度法定化。此外,其“消费者保护法”第12条第1项亦规定:“定型化契约中之条款违反诚信原则,对消费者显失公平者,无效。”王泽鉴教授指出,“上述三项修正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君临法域的帝王法条,对民法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1]“帝王法条”之认知,系受德国学说影响所致。[22]这一认知,对大陆学者形成决定性影响。梁慧星教授与王利明教授均援引王泽鉴教授《诚信原则仅适用于债之关系?》一文,称此原则为现代民法“最高指导原则”,系“帝王条款(规则)”。[23]
耐人寻味的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并不因为诚信原则的备受重视而遭到轻忽。民国民法典第148条规定:“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该表述几乎是德文语句的逐字翻译,唯在一个关键之处作出改变,即将德国民法典第226条的“仅(nur)”以损害他人为目的放宽为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放宽的后果是,构成权利滥用者,“不必其目的全在损害他人”,“第一四八条之所谓主要目的,即其行为虽不无某种正当之目的,但与其权利一般之社会任务相背时,即属滥用权利。”[24]另外,民国与台湾地区学者多主张,所谓“以损害他人为目的”,德国民法典虽以主观标准判断,但为顾及法律社会化之进步潮流,顺应权利滥用要件客观化之趋势,宜以客观标准为断。[25]“社会化”与“客观化”构成偏离德国轨道的关键考量,在此考量下,权利滥用标准大大泛化。1982年台湾地区修正法典总则编,将原第148条内容变更为第1项,并增列一种情形,修订为:“权利之行使,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王泽鉴教授指出,“行使权利不得违反公共利益”为台湾地区所创,同时,修订结果使得权利行使“具有社会化的内涵、伦理的性质及客观的判断标准”。[26]要件宽松化与适用宽泛化的趋势亦因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相同的趋势上,我国实证法在台湾地区的基础上又迈进一步。《民法典》新增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内容上,第132条(“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删除权利行使目的之主观标准,仅保留客观标准,并且该客观标准较之台湾地区又大幅放宽,国家利益、他人合法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鼎足为三。《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3条在此基础上作出细化。其中第1款为客观标准提供判定依据:“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出认定。”第2款则仿照台湾地区新增主观标准并继续放宽:“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如此,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符合其一,即可构成权利滥用。此创举,司法解释执笔者称之为“动态系统论”的运用结果。[27]标准如此宽松,可以想见,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司法适用必定有着广阔的空间,甚至难免让人怀疑,基于特定司法政策的考量,行使债权将导致债务人破产甚或生活不便的情形是否也可归入权利滥用之列,毕竟破产带来大量失业,无疑关乎社会公共利益,即使仅仅带来生活不便,亦难免涉及“他人合法权益”或“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
如前所述,无论强调诚信原则还是偏重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抑或划界分工,德法瑞诸国的权利限制轨迹均显得小心翼翼。与之相较,汉语法域无论立法、司法抑或学说,给人以大刀阔斧之感。谈及诚信原则时,高调突出其权利限制功能而尊其为“帝王条款”;论及权利滥用之禁止时,又门户大开,慷慨泛化其适用要件。双管齐下重叠交错,以及各自适用要件极大泛化,这些固然不无检讨余地,但也都只是技术化的表象,真正令人担忧的是隐于其后的权利理念。在这种理念中,权利限制较之自由行使似乎更具基础性。笔者感到疑惑的是,为何立法者如此醉心于权利限制?如此不遗余力编织权利限制之网,于私权自由乃至私权神圣理念是否有益?毕竟,限制与自由此长彼消,当权利行使动辄得咎、限制因而成为出发点时,自由也就相应成为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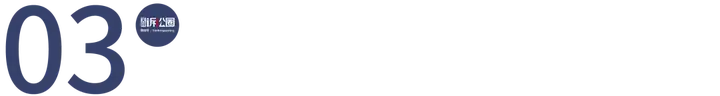
权利能力的反思:如何应对自然人与团体权利能力概念及其突破?
德国民法创造形式化权利能力概念,既以此表达所有自然人生而平等的观念,亦借助这一概念将自然人与团体整合于相同的主体范畴内。无论有意抑或无心,我国《民法典》恰有两项突破对这两项成就提出挑战。两项突破分别涉及自然人与团体:涉及自然人者,系胎儿权利能力之确认,此为《民法典》第16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所规范;涉及团体者,系关于非法人组织法律地位的规定,核心规范见诸第102条第1款(“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所提出的挑战是:人生而平等命题可否在实证法上适用于出生前的胎儿?“全有或全无”的权利能力概念是否适于团体?
(一)胎儿权利能力的一般化
人并非凭空出现,从母体受孕到活体娩出须经大约40周时间。何时可称之为“人”,神学、医学和法学各有考虑。法学上,有学者认为,根据自然法观念,自受胎之日起,形成中的人即应享有权利能力,[28]但各国实证法仍普遍以出生(之完成)作为权利能力的始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规则需要准确界定权利能力的开始时间,而受胎时刻难以确定,生育时点则为此提供了可能。[29]
正常情况下,受孕胎儿终将出生,若一概不对胎儿提供保护,有违人道精神。问题在于,如何保护?各立法例采取的办法一般是将权利能力前置,以例外条款的方式予胎儿以权利能力。具体又有两种做法。一是概括式,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款:“婴儿以其活体出生为限,出生前具有权利能力。”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二为列举式,德国民法典未设胎儿权利能力一般条款,而是通过具体条文一一确定胎儿之为权利主体的领域,如第844条第2款末句:“若第三人于损害发生时已受孕,纵未出生,亦发生赔偿义务。”第1923条第2款:“继承发生时虽未生存却已受孕者,视为继承之前即已出生。”两种做法的差别在于:概括式在一般意义上承认胎儿的权利能力,“凡关于胎儿利益之保护,均视为既已出生,……胎儿能取得的权利,并无限制”;[30]列举式则仅认可所列举范围内的权利能力。《民法典》第16条之规范模式,较接近于台湾,亦属概括式立法,即在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一般性赋予胎儿权利能力。
对未出生的胎儿提供相当于已出生之人的保护,德国有学者以之为拟制。[31]《民法典》第16条前句亦称“视为”,似同采拟制技术。但拟制的效果是终局的,即便与实际情形不符,亦不可推翻。胎儿的保护则以出生存活为条件,出生之前,效果尚未终局确定。条件有停止条件与解除条件之别。德国有学者以停止条件解释。[32]台湾通说则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所谓“以非死产者为限,视为既已出生”,宜解释为法定解除条件,胎儿出生前便取得权利能力,死产则溯及丧失权利能力。理由在于:若解释为附停止条件,则出生前的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此时发生的损害救济或继承皆不得主张,似不足保护胎儿利益;若为附解除条件,则胎儿虽未出生,仍可主张损害赔偿等请求,若为死体,就所获得的损害赔偿发生不当得利返还,对胎儿保护甚是周全。[33]
《民法典》第16条后句但书称“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规范方式与台湾相似,文义上亦较接近法定解除条件说。第1155条针对继承另作具体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所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民法典继承编解释》第31条第2款第2分句规定,是指“如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显然是法定解除条件运用的结果。《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4条则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法定代理人主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胎儿出生前可通过法定代理人行使权利,此亦在法定解除条件框架之内。不过,无论《民法典》抑或《民法典总则编解释》,均未涉及胎儿损害赔偿问题。一种解释是,损害赔偿请求权亦属“胎儿利益保护”,故包含在《民法典》第16条前句中的“等”之列。[34]如此,《民法典》第16条可谓全面对标台湾地区。
不过,同为胎儿利益保护,继承与损害赔偿未必奉行相同的逻辑。法定继承中,遗产的分配对象系被继承人死亡时确定的继承人。为确保胎儿尽可能获得遗产以备出生后所需,从而最大限度保护新生婴儿利益,有必要将胎儿列为继承人俾使参与遗产分配,否则,待得婴儿出生,遗产重作分配几无可能。相应的,因胎儿死产而导致的遗产再次分配便成为需要承受的制度成本。此意味着,关于继承利益的保护,胎儿权利能力以法定解除条件对待似较为适宜。损害赔偿与之不同。胎儿所受损害,并无继承所面对的可能失去保护之急迫风险,更重要的是,胎儿出生前,损害难以确定。此难以确定,既含质的方面,即何种损害可归于未出生胎儿,亦含量的方面,即胎儿损害程度如何量度。
首先,质的方面,胎儿娩出前如同母体器官,属于母体的一部分,不同的只是,胎儿终将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但即便如此,其独立意义亦始于脱离母体之时。腹中胎儿所受一切损害,均由母亲承受;所作一切治疗,皆作用于母亲身体;所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亦皆归于母亲。母亲以自己名义提起包括医治胎儿在内的损害赔偿,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反之,若是试图分离胎儿损害和母体损害,将面临重重障碍。直接针对胎儿的救治手段固然可归诸胎儿,但何尝不是母体损害的救治?而母体自身的损害和救治,亦难免对胎儿构成程度不同的影响,此时又如何清楚分辨?其次,量的方面,即便可对胎儿所受损害予以单独观察,其损害程度亦难以量度。胎儿从受孕胚胎到娩出,经历各个生命成长阶段,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外在损害发生时,如何确定损害程度?若以出生后的身体状况为判断标准,恰恰表明,胎儿损害须待出生方可确定。
问题不止于此。若许胎儿出生前提起损害赔偿,诉讼上的难题亦不可忽视。诉讼上,母亲虽无妨以胎儿法定代理人身份提起诉讼,但此亦往往意味着,母亲须同时提起两项诉讼,一为自己,一为胎儿。进而,举证责任上,母亲不仅须一般性证明损害与因果关系,还须进一步证明自己与胎儿各自损害及其因果关系。考虑到胎儿损害确定之困难,这一双重举证要求难度恐怕不止加倍。之后需要面对的,还有赔偿额的确定以及可能的返还与追加。若胎儿未能活体出生,几乎必然涉及赔偿返还;活体出生,亦可能因为赔偿不足再次求偿或赔偿过度须作返还。如此层层设卡,难免让人怀疑,法律令胎儿在出生前提起诉请,究竟是旨在保护胎儿抑或只是声称保护胎儿?
所有的困难皆源于胎儿出生前的独立赔偿请求。待胎儿出生后再为损害赔偿,出生前一切损害归于母体,则可消解上述所有困难。仍有疑问的是,胎儿生命健康遭受侵害所生停止侵害请求权是否又须另作别论?此类请求权既具时间急迫性,且不存在损害程度认定难题,往往还是胎儿得以健康出生的前提,此时是否应予胎儿独立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以便对其生命与健康预作保护?若是应当,该权利又如何行使?父母怠于行使或行使不当是否须负损害赔偿之责?母亲自身与胎儿的停止侵害请求权又该如何协调?
至于诸如受赠等通过法律行为纯获利益的情形,通过赋予胎儿权利能力的方式加以保护,其必要性似乎值得斟酌。规范技术上,胎儿欲成为受赠人,除须创设权利能力之例外外,还须进一步在无行为能力、法定代理(尤其是涉及父母双方代理时)等伴随法律行为始终的规则全程亮起例外绿灯,制度成本是否过高,恐怕有必要再作权衡,尤其考虑到赋予权利能力未必是保护胎儿利益唯一方式,其正当性更须三思。为了保护胎儿的受赠利益,法律上至少还包括对法定代理人附负担的赠与、以胎儿出生为条件的第三人利益契约、设立信托基金等构造。如果在既有框架内可实现相同规范目的,是否有必要如此大刀阔斧创设例外撕裂一般规则?
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权利能力一般化带来的真正挑战也许未必在于上述技术细节,而在于权利能力起算时点的重新考量。生物意义上的生命始于受孕,但规范意义上的生命却始于出生,看起来,二者时间不能重合系出现胎儿特别保护格局的关键原因。规范意义不能与生物意义保持一致,重要原因又在于察知生物意义生命时点的技术障碍。如今医学技术发展,这一障碍即使尚未得到解决,亦已大大缓解。更大的挑战因而在于:如果胎儿出生前即可具备一般性的权利能力,是否可能往前再迈一步,将权利能力起始时点提前至受孕之日,而不再以例外规则的形式赋予胎儿权利能力?如此,权利能力一般化之立场可名正言顺,对于胎儿的保护亦堪称全面,符合自然法理念。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建立在既有权利能力规则基础上的规范体系与交往模式也许需要作出大幅调整乃至推倒重来,例如,胎儿是否因此具备承受义务的能力?当父母以胎儿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时,法律效果如何归属?侵害胎儿致死是否构成生命权的侵害?堕胎等孕母“侵害”胎儿生命与健康的合法性又如何评估?等等。
(二)非法人组织作为第三主体
既有规则下,自然人权利能力均为完全,除胎儿的特殊用法外,不存在“部分权利能力”之人,无权利能力则不可能是权利主体。此“全有或全无”的模式常被套用于团体:具有权利主体地位的团体称法人,拥有独立的权利能力;未取得法人资格者,无主体资格。权利主体的二元结构由此得以逻辑构建,简单清晰,界限分明。
然而,生活逻辑似乎复杂许多。例如,合伙企业并非法人,但得以其名义参与法律交往,具有诉讼当事人能力,企业财产相对独立于合伙人其他个人财产,对于企业债务的承担,合伙人个人财产承担的是补充责任,等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合伙企业与合伙人相对独立。简单宣称合伙企业不是法人因而无主体资格,难免显得草率。于是,“第三主体”说顺势而生。《民法典》第四章为“非法人组织”,与第二章“自然人”及第三章“法人”并列,并于第102条第1款规定:“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虽未明确称之为第三主体,但从体例安排上,可视之为“第三主体”说的产物。
第三主体可回应交往需求,缓和二元主体格局的僵硬性。不过,第三主体说的漏洞亦一望可知。所谓权利能力,指的是成为权利与义务承受者的能力。合伙企业的财产却是合伙人共有,非为企业所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人,亦是各合伙人;更有进者,依现行税法,合伙企业本身并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各合伙人才是纳税主体。合伙企业的“主体”地位如何能与自然人、法人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如果权利能力“全有或全无”,“第三主体”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存在。
需要反思的问题似乎在于:团体的权利能力,是否适用自然人的“全有或全无”逻辑?基于人性尊严的伦理考虑,现代法律肯认所有自然人自出生即享有相同程度的权利能力,同时废止人格减等制度。因而,称自然人“有”权利能力与自然人有“完全”权利能力,意义并无分别,此即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全有或全无”逻辑。这一逻辑未必适于团体。[35]
通过权利能力这一形式化概念,法人在德国民法中得以与自然人并列为“人“,但这不意味着,揭开形式化面纱,法人依然与自然人有着相同的伦理意义。法人作为法律构造物,并无承载人性尊严之伦理价值,仅仅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法人设立者的目的。实证法之所以予某类团体以权利能力,自然非为尊重法人的伦理尊严,更多是基于合目的性的考虑,如有助于节省交易成本、降低交往风险等等。既然如此,何种团体拥有何种程度的权利能力,亦属合目的性考量范畴。当事人根据需要,得自由设立独立程度不同的团体。换言之,团体是否应具或应具何种程度的权利能力,仅仅是技术性的归属手段而已。实证法无妨根据团体的独立程度,予以相应权利能力。[36]法人并非团体的唯一构造形式,拥有“完全”权利能力亦非团体的逻辑必然。如此,与自然人权利能力之“全有或全无”模式不同,团体的权利能力表现为“或多或少”。
如果这一视角可以成立,对于团体,以“是否具有权利能力”方式提问便不再适宜,恰当的提问是“具有何种程度的权利能力”。根据独立程度之不同,自然人之间的结合处于从“无权利能力”增强至“完全权利能力”的类型序列中:最为松散不具有任何独立地位的结合处于序列一端,如单纯以买卖、租赁等契约连接的双方当事人互为对立两造,难以形成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独立团体,故不具有任何权利能力;最为紧密的结合,则是有着完整利益归属关系的法人;在此两端之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各类合伙等团体依其独立程度处在权利能力光谱的不同位置。[37]如果以法人为“完全”权利能力,则两端之间的团体均仅具“部分”权利能力。如此,权利能力“全有或全无”带来的“第三主体”困境可迎刃而解。
其实并未迎刃而解。“或多或少”的权利能力进路下,“第三主体”之说似乎同样不合乎逻辑。原因在于,既然强调权利能力的不同程度,“是否具备主体资格”此类非此即彼式的提问便不再适宜,非此即彼式的二元主体格局亦无生成基础,在此前提下的“第三主体”便难免师出无名。更棘手的是,若是回归团体的工具性地位认知,团体权利能力转奉“或多或少”逻辑,作为形式概念的权利能力,其意义也许就需要重作评估,例如,将法人定义为具有权利能力的主体(《民法典》第57条)是否依然成立?以此形式概念统合自然人与法人、构建统一主体制度的规范方向是否须随之调整?与权利能力脉络相连的其他制度体系也许亦须重作审视,例如法人(团体)所享有的人格权是否仍有其正当性?团体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如何建立规范关联?除赋予法人以行为能力外,其他团体是否拥有行为能力?不法行为能力又如何?等等。此意味着,权利能力概念在团体中的实质化,也许将改变既往建立在形式化权利能力概念基础上的规范设置方式,民事主体尤其是私法团体制度及规范体系将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需要仔细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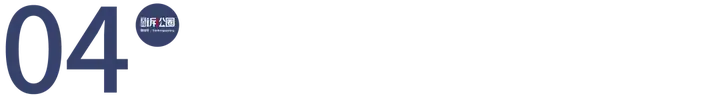
行为能力相对化:如何设置未成年限制行为能力人自由行为界限?
限制行为能力介于无行为能力与完全行为能力之间,对其行为规制,法律要做的,是划界与制限——划出自由行为之边界并确定非自由领域管制的限度。德国法上,除非纯获法律利益,否则限制行为能力人行为均须征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德国民法典第107条)。其民法典第110条虽以“零用钱条款”稍作缓和,但德国通说认为,此处其实存在一种特殊允许,即当法定代理人或得到法定代理人同意之第三人给予金钱,并要求为某种目的使用或供其自由使用时,即可推断其以此使用领域为条件事先表示同意。[38]换言之,“零用钱条款”并未突破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之规则。与德国相比,我国显得宽松灵活。作为《民法通则》规则的延续,《民法典》第19条但书规定,未成年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自由行为领域分两部分:一是“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二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法律行为。两部分中,“纯获利益”系新增规则,可限缩解释为“法律利益”从而封锁边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则是《民法通则》的延续,也正是这一规则,使得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领域呈开放态势。
不同成长阶段拥有不同程度的理性,看起来,为避免一刀切的僵硬规则压抑成长、限制自由,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自由行为领域有必要作相应动态调整。因而,开放灵活的优点在于:可呼应未成年人的成长态势,亦可帮助未成年人通过渐次放开的私法交往增强理性。问题是,如何在技术上做到规范上的自由程度准确映射事实上的理性程度?这个问题可从另外一个问题的讨论中看到思考方向,即,开放灵活的规则可能带来何等规范效应?
制定法显然无法针对个体给出“相适应”的具体标准,亦因此无法在立法层面准确映射,委诸法官判断便显得顺理成章。因而,灵活规则一个势所必然的规范效应是,法官裁量自由得到极大扩张。《民法典总则编解释》第5条沿《民通意见》思路,为法官裁量何谓“相适应”提供判断准据:“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方面认定。”这些考虑因素乃是对法官裁量的指引,通过指引,法官得到明确的裁量授权。制定法的功能之一固然是制约法官的裁量行为,但民法领域里,法官存在裁量空间事属寻常,因此,泛泛而谈法官的裁量自由,无法笼统做正当性评价。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具体到限制行为能力人行为领域,法官的裁量空间应予严格限制抑或放任无妨?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回到行为能力制度的规范意旨。
行为能力制度的规范意旨,除令理性人对其行为负责外,还在为理性欠缺之人提供保护。守护理性不及的未成年人被称为文明社会的底线,俾免人类社会堕入丛林法则的支配,为此,未成年人保护须以刚性规则支撑,不作利益衡量,不考虑交易安全问题。[39]未成年人保护要求强度如此之高,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本应尽可能予以排除,俾使制定法规则的刚性得到维持。就此而言,《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授予法官裁量权之举,似与制度意旨背道而驰。行使裁量权,在具体个案中给出是否“相适应”的判断,且其判断又须综合考量“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因素,法官所做的,其实就是基于交易安全的利益衡量。这种将限制行为能力相对化的立场,无异于对未成年人绝对保护要求的否认。
问题不止于此。无论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抑或因为法官行使裁量权,未成年人保护失去较之交易安全的优先性,都发生在法律行为实施完毕纠纷发生之后,此时,无论法官作出何种裁断,均属事后审查。事后审查与救济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损害均可通过事后救济的方式弥补。一种可能是,法律行为一旦实施,未成年人即已陷入不利境地,事后补救鞭长莫及,例如,未成年人擅将某画作售与他人并交付,买受人不慎损毁,此时,事后的法律救济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复其画,但如果监护人能事先介入,交易也许原本不会发生。事先介入当然不能完全消除风险,纵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也可能思虑不周而作出误判,只不过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即便无法挽回,法律亦无可奈何。在此意义上,将未成年人置于监护人保护之下,并非旨在杜绝对未成年人不利的后果,而是以监护人自身理性弥补未成年人之不足,从而将未成年人理性抬升至完全行为能力程度。为此,监护人的理性考量有必要全程覆盖法律行为的实施,法律则须提供强制性的事先介入机制,让限制行为能力人在考虑是否实施法律行为时即处于监护之下,防止限制行为能力人“自由”踏入交易领域、独自面对不可控的交往风险。受保护与受约束管制本就一体两面,无法自负其责之人,自由也无从谈起。很遗憾,《民法典》的灵活机制恰恰是起到阻碍监护人事先介入的效果。
根据《民法典》第19条但书规定,如果法律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限制行为能力人可自由实施,无须法定代理人同意。然而,年龄不同,理性成熟度不同,不同个体之间,即使年龄相同,实际理性程度亦非一律,加之法律行为类型与复杂程度千差万别,每项法律行为所需要的具体判断能力相去甚远,局面如此复杂,关于如何判断“相适应”的问题,很难期待通过一般交往惯例形成类型化的普遍默会知识,亦难期待缺乏社会经验的未成年人具备此等默会知识,进而知晓其自由行为的界域,即便果真可以知晓,未成年人能否自觉遵守,不越雷池,更是未知之数。这意味着,为了获知某项法律行为是否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行为实施之前须个别判断该项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问题是,由谁判断?法官未得到立法授权不得提前介入个案,剩下无非两种可能:法定代理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自己。
如果由法定代理人判断,未成年人即负有将其行为在实施之前告知法定代理人的义务,否则法定代理人无法事先判断。然而,一方面,法律并未课予未成年人此项义务,另一方面,果若未成年人负有此项义务,行为自由即无从谈起。况且,交由法定代理人判断,无异于要求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因为如果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其判断结果必是不“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如果由限制行为能力人自己判断,疑问则在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为何有此判断能力?逻辑上,一项行为是否可由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交由限制行为能力人自己判断,本身就与限制行为能力制度的规范意旨相矛盾。限制行为能力人若是想要独立实施法律行为,往往意味着,在其判断中,所实施的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因而无需法定代理人介入。因此,结果可能是,越是自以为是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越需要法定代理人费心防范的未成年人,反倒越有可能脱离法定代理人的照管。防范未成年人思虑不周的规范意旨,将因为未成年人的自以为是而落空。未成年人监护属强制性秩序安排,本与未成年人是否愿意接受无关。
既有实证法框架下的应对之道是,当限制行为能力人选择绕过法定代理人独立实施法律行为时,究否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交由法官事后裁量。且不论如前文所述,此属事后补救之道,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即便该事后补救之道本身,亦横生枝节,制造困境。法官裁量结果,可能认定属于“相适应”因而有效,亦可能认定不“相适应”因而须加入法定代理人意志。此意味着,行为实施时,当事人双方均无法确定该行为效力状态系有效抑或效力待定。这种“薛定谔的效力状态”,恐怕无论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抑或正常的法律交往秩序均非有益。
上述分析表明,指望以开放灵活的界限设定,实现限制行为能力人规范上的自由程度准确映射事实上的理性程度,也许只是看上去很美的追求。至少在既有规范配置下,尚有重重疑虑未能得到有效回应。不可否认,限制行为能力人有必要随其年岁增长逐渐扩大法律交往,唯有如此,理性能力才有机会在实际交往中慢慢锻炼成熟。问题在于,除了《民法典》简单粗放的“开放灵活”,是否存在其他方式,既可满足未成年人日益增长的交往需求,又不至于令其独自面对未知不可控的交往风险?对此,德国做法也许具有某种启发。
德国民法典第107条过于僵硬,若限制行为能力人仅受该条规制,无疑有碍其适度参与法律交往并通过适度交往逐渐成长。但这并非限制行为能力人规则的全部。德国民法典第110条的“零用钱条款”虽在实质上仍属事先允许,但较之个别允许已迈进一步,该有限的概括允许通过金额与用途控制,既予限制行为能力人一定程度的自主选择余地,又可在法定代理人的事先介入下实现风险总控,不失为二者兼顾的可行之道。仅仅是“零用钱”自然无法满足未成年人的成长需求。在德国民法典第112条的独立经营之许可与第113条雇佣劳动之许可规则下,未成年人的法律交往得到进一步放开,从“零用钱”的偏于消费而进入生产经营领域。同时,鉴于独立经营与雇佣劳动风险大增,为慎重计,这两个领域除须经法定代理人事先概括允许外,还须置于监护法院的监督之下,甚至在法定代理人怠于授权时,为未成年人利益计,可由监护法院越过法定代理人代为许可。而一旦得到概括允许,未成年人即在被允许范围内拥有完全行为能力。如此,未成年人的自由发展与交往风险控制均得到较为周密的考量,法定代理人的监护亦全程在线,制度设计可谓煞费苦心。
不过,即使认为德国规范方式较稳健、体系较融贯,亦未必意味着可植入我国规范体系。规范技术的移植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配备支撑技术运行的制度环境与理念。我国疆土面积与人口数量均远超德国,法治化、国民教育、城市化、经济发展程度与均衡度等方面则远远不如。这种制度环境下,至少在独立经营与雇佣劳动方面,德国规则恐将水土不服。例如,农民工是我国持续多年的普遍现象,当辍学的未成年子女想要外出务工时,若需要父母允许,难免令人怀疑,一直生活在农村甚至目不识丁的父母有何能力看到其中利弊与风险?其同意与否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有何意义?虽然这种怀疑多少误解了监护制度的本旨,无意中误将监护人的知识能力纳入监护要件,但至少看起来现实如此,并且该现实似乎得到普遍认可。如果制度设计以之为前提,则易于将其正当化。《民法典》第18条第2款复制《民法通则》的劳动成年制,正是可用于正当化该现实的规则。劳动成年制中,进入劳动领域之前的法定代理人允许固然未见体现——此意味着未成年人在进入劳动领域之初便已脱离监护,立法者似乎还进而认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既然有能力通过劳动自食其力,除该劳动领域之外的其他各方面心智必亦成熟至成年人程度,因而慷慨地顺水推舟,索性彻底予其完全行为能力。如此千方百计令未成年人趋于成年的规范方向与理念,与第19条的开放灵活立场倒是体系融贯,而与德国反向而行。
基于上述讨论,立足我国实证法给出的局限条件,本节副标题所提出的未成年限制行为能力人自由行为界限应如何设置之问题,核心在于:假如关于未成年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范方向和立法理念不可转变、开放灵活的立场必须坚持,制度设计上,如何确保限制行为能力人能得到充分监护,以免触碰文明社会的底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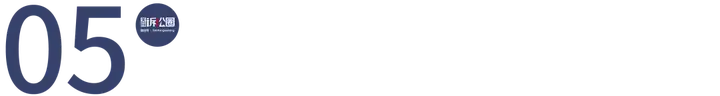
权利变动的迷雾:如何解释法典关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立场?
依法律行为的权利变动是私法交往常态,亦是私人实现自治的基本手段。《民法典》第133条是关于法律行为的立法定义:“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照此定义,是否有必要依所涉民事法律关系之不同区分不同的法律行为?例如,旨在设定义务与旨在变动既有权利的意思表示是否对应不同的法律行为?换言之,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分类是否有意义?负担行为是指负担义务(债务),处分对象则包括一切可让与的财产权,其中又以物权为典型,因此,这一问题可置换为:物权行为是否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中国法应否及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问题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单纯的理论之争不必在此展开,民法典既出,直面我国实证法的规范立场也许别具意义。对此,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未提供足够的线索,须进入债法与物法的规范丛林。最能体现物权行为规范立场的,莫过于所有权移转问题。本节即围绕“买卖契约产生何种效力”与“所有权如何移转”两个子问题,在规范解释中寻访民法典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踪迹。
关于买卖契约,《民法典》第595条作有立法定义:“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与台湾地区“民法”第345条第1项(“称买卖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移转财产权于他方,他方支付价金之契约。”)相较,实质差别在于,《民法典》第595条缺少“约定”二字。台湾地区“民法”认可物权行为,其买卖契约定义中的“约定”一词可相应解释为指向债法义务。由此反推,《民法典》第595条似乎表示,买卖契约可直接导致所有权移转,不必另行求诸物权行为。不过,这只是似乎而已。作为立法定义,第595条属于描述规范,具体法律效果须待填补规范进一步阐明,第598条即是其中一项填补规范。根据第598条,出卖人负有向买受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此意味着,该项义务得到履行之前,所有权不会因为买卖契约而发生移转;亦意味着,第595条的表述即使不谓之错误,至少是有欠严谨。
解释不是唯一的。日本民法典第555条(“买卖,因一方当事人约定移转某财产权至相对人,相对人约定对之支付价款,而生其效力。”[40])关于买卖契约的立法定义含“约定”二字——此类似台湾地区“民法”;但关于物权变动立场,日本通说并不认可物权行为——此不同于台湾地区“民法”,其民法典第176条(“物权之设定及移转,仅因当事人之意思,生其效力。”)之“意思”,被解释为债权意思而非物权意思,故买卖契约直接发生所有权变动效果。[41]这似乎表明,立法定义有无“约定”二字,与物权变动立场并无必然关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日本民法典,出卖人所负义务并非移转所有权,而是“对买受人,负有登记、注册及其他使买卖标的权利之移转具备对抗要件之义务”(第560条),相应的,不动产登记(第177条)与动产交付(第178条)均属物权变动之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我国《民法典》无论在出卖人义务设定,还是登记、交付的效力方面,均与日本不同,《民法典》第595条及相关法条之解释,自然难以比附。
逻辑上还存在一种可能,即,买卖契约具有双重效果:既发生债法给付义务,又直接导致所有权变动。如此,第598条所填补的,可认为只是买卖契约其中一项效果,所有权变动之效果未必遭到排斥,第595条与第598条的裂隙亦得到弥合。不过,难题依然存在。首先,如果一方面令买卖契约直接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效力,另一方面却以第598条要求出卖人负有“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出卖人如何履行这一义务?其次,法律行为之区分,关键即在法律效果,将负担义务与移转权利两项截然不同的效果计为同一行为,同样是在逻辑上显得牵强。更直接的解释难题来自于规范体系。根据《民法典》第597条第1款,出卖人无处分权并不影响买卖契约的有效性。在此前提下,如果坚持认为买卖契约包含处分效力,唯一的解释路径,恐怕就是运用法律行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将作为整体的买卖契约拆分为负担部分与处分部分,再将第597条第1款之“合同”限缩为“合同的负担部分”。但此亦意味着,买卖契约的负担部分与处分部分各有其有效要件,法律命运也互不影响。问题因而在于,买卖契约的“负担部分”与“处分部分”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均有不同,以之为一项行为的两个部分或承认其为两项行为,何者更为妥适?
当然,即便认可买卖契约仅具负担效力,亦不表示《民法典》因此承认物权行为。买卖契约仅生负担义务只是表明,该契约不足以导致所有权发生变动,至于如何变动所有权,在逻辑上则包含法律行为与非法律行为(如事实行为)两种可能。
所有权移转的基本规范见诸《民法典》第209条第1款与第224条,其中,不动产“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动产“自交付时发生效力”。此规定与德国以及台湾地区均有显著不同。德国民法典第873条(不动产基于合意与登记之取得)与第929条(动产之合意与交付)皆明确规定让与合意,作为法律行为的物权行为清晰可辨。台湾地区“民法”未如德国般写入物权合意,但其表述是“非经登记,不生效力”(第758条第1项)及“非将动产交付,不生效力”(第761条第1项),此系必要条件的表达方式,传达的信息是,登记与交付只是物权让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为了表达物权合意亦属必要,2009年修正新增第2项:“前项行为,应以书面为之。”修正理由谓:“……现行条文第七百六十条之‘书面’,究为债权行为,或为物权行为,适用上有不同见解,爰增订第二项,并将上述第七百六十条删除。……至以不动产物权变动为目的之债权行为者,固亦宜以书面为之,以昭慎重;惟核其性质则以于债编中规定为宜……并此叙明。”[42]显然是以“书面”的要求确认物权合意之存在。反观《民法典》,无论“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抑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皆是充分条件式表达,不动产变动更增加一句“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从而构成充要条件的逻辑闭合。这容易让人理解为,物权变动,需且仅需登记或交付即可完成。由于登记与交付并非法律行为,故可认为,物权变动非物权行为所致。
不过,称仅需登记或交付即可完成物权变动,可能遭遇实证法上的解释难题。例如,根据《民法典》第598条,出卖人负有“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以“并”字连接,说明交付与移转所有权系两项不同的义务,亦说明,仅仅是履行交付义务,不足以导致所有权移转,况且其他诸如不动产所有权变动、租赁契约的履行等交易均存在交付,却均与移转所有权无关。可见,交付并非物权变动的充分条件。再如,根据《民法典》第597条第1款,出卖人未取得处分权无法移转标的物所有权,此意味着,处分权影响所有权移转的有效性,可是,如果物权变动并非法律行为的结果,处分权如何施加影响?
至此为止,从《民法典》上述各项规范中可获知的信息是:所有权移转之效果,解释为第595条字面显示的系买卖契约效力所致,固然存在规范冲突,解释为第209条第1款与第224条字面显示的登记或交付所致,规范体系亦无法融贯,而物权变动合意又似乎未体现或者说至少未直接体现于实证规范。然则所有权如何移转?
奥地利进路也许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方向。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380条规定:“缺乏名义(Titel)或法定取得方式(rechtliche Erwerbungsart)者,不能取得所有权。”此系罗马法上经典的“名义+方式”(titulus-modus-Lehre)权利变动模式。[43]该进路提示:单独的买卖契约(名义)或单独的登记或交付(方式)均无法导致物权变动,物权变动系二者合力的结果。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053条正是这模式的直接运用:“通过买卖契约,物以一定数额金钱为对价移转于对方。如同互易,买卖契约系所有权取得之名义,该取得须经买卖标的之交付。交付前,所有权属于出卖人。”
不过,于我国实证法而言,奥地利之路未必是坦途。首先,“名义+方式”模式下,作为名义的买卖契约亦具处分效力,故出卖人的义务如日本般同样不包含移转所有权。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061条规定:“出卖人负有交付前谨慎保管标的物之义务,并有义务依上述关于互易(1047条)之规定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与日本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以登记、交付为对抗要件,奥地利则以之为生效要件。而如前述,移转所有权乃是我国《民法典》第598条为出卖人确立的两项主给付义务之一,若在物权变动问题上随奥地利进路,规范冲突势所难免。其次,1811年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虽采罗马法经典权利变动模式,但随着潘德克顿法学影响日隆,其物权变动立场逐渐发生转向,时至今日,奥地利通说已承认独立物权合意(dingliche Einigung)之存在。[44]如此,欲借助奥地利立场而否认物权行为,恐难如愿。再次,奥地利“名义+方式”的模式为法典明文规定,我国则不仅未专设相当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380条的规范,《民法典》第209条第1款与第224条亦未显示买卖契约的“名义”地位,其充分条件式表述甚至具有排斥效果,因此,引入“名义+方式”的解释模式是否有足够的规范基础,值得怀疑。这一疑虑又引发更一般的解释疑问:如果实证法既未直接规定物权合意之存在,又未明文规定物权变动奉“名义+方式”立场,解释时,应如何认定实证法的态度?
民法典的功能之一原本在于整合实证法规范,使之体系融贯,但在所有权移转问题上,遗憾的是,纳入观察的规范越多,冲突便越大,解释选择也越困难。
例如,《民法典》第641条第1款规定所有权保留:“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既称“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依字面文义,应指所有权移转效果系买卖契约所致,或买卖契约至少发生影响,否则不必且无法通过买卖契约保留所有权。但如果买卖契约产生处分效力,不仅如上文所述,与第598条出卖人的所有权移转义务和第597条第1款不以处分权为有效要件相冲突,且难以解释买卖契约处于何种效力状态。申言之,如果所附停止条件用以控制买卖契约,条件成就前,买卖契约尚未生效,如何解释买受人因买卖契约而生履行义务?如果所附停止条件仅用来控制买卖契约中的所有权移转部分,由此创造买卖契约部分未生效状态,引发的疑问则又如上文所述,负担与处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力,将其视为统一行为的两个部分抑或两项不同行为更为妥适?
再如,《民法典》第311条第1款将“以合理的价格转让”设置为善意取得的条件之一。由于价格因素只存在于买卖契约,该条件是否意味着买卖契约制约所有权移转、因而具有处分效力?抑或如德国学者所解读的,在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格局下,合理的价格并非善意取得之独立要件,而只是善意的判断因素?[45]《民法典物权编司法解释(一)》第20条进而要求,善意取得须以“转让合同”有效且未被撤销为前提。所谓“转让合同”,如果指的是直接移转所有权之物权合同,该合同除得以善意补足处分权之欠缺外,不得存在其他效力瑕疵,此乃题中之义;若被用以指称买卖契约,则意味着,买卖契约之有效是善意取得的前提,而这一规范立场,可同时与买卖契约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买卖契约+登记或交付发生物权变动及物权行为有因性数种物权变动模式相呼应。换言之,单就善意取得规范而言,各种物权变动立场似均有腾挪余地,然则规范适用时应作何种解释选择?
“转让合同”概念所构成的解释难题也许有必要略作展开。涉及权利变动时,这一概念究竟指称买卖契约抑或直接变动物权之物权契约,一直模糊难辨。《民法典》物权编未直接使用转让合同概念,与之最为相关的是第215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语法结构上,本条出现三次的“合同”所指皆一,均系“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如果其中转让情形可简称为转让合同,所转让的不动产物权是所有权时,此处所指应是买卖契约。不过这未必表明,物权编司法解释第20条的“转让合同”应作同一解释。例如,如果第20条的“转让合同”指买卖合同,是否意味着第14条第1款(“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定受让人为善意。”)之善意判断时点应以买卖契约订立之时为准?第17条第1款(“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所称的‘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指依法完成不动产物权转移登记或者动产交付之时。”)又该如何理解?况且,即使作同一解释,如上文所言,亦存在否认物权行为及肯认(有因)物权行为数种可能。
另外一个与转让合同概念相关、用法同样未必清晰一贯的概念是“无权处分合同”。这个概念一般用来指称《民法典》第597条所规制的合同。最高法院2022年11月4日公布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0条系《民法典》第597条的释文,其条旨即是“无权处分的合同效力”。该条第1款的内容是:“转让他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或者真正权利人仅以让与人在订立合同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表面上看,“无权处分合同”含义清晰: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问题是,无处分权人订立的什么合同?逻辑上,如果强调订立合同时无处分权,即意味着该合同属于处分行为,并且处分权之欠缺对处分行为的有效性构成影响,这显然是直接变动权利的物权行为。但该条第1款与《民法典》第597条也显然不是在此意义上使用“无权处分合同”概念,否则无法理解为何缺乏处分权不影响“合同”的有效性,更可能的是,无权处分合同被当作“(无权)转让他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订立的合同”即“无权转让合同”(“转让他人之物的合同”)的同义概念。“转让合同”概念本就充满疑义,如今再以“无权处分合同”作为“无权转让合同”的同义概念,语词密林愈加迷雾重重。例如,既然处分权不影响该合同的有效性,为何将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称为无权处分合同?为履行此买卖合同而旨在移转该无处分权之物所有权的行为如何表述?结合转让合同概念,既然买卖合同不产生所有权让与的效力,为何将买受人与出卖人分别称为受让人与让与人(转让人)?在所有权让与的法律关系层面,又以何种称谓指称当事人?
至于备受瞩目的《民法典》第215条,管见以为,似难为任何一种物权变动立场提供支持,因而意义有限。原因在于,无论日本进路、奥地利解释转向前后的两条进路抑或德国进路,均不否认“买卖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买卖合同有效性”这一近乎自明的命题。申言之:日本法上,未办理物权登记,无非是当事人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不能对抗第三人而已,买卖契约的有效性不受任何影响;于奥地利而言,未办理登记仅仅意味着不动产物权因未满足“名义+方式”之“方式”要件而无法变动,无论其物权变动的解释路径是否发生转换,登记之阙如均与作为“名义”的买卖契约有效性无关;至于德国,由于采行物权行为理论,作为负担行为的买卖契约与作为处分行为的物权契约,其各自有效性本就分别观察,即使需要运用抽象(无因性)原则,讨论的也只是作为原因行为的买卖契约是否影响物权契约的有效性,而不是反过来,讨论物权契约是否影响买卖契约的有效性,更不会讨论作为物权行为生效要件的登记是否影响买卖契约这一债权行为的有效性。
权利变动是市场运行的关键节点,亦是民事财产法的贯通之道。本节仅以涉所有权让与法律关系为例的分析信已表明,无论采取何种解释进路,《民法典》关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规范设置均未臻体系融贯之程度。笔者无力透过我国实证法之迷雾看清前路,本文所能做的,无非是简笔勾勒迷雾之轮廓,至于如何拨云见日,唯俟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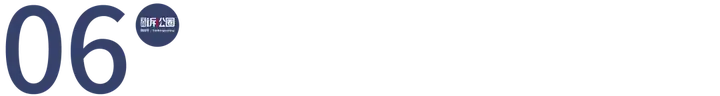
分裂的错误规则:如何建构融贯的二元论或一元论错误规则体系?
私法自治要求各人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即便出现失误,亦须承受其代价,不得将风险转嫁他人。但另一方面,理性毕竟有限,百密难免一疏,如果将错就错是唯一选择,私人获得自治的同时,将失去试错机会,此无异于追求永不犯错的无限理性。试图处理这一矛盾的,是错误制度。错误制度的要旨在于利益平衡:既为错误人提供纠错机会,又不至于辜负相对人的信赖。与之相应,“何种错误可被废止?”“如何废止?”与“错误人为废止错误须付出何等代价?”便是错误制度的三个关键问题。其中尤以第一个问题最为核心,它不仅制约着后两个问题的回答方向,更在整体上塑造实证法错误制度的基本构架。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围绕第一个问题略作展开。
关于何种错误可被废止,各国实证法与国际公约上主要有两条进路,切入点分别是意思表示的内容和对方当事人在错误中所扮演的角色。[46]就思考逻辑而言,前者从意思表示本身出发,旨在回答“意思表示发生何种错误可被废止”之问题,后者则从相对人信赖保护出发,对应的设问是“何种情况下相对人(不)值得保护”。这看似意思表示理论中偏重表意人真意的意思主义与偏重相对人信赖的表示主义的结果,但其实不然。进路一可能因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不同侧重而采不同规范构造,进路二亦无妨披上意思主义外衣。具言之,进路一之下,如果采取纯粹的意思主义立场,逻辑上,意思表示发生错误时,因其未表达真意而应归于无效,契约亦因隐藏的不合意而不成立,此即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规定之所由。[47]当德国民法典放弃第一草案立场,更以法律行为生效但可撤销时,即意味着认可合意之存在,并在此前提下寻求表意人与相对人的利益平衡,表示主义的考量清晰可见。进路二则因其同时关注契约双方对于错误发生的影响,目光必然在表意人真意与相对人信赖之间流转权衡。更具说明价值的是,普遍采进路二的国际公约,在规定意思表示解释时,多以探求当事人双方共同理解及表意人真意为要,唯在探求无果时,始得寻求一般理性人之通常理解。[48]此解释规则,很难说是表示主义立场贯彻的结果。可见,以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的对立为两条进路贴标签,难免过于简单化。撕去标签,观察两条进路下的规范构造逻辑也许更具意义。
规范构造上,进路一可称二元论,其显著特点在于,根据意思表示形成与表达阶段区分动机错误与内容(表示)错误,并原则上排除动机错误对于法律行为有效性的影响。[49]二元论系罗马法契约实质内容(essentialia negotii)标准之延续,构成实质内容的,一般包括契约性质、标的物、缔约人、数量等契约各项要素,代表性立法为意大利民法典与西班牙民法典。[50]但仅仅从契约要素角度作静态观察,粗糙而机械,难以甄辨错误存在于意思表示形成抑或表达阶段。德国民法典亦是二元论代表,不同的是,规范技术上,德国民法典未采传统强调契约(法律行为)要素之界定方式,而是直接在行为动机与表示行为二分框架下,以第119条第1款明确规定唯有表示行为自身错误方可撤销,并以第2款将“交易上视作重要的人或物的性质”之动机错误视为内容错误,以此缓解二元划分的僵硬性。
二元论虽逻辑清晰,却并非无懈可击。时至今日,如何准确鉴别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意思表示内容究应具体至何种程度(尤其是关于当事人和标的物等构成法律关系要素的性质指涉应具体至何种程度)、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二分格局下如何界定错误、何种动机可例外影响法律行为有效性等问题,仍是二元论备受质疑之点。欲要避开此类难题,最彻底的办法似乎是釜底抽薪,否弃二元论本身。此正是一元论的努力方向。
二元论的基础之一是意思表示的心理过程分析。[51]一元论在判断错误对于法律行为有效性影响时,就心理过程是否能准确观察并对应于法律效果表示高度怀疑,遂不再分辨意思表示的形成与表达阶段,而作一体规制。不过,对心理分析正当性的质疑,未必足以否认意思形成与表达两个阶段的区分,因为真正体现心理分析的,只是行为意思(Handlungswille)、意图(Absicht)及动机(Motiv)等内心意思的分层操作,而意思表达本身是一个可外部观察的现象,表达之前即可归入形成阶段。在实效上,通过两个阶段的区分,二元论原本具有阀门效应,将未进入表达阶段的错误阻隔于外,从而降低错误风险转嫁于相对人的可能性。若仅将阀门拆除,必然涌入大量需要考量的错误,加之形成阶段的错误较之表达阶段更难认知,若无差别一概准许撤销,将极大增加相对人的交往风险。为此,一元论把关注目光从表意人转向相对人,以相对人的可归责性确立风险承担的正当性,重建风险阀门。
一元论多见于国际公约,如国际商事契约通则(PICC)、欧洲私法共同参考框架草案(DCFR)、欧洲共同买卖法(CESL)、欧洲契约法通则(PECL)等。以欧洲契约法通则第4:103条为例,可撤销的错误,其要件包括:第一,错误不必存在于表示行为中,仅需订立契约时存在事实或法律错误即为已足,但如果错误在特定情境下不可原谅或者错误风险为交易本身或特定情境所内含,则不在此限;第二,错误或者由相对人所提供的信息引发,或者为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并且该错误将致交易有悖诚信与公平,或者相对人犯有相同错误;第三,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若错误人知悉真情,不会缔结契约或以如此条款缔结契约。[52]通过可归责性与相对人的认知可能,一元论以相对人信赖保护的正当性反求错误的可撤销性,为错误风险的承担重新建起不同于二元论的阀门机制,又因其将判断标准外在化,避免了二元论判断动机与内容的难题,看起来,可操作性与确定性均得到提高。不过,一元论带来的疑虑亦不可忽视。
首先,判断标准的外在化其实并未消除难题,更多只是转移难题。一元论下,法官得以摆脱动机与内容的判断难题,但需要额外判断相对人行为与表意人错误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因果判断之引入,很难说在何种程度上降低了法官工作的难度系数,尤其是未进入表达阶段、仅存在于内心的错误亦在撤销之列,此时判断因果关联更为棘手。
其次,即使在可操作性与确定性上,一元论亦未必有多大程度的实质提升。意思表示唯有通过表达方可固定,但由于形成阶段的意思错误亦在考察之列,为了确定何种错误终将影响法律行为有效性以及最终的因果关联,判断时,应对意思表示从形成到表达的整个过程作通盘考察。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审查范围的扩张,更有意思形成阶段存在于表意人内心的各种不确定性,以及表意人何种内心思虑为相对人所认知。而在二元论下,法官原则上仅需关注表达于外因而得以固定的意思表示,不必涉足表意人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
再次,由于一元论将意思形成与表达两阶段合并一体观察,为了保证最不确定的情形亦可作出是否符合法定构成的判断,关注重心不得不前移至意思形成阶段。结果是,意思形成阶段的动机错误成为规范原型,本属典型规制对象的内容错误反倒成为例外。此举近乎本末倒置。[53]因为,效力瑕疵因素存在于行为自身原本是题中之义,二元论将关注焦点集中于表示行为,所体现的,正是这一题中之义。
最后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以相对人的可归责性作为错误可撤销的要件,将改变错误制度的功能定位。二元论的错误制度旨在为单方错误提供改正机会,在此基础上令错误人承受改正错误的代价,以平衡相对人信赖利益;一元论则是将错误人的救济建立在相对人可归责性的基础上,相应的,错误人之享有撤销权便成为相对人不当行为的制裁手段。功能定位之改变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错误制度的构建:第一,在相对人不具有可归责性的情况下,错误人原则上将失去改正错误的机会,例如,写错、说错等单方表示错误原本属于典型的可撤销情形,但一元论下,由于相对人不具有可归责性,此类错误难以通过撤销而废止。显然,一元论对理性的审慎提出更高要求,在容错率较低的商事交往中或可有其正当性,此亦可部分解释,为何一元论盛行于以商事契约尤其是国际商事契约为原型的国际公约;与之相对,二元论则以普通民事交往为规范原型,容错率较高。[54]由此引发的思考是,民商分立体制下,民法固以普通民事交往为规范对象,然则民商合一的法典,其规范原型应设定为民事交往抑或商事交往?第二,如前所述,二元论下,错误人享有撤销权乃是实证法对其单方错误的宽容,相应的,错误人亦须承担改正错误的代价,以免向相对人转嫁风险,此代价即是,就相对人因撤销所受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且不以过失为要件。一元论逻辑中,错误人之所以享有撤销权,系因相对人可归责所致,因此,错误如同受欺诈胁迫,撤销权人亦是损害赔偿请求权人。[55]第三,进而,除撤销权的配置外,一元论错误制度与欺诈制度在整体上都将变得界限模糊。[56]尤其是,一元论所强调的相对人不当影响,若属故意,构成错误的同时往往也满足欺诈要件。在二元论看来,错误规则原本用以矫正不真实意思表示,欺诈规则则对意思表示不自由提供救济,二者在当事人救济的正当性及与之相应的撤销权的配置、撤销期间的设定、损害赔偿义务的界定等各方面均相去甚远,不容混淆。
二元论与一元论尺短寸长,对“何种错误可被废止”问题给出的答案均未臻完美。在二者之间作出高下评判已然不易,超乎二者创制新规更难之又难。不过,如同上节“权利变动的迷雾”所显示的,我国实证法的首要障碍,恐怕既不在于判断何者较为可采,更非检验规则创新是否作出了实质改进,而是无论采行何种立场,如何了解其基本脉络并作相应逻辑一贯的表述,以免法律解释与适用陷入概念泥淖。
《民法通则》以来,我国实证法上表述错误的法定术语一直是“重大误解”,并且损害赔偿奉过错归责主义,就此而言,我国错误制度自发轫之初即带有一元论烙印,游走在二元论与一元论之间。
过错归责之损害赔偿立场,其规范逻辑较接近一元论,已如上述。关于术语选择,如果区分意思形成与表达两个阶段并以表达阶段为规制重点,错误制度的关键即在“错误表达”,而非“错误理解(误解)”。在“基于误解而作出意思表示”与“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两个表述中,前者侧重意思形成阶段的“错误理解”,后者则是意思表示本身发生错误的直观表达。这意味着,“误解”一词将错误的规制起点前伸至意思表示形成阶段,较适于表达一元论立场。不过,单独的语词本身不能提供太多信息,真正重要的,是语词指向的法律规则。
《民法通则》第59条第1款将误解对象定位为“行为内容”,《民通意见》第71条对“重大误解”的含义作具体化解释时,一方面通过列举“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行为要素界定“行为内容”,另一方面增加“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之描述,突出意思表示与法律效果的错位,并且仅以错误人单方因素为要件,相对人因素则未作考虑。若以二元论或一元论贴标签,此规范逻辑显然较偏于二元论,或者说,以解释为二元论为宜。相应的,学者普遍忽略“误解”一词的一元论用法基因,在可撤销性的判断上,直接在二元论的脉络下接引德国错误制度。
《合同法》第54条第1款未沿用《民法通则》的表述,改称“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这一表述较符合“误解”的惯常用法,咬文嚼字的话,所表达的是,受规制的是“因误解订立的合同”,而非“订立的错误合同”。这一微妙的措辞变化,似乎表明立法者有意无意将错误制度改造为一元论构造。不过,也许部分是因为除这句语焉不详的表述外,实证法并未构建与一元论相呼应的规则体系,[57]关于重大误解的含义界定亦依旧沿用《民通意见》,所以,学理解释几乎未受影响,仍以二元论阐述我国错误制度。结果,裂缝不仅未消除,反倒因为《合同法》的措辞变化而有所放大。
作为新一轮也是规模最大一轮的制度重构,《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原本有机会弥合裂缝,很可惜,机会再次擦肩而过。《民法典》第147条的表述是:“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语用逻辑与《合同法》一致。最高法院制定《民法典总则编解释》时,2021年11月21日最后一次征求意见的专家讨论稿包含两个方案。方案一关于重大误解的解释是:“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和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且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误解。”方案二则除此之外增加一款:“行为人存在重大误解,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行为人主张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一)相对人导致该错误认识发生的;(二)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存在错误认识,仍然促使该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三)行为人和相对人存在相同错误认识的。”方案二增加的该款内容乃是盛行于国际公约的一元论表达,此可看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朝一元论方向重塑我国错误制度的努力。不过,司法解释关于重大误解的含义界定乃是《民通意见》二元论脉络的延续,聚焦于行为内容,而如前文所述,一元论以意思表示形成阶段的动机错误为规制原型。此意味着,若方案二得以采行,二元论与一元论在我国实证法中的裂缝将在司法解释的同一条以公开化的形式呈现。最终定案采行方案一,《民法典》第147条的隐晦一元论因而与总则编司法解释第19条的粗糙二元论继续“和平共处”。分裂状态何时消除、以何种方式消除,笔者无法预知。
结语
本文选取的六个问题,分别涉及总则编所折射的法典体例、权利基本理念、主体架构基本逻辑以及三项法律行为制度,重要性见仁见智,亦未必属于民法总则中最难求解的问题,兼之多属中国制造,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意义更是值得怀疑。予以讨论,更多是笔者基于自身困惑的自我追问。敢于献曝,无非抛砖引玉而已。学术分歧在所难免,笔者唯一担忧的是,如果我们的学术思考总在概念浑沌逻辑混乱的泥淖中挣扎,所谓学术进步与创新,恐怕不过是自娱自乐的幻像。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希尔伯特这句名言镌刻在他的墓碑上伴其长眠。在这句名言里,人类永续不竭的探索精神与高度的理性自信被表述得坚定而乐观。求知探索与理性思维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只不过,具体到兼具普世性与地方性特点的法律文明,是否真能“必将知道”,似乎未必如此乐观。
注释:
[1] 参见〔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下册)》,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66-467页;朱庆育:《民法总论》(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35页。
[2] Schweizerisches Civilgesetzbuch: Erläuterungen zum Vorentwurf des Eidgenössischen Justiz-und Polizeidepartements, 1902, S.22f.
[3] 本文瑞士民法典译文系笔者据其德文本自译。
[4]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初版序”,第1页。
[5] 同上注,第121页。
[6] 本文奥地利普通民法典译文系笔者自译。
[7] 详参朱庆育:《第三种体例: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总则编》,《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第83-89页。
[8] 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4页。
[9] 本文德国民法典译文系笔者自译。
[10] Hans Brox/Wolf-Dietrich Walk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45.Aufl., 2021, §32 Rn.2; Dieter Medicus/Jens Petersen,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1.Aufl., 2016, Rn.130; Jörg Neu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2.Aufl., 2020, §20 Rn.79.
[11] Brox/Walker, a.a.O., §32 Rn.3.
[12] Brox/Walker, a.a.O., §32 Rn.3.
[13] Medicus/Petersen (Fn.10), Rn.136ff.; Astrid Stadl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20.Aufl., 2020,§7 Rn.2.
[14] 参见(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缪黑埃·法布赫-马南:《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03-705页。
[15] 同上注,第726页以下。
[16] 参见(德)莱因哈德·齐默曼、(英)西蒙·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17] 同上注,第25页;另见(德)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谢怀栻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18] (瑞)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页。
[19] 同上注,第95、98页。
[20] 同上注,第97-98页。本文参照德文本对个别术语的翻译表述略作调整:Bettina Hürlimann-Kaup/Jörg Schmid, Einleitungsartikel des ZGB und Personenrecht, 3. Aufl., 2016, Nr.264f.
[21] 王泽鉴:《民法总则》(2022年重排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印刷,第573页。
[22] 参见王泽鉴:《诚信原则仅适用于债之关系?》,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页。德国民法典颁行不久,学界即掀起一场关于第242条的激烈争论。支持者称之为“帝王条款”(königlicher Paragraph),反对者则斥其为“以最恶毒的方式吞噬我们法律文化的致命祸根”。如今,争论基本已尘埃落定。学者意识到,第242条既没有尊贵到“帝王条款”的地步,亦远非“致命的祸害”,不过是提供一种通过法官补充与发展法律的渠道。莱因哈德·齐默曼、西蒙·惠特克(主编),见前注16,第12-14、24页;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G·莱塞,见前注17,第148-150页。
[23]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6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282页;王利明:《民法总则》(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77页。
[24] 王伯琦:《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地区“国立编译馆”1979年版,第240页。另见,施启扬:《民法总则》(第8版),台湾地区自版发行2009年版,第428-429页;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8页;郑玉波著,黄宗乐修订:《民法总则》(修订11版),台湾地区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572页。
[25] 史尚宽,上注,第714-716页、718页;施启扬,上注,第428页;李宜琛:《民法总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26] 王泽鉴,见前注21,第565页。
[27] 参见郭锋等:《〈关于适用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22年第10期,第39页。
[28] Ernst Wolf, in: Ernst Wolf/Hans Naujoks, Anfang und Ende der Rechtsfähigkeit des Menschen, 1955, S.83ff.
[29] Karl Larenz,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7.Aufl., 1989, S.92.
[30] 王泽鉴,见前注21,第121页。
[31] Dieter Leipold, BGB I: Einführung und Allgemeiner Teil, 10.Aufl., 2019, §30 Rn.8.
[32] Medicus/Petersen (Fn.10), Rn.1048.
[33] 王泽鉴,见前注21,第121、123页。
[34] 2021年11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民法典总则编解释(讨论稿)》专家研讨会,此系该司法解释颁布前的最后一次专家研讨会。该讨论稿第5条分三款对胎儿损害赔偿问题予以单独规定:“(第1款)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父母在胎儿出生后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主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第2款)前款情形下,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起诉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父母代为申请保全,或者因追索医疗费用等代为申请先予执行,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裁定先予执行;有关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事实需要在胎儿娩出后才能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中止审理。(第3款)胎儿娩出时为死体,有关当事人请求胎儿父母返还利益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为治疗和保障胎儿正常发育,侵权人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支出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合理费用以及父母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除外。”对此规定,与会专家多数表示反对。正式颁行的司法解释将该条删除,胎儿利益保护问题仅保留第4条。此可略窥最高法院的基本立场。
[35] Bernd Kannowski, in: J. von Staudingers Kommenetar zum BGB, 2013, Vorbem. zu §1 Rn.3.
[36] Dieter Schwab/Martin Löhnig, 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 20. Aufl., 2016, Rn. 153.
[37] 关于团体的权利能力构造,汉语法学中采类似分析进路者,亦见费安玲等著:《民法总论》(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页(吴香香)。
[38] Reinhard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4.Aufl., 2016, Rn.1021; Brox/Walker (Fn.10), §12 Rn.26; Medicus/Petersen (Fn.10), Rn.579; Neuner (Fn.10), §34 Rn.42; Stadler (Fn.13), §23 Rn.24.
[39] Brox/Walker (Fn.10), §12 Rn.2; Medicus/Petersen (Fn.10), Rn.552; Neuner (Fn.10), §34 Rn.8.
[40] 本文日本民法典译文引自王融擎编译:《日本民法:条文与判例》(上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
[41] 典型判例如:昭和33年(1958年)最高法院判决:“以属于出卖人所有之特定物为标的的买卖中,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其所有权应于将来移转时,所有权径直移转至买受人。”昭和35年(1960年)最高法院判决:“不特定物买卖中,若无特别情事,所有权在标的物特定时移转至买受人。”同上注,第150页。
[42] 黄荣坚、许宗力、詹森林、王文宇编纂:《月旦简明六法(第26版)》,元照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叁-63页。
[43] Christian Holzner, in: Attila Fenyves/Ferdinand Kerschner/Andreas Vonkilch (Hrsg.), Kommentar zum ABGB, 2018, §380 Rz.1.
[44] Erika Wagner, a.a.O., §425 Rz.3; Bernhard Eccher/Olaf Riss in: Helmut Koziol/Peter Bydlinski/Raimund Bollenberger (Hrsg.), Kurzkommentar zum ABGB, 2017, §380 Rz.2, §425 Rz.1; Gert Iro, Sachenrecht, 6. Aufl., 2016, Rz.6/40.
[45] (德)罗尔夫·施蒂尔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新物权法》,王洪亮译,徐杭校,《中德私法研究》2009年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46] Sebastian Lohsse, in: Nils Jansen and Reinhard Zimmermann (ed.), Commentaries on European Contract La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661-662.
[47] Martin Josef Schermaier, in: Mathias Schmoeckel/Joachim Rückert/Reinhard Zimmermann, Historisch-Kritischer Kommentar zum BGB, 2003, §§116-124, Rn.52f.
[48] 例如CISG 8, PICC 4.1, DCFR II.-8:101, CESL 58, PECL 5:101. Stefan Vogen, supra note 46, p.754.
[49] Lohsse, supra note 46, p.661.
[50] Lohsse, supra note 46, p.661.
[51] Schermaier (Fn. 47), Rn.6.
[52] Lohsse, supra note 46, p.657.
[53] 亦见陈自强:《契约错误法则之基本理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74页。
[54]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独具特色。据该法第871条规定,可撤销的错误原则上仅限于内容错误(Inhaltsirrtum),包括表示错误(Erklärungsirrtum)与行为错误(Geschäftsirrtum),动机错误可撤销则属例外,并且相对人的可归责性为要件之一,可归责情形包括错误由相对人引发、错误依其情形于相对人显而易见及相对人未作及时说明三项。奥地利新近学说同时主张,错误人存在过失时,撤销后须对相对人承担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Vgl. Peter Bydlinski, Bürgerliches Recht Allgemeiner Teil, 7.Aufl., 2016, Rz.8/6ff, 8/26;Raimund Bollenberger, in: Koziol/Bydlinski/Bollenberger (Hrsg.)(Fn.44), §871 Rz.1ff.,23.此兼具二元论与一元论特点的规则,在各立法例中似乎对错误人最为严厉。
[55] 例如PICC 3.2.16, DCFR II.-7:214, CESL 55, PECL 4:117。Lohsse, supra note 46, pp.730-733.
[56] Lohsse, supra note 46, p.663.
[57] 亦见翟远见:《重大误解的制度体系与规范适用》,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第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