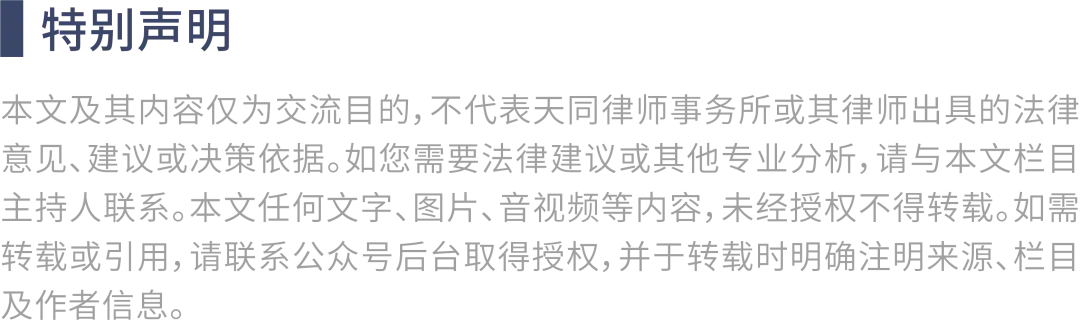文/杨骏啸 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丹丹 天同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姚一纯、余周洋、高西雅 天同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
在报告第二篇上篇开篇给定的案例中,股东甲与股东乙通过签订一份《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股东甲将其持有的A公司股权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乙行使”。两年后双方产生矛盾,甲口头通知乙解除协议,并在A公司召开重大决策事项的股东会议时到会投票,内容与乙的投票相反,双方因此就股东会决议内容和效力产生纠纷。
我们在上篇中,就双方围绕协议产生的表决权行使的可代理性,以及表决权委托与表决权代理之间的关系、表决权委托与表决权代理的效力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详见报告第二篇上篇:协议型一致行动研究报告(二·上):表决权归集——代理模式)。在此基础之上,第二篇下篇将进一步探讨案例中反映的表决权委托的解除与表决权代理的撤回的相关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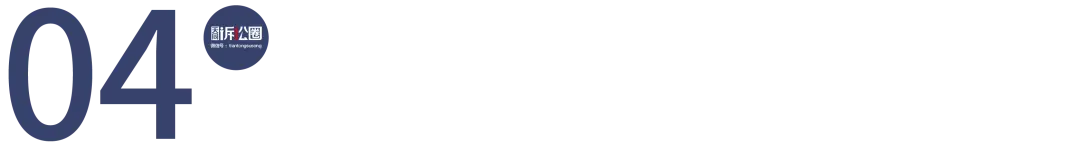
表决权委托的解除与表决权代理的撤回
相较于效力瑕疵,实践中更容易产生纠纷的是表决权委托的解除与表决权代理的撤回问题。
如前所述,表决权委托协议中,当事人往往会约定该委托授权“不可撤销”,意在保障部分股东能够长期稳定地行使其他股东的表决权。而这样的约定,通常会被解读为排除或限制协议的解除权行使、禁止任意撤回代理权。
就此类约定是否能发生相应效果,司法实践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例如,(2021)粤07民终7006号案中,法院认为,即便诉争协议约定了部分股东“将其拥有的股东表决权不可撤销的委托给”另一股东行使,但由于“该表决权委托约定性质上属委托合同关系,在委托方与受托方信任基础动摇或丧失信任的情形下,双方所作出的不可撤销委托的约定显然不具有强制力”,进而认定部分股东得以行使任意解除权。[1]相反,(2021)赣06民终375号案中,法院查明诉争《表决权委托协议书》约定地产公司的股东诸暨公司和张某“不可撤销地授权委托并授予”另一股东黄某行使前者持有的目标公司表决权,且约定诸暨公司和张某“不得再就目标股份行使表决权”,据此,法院认定诸暨公司和张某无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2]
我们认为,要彻底厘清表决权代理模式下基础法律关系的解除权及其排除、代理权的任意撤回及其禁止,仅仅梳理或分析前述司法实践的分歧尚不足够,而是需要回归底层法律构造,分析并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基础法律关系的解除与代理权的消灭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基础法律关系的解除是否直接导致代理权的终止,抑须另行通过撤回的方式取消代理权?
第二,表决权委托作为基础法律关系,是否适用任意解除权规范?
第三,若表决权委托适用任意解除权规范,当事人是否可以通过合意的方式予以排除?
第四,在孤立代理权场合,代理权的任意撤回权能否被排除?
第五,若作为被代理人的协议股东本人到场行使表决权,并且与代理人表决内容存在差异,应如何认定表决内容?
厘清以上问题的分析思路,我们才能回答本篇篇首案例中的问题。以下我们将依此脉络分别展开讨论。
(一)基础法律关系的解除与代理权终止的关系
1.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观察
如前所述,基础法律关系与代理权授予行为的区分原则已被理论学说和司法实践普遍承认(详见报告第二篇上篇:协议型一致行动研究报告(二·上):表决权归集——代理模式)。但存有一定争议的是,在区分原则基础之上,对代理权授予行为应采用无因原则(抽象原则)还是有因原则。若采无因原则,意味着基础法律关系的消灭或终止不影响代理权的存续;相反,若采有因原则,则基础法律关系的消灭或终止,将直接导致代理权的消灭或终止。[3]
就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无因、有因之争,实证法层面自《民法通则》至《民法典》,均未明确其立场。理论学说亦未对此形成通说,支持无因者[4]及有因者[5]皆有之。这两种观点背后的核心差异源于代理行为相对人与被代理人利益保护的衡量与取舍——更应当通过切断基础法律关系与代理权授予行为的联系以保护代理行为的相对人(无因原则)[6],还是更应当肯认基础法律关系与代理权授予行为的联系以保护被代理人(有因原则)[7]。
基于此种利益博弈,部分学者提出了区分说,但区分的方式有所差别。有观点认为应在代理人与相对人的外部关系中采无因原则,而在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内部关系中采有因原则。[8]亦有观点认为,若代理权系通过外部方式授予(被代理人向相对人作出授权意思表示),采用无因原则;若代理权系通过内部方式授予(被代理人向代理人作出授权意思表示),无论是否告知相对人,均采用有因原则。[9]无论是无因说、有因说还是区分说,均有其体系,论理也都较为充分。
司法实践倾向于采用有因原则。例如,(2020)川1303民初383号案中,法院认定王某与建设公司之间《内部承包合同》无效,在此基础上,法院进一步阐明“委托合同的成立并不当然产生代理权,而是被代理人将代理权授予代理人的委托授权行为才产生代理权”,并认定“即便扩张性的将《内部承包合同》视为包含有委托合同的内容和作出了委托授权成立项目部的行为,则所谓‘委托合同’和‘委托授权行为’也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即使存在委托授权行为也属无效授权”。[10]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著的“理解与适用”丛书中的观点认为,由于“无因性理论本身过于抽象的争议和我国民众对授权行为无因性不易接受等问题,《民法总则》并没有规定授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该观点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司法实践采有因原则的倾向。[11]
2.本文以有因原则作为基本立场
综合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本文就代理权授予行为采有因原则,即认为基础法律关系消灭或终止时,代理权亦告消灭或终止。据此,在基础法律关系与代理权授予行为并存的情况下,如果基础法律关系因解除而终止的,代理权同时终止,无须另行撤回。此外,即便采用无因原则,但从商业和生活实践的角度来看,当事人作出解除基础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通常也可以视为其中包含了撤回代理权的意思。[12]因此,本文以下将主要围绕基础法律关系的任意解除问题展开,但考虑到孤立代理权在表决权归集中有存在的可能性,对孤立代理权场合下的代理权撤回问题也将作简要阐述。
(二)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性质决定了任意解除权规范是否适用
司法实践中,在涉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合同解除纠纷中,核心争议焦点往往为一方协议股东是否享有《民法典》第933条或《合同法》第410条[13]规定的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例如,(2017)京01民终4548号案中,法院认为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为双方当事人在“约定了限制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条款”的情况下,委托方是否仍能行使任意解除权。再如,(2020)豫03民终5122号案中,王某请求确认其与投资公司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已解除,法院查明《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王某“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投资公司行使,并对“委托授权标的、委托权利、委托期限、委托权利的行使”等事项作出了约定,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法院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为王某能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行使合同任意解除权”。[14]
司法实践中,若诉争内容与合同相关时,裁判者通常会先认定合同的类型,其目的在于确定裁判所适用的具体法律规范以及适用优先次序。[15]前述案例中,法院均是先将诉争表决权委托协议定性为委托合同,再以此为基础判断当事人是否享有委托合同项下的任意解除权。但是,在协议型一致行动的交易背景下,当事人订立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在性质上是否属于委托合同,不无讨论与反思的空间。此外,无论表决权委托协议性质为何,不应被忽视的是,法定解除权等其他合同解除权亦有一定的适用空间。
1.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性质反思
民法上债的关系,均是建立在主给付义务之上。[16]在潘德克顿立法模式下,民法于立法时,往往会对日常生活、经济活动中频繁发生的主给付义务(给付内容)进行归纳,从而设定不同的典型合同类型。[17]主给付义务是典型合同的最主要特征,通常作为合同类型认定时的核心因素,这在司法实践中亦常有所体现。[18]
委托合同系《民法典》规定的典型合同,《民法典》第919条(委托合同的定义条款)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一般来说,典型合同的定义条款能够反映该典型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就委托合同而言,通常认为委托合同项下的主给付义务(作为特征的给付内容)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人的事务。[19]“处理事务”在文义上具有相当的开放性,甚至可以泛指一切与生活、交易相关的事项,因此委托合同往往承载着“劳务性合同”的兜底功能。[20]司法实践中,“委托采购”“委托理财”“委托投资”“股权代持”等交易所涉合同都常被定性为委托合同。[21]
表决权委托协议作为基础法律关系时,通常约定由部分股东将其享有的公司表决权委托于其他股东行使,若如前所述对“处理事务”作更为宽泛的理解,将表决权委托协议定性为委托合同并无不妥。但是,在表决权归集的商业目的与交易背景下,将表决权委托协议定性为委托合同,也会面临一些挑战。其中最为核心的是,若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受托股东无须服从委托股东之指示,而是可以完全以受托股东自己的想法来行使委托股东的表决权,是否会使双方的权利义务状态背离了委托合同的典型特征,从而影响法律关系的定性。
具体而言,《民法典》第922条第1句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虽然该规定的内容并未被直接吸纳入《民法典》第919条的定义条款,但通常认为这属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当然要求。[22]申言之,当委托人有明确的命令性指示时,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人事务。
然而,在商业实践中,股东为实现表决权归集订立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往往会作相反约定,即受托人无须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行事。例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显示,该公司的股东在《表决权委托协议》中约定,“委托方同意,受托方在依据本协议行使委托股份所对应权利时,可自主决策,而无需再另行征得委托方同意。”
可见,在此类表决权委托协议中,当事人并不意欲由委托人来决定表决权的内容(同意、反对或弃权),而是由受托人独立地、不受委托人指示地行使表决权,这已经完全背离了《民法典》第922条第1句的规定。换言之,在此类表决权委托协议中,当事人实际上并不希望受到《民法典》第922条第1句的约束;甚至,在当事人看来,受托人行使委托人的表决权,相较而言更像是受托人的权利而非义务。以此而言,此类表决权委托协议有可能区别于一般的委托合同[23],属于非典型合同。[24]
此外,如果当事人订立的表决权委托协议还约定,委托方将其表决权委托给受托方行使,而受托方需要向委托方支付一定的价款或给予一定的经济利益,该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法律关系也有可能经由意思表示解释,被认定为表决权的转让而非委托,就此,我们将在报告第三篇中作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虽然表决权委托纠纷通常以诉争协议性质上属于委托合同作为法律适用的基础,但该前提有被挑战的空间。在个案中,若诉争表决权委托协议被认定不属于委托合同,则不应适用《民法典》第933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
2.其他类型合同解除权的适用可能
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原则上需要具备特定的原因,通常由法律规定(狭义的法定解除权)或由当事人约定(约定解除权)。此外,《民法典》在部分条文中设置了任意解除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劳务或服务为内容的典型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以前文所述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为代表),二是以持续履行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除《民法典》第563条第2款[25]的一般规定外,还包括《民法典》第730条[26]规定的不定期租赁合同的任意解除权等)。[27]因此,在涉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合同解除纠纷中,除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之外,法院也可以根据案件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诉辩理由,考察是否存在其他类型的合同解除权。
例如,(2020)豫03民终5122号案中,二审法院虽然否定了委托人王某有权行使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认为受托人投资公司在目标公司某次临时股东大会(代理王某)的投票行为违反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相关约定,导致《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因而王某有权行使《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权。[28]
此外,从检索的案例及公司公告来看,绝大多数表决权委托协议中都约定了委托期限,因此较难适用《民法典》第563条第2款关于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规范。但如本篇开篇给定的案例情形,在当事人未约定委托期限时,该任意解除权仍可能具有一定的适用空间。
(三)作为委托合同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任意解除权的合意排除
1.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合意排除之争议
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是否可以合意排除,近年来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形成的学说及司法实践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否定说(不可排除),二是肯定说(可以排除),三是区分说(按照某种标准区分是否可以排除)。
否定说认为,立法者基于“自由与效率”的价值追求,在部分典型合同中设立了任意解除权以突破合同严守原则,此类解除权系“法定任意解除权”,无论该合同系有偿还是无偿,“法定任意解除权”都不能由当事人合意抛弃。[29]虽然我们检索后发现采用否定说的案例并不常见[30],但值得重视的是,《民法典》施行后,多部具有一定实践影响力的民法典相关丛书的观点持否定说立场。[31]
肯定说认为,虽然部分典型合同规定了任意解除权,但该任意解除权同样属于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原则上可合意排除其适用;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排除任意解除权违背公序良俗的,则应例外地认定不能排除。[32]司法实践亦有采用肯定说者。[33]
区分说则认为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来认定当事人能否合意排除任意解除权,但对于采用何种区分标准,区分说内部亦有不同观点。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应以有偿和无偿作为区分标准——无偿委托合同原则上不得合意排除任意解除权,有偿委托合同反之。[34]还有观点认为应以民事委托和商事委托作为区分标准——民事委托合同原则上不得合意排除任意解除权,商事委托合同则反之。[35]对后续司法实践具有不小影响的(2013)民申字第2491号案即采用了该区分标准。[36]
实际上,不管采用“有偿-无偿”还是“民事-商事”的区分标准,都是在强调应当综合考虑委托合同中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来衡量是否应允许当事人排除任意解除权。[37]在生活往来与商业交易越来越复杂的今日,委托合同往往不再单纯地依托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人身信赖关系,而是有可能兼具甚至更侧重于其他利益方面的考虑或需要,而这同样值得被保护。[38]前述两种不同的区分标准,通过委托合同的有偿属性或商事属性,表达了当委托合同的双方(尤其是受托方)存在一定的利益时,原则上就应当允许当事人排除任意解除权,以保障双方利益之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就受托人是否存有利益,不应仅仅以受托人是否享有报酬请求权(是否为有偿委托)来判断,而是应当考虑委托事务的完成对受托人是否产生利益。[39]
综上所述,虽然否定说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至少就具有商业交易背景的委托合同而言,委托人与受托人合意排除任意解除权仍有较大可能被认可。另外,通说认为,代理权的撤回权原则上亦可被合意排除(孤立代理权除外),其理由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合意排除较为相似。[40]并且,在基础法律关系的设立与代理权的授予系通过一份文件实现的情况下,双方合意排除基础法律关系的任意解除权通常意味着双方亦合意排除了代理权的任意撤回。[41]
2.表决权委托协议任意解除权之排除
如前所述,司法实践通常将表决权委托协议定性为委托合同,就当事人是否能够合意排除任意解除权同样存在分歧。
部分法院认为当事人就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的,不应发生效力。例如前文提及的(2021)粤07民终7006号案中,法院认为“表决权委托约定性质上属委托合同关系,在委托方与受托方信任基础动摇或丧失信任的情形下,双方所作出的不可撤销委托的约定显然不具有强制力”。[42]再如,(2017)京01民终4548号案中,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是建立在对受托人的信赖基础上的……如果委托对受托方的信赖基础发生动摇或者不复存在,即使这种信赖的动摇仅仅是委托人主观意识中的一种担心、焦虑,合同的继续履行都有可能会使委托人处于不安的状态……由于委托人将本人的事务交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的利益处于受托人的控制、支配之下,受托人是否忠实处理或者是否有能力完成受托事务,对委托人的利益关系极大。因此,从法理上说,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更为重要,更不应受到不当的限制……除非受托人有充足的理由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否则这种限制应视为受托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限制委托人利益而设置的法律障碍,蕴含着受托人对忠实义务的拒绝承担。对于这样的不当限制,法律应该对其做出否定性的评价”。二审法院认为,“‘不可撤销’确为双方当事人对不得解除委托所做的特别约定,但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并不因当事人预先对权利行使作出限制而随即产生丧失单方解除权的法律后果……委托合同关系主要基于人身信赖关系订立……委托合同双方在订立合同时难以对此后双方的信任关系作出预判,在委托方与受托方信任基础动摇或丧失信任的情形下,双方所做的不可解除委托的约定显然有悖于委托合同的基本性质”。据此,法院认定虽然李某与陈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8条第5款约定了李某将经营管理权全部授予陈某且“不得单方撤销”,但该约定的性质属于委托合同,李某仍得以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第8条第5款。[43]
部分法院则认为当事人就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的,应为有效。例如前文提及的(2021)赣06民终375号案中,二审法院认定“《表决权委托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该协议书约定诸暨公司和张某将拥有的公司全部股份表决权“不可撤销地授权委托”黄某行使并约定了委托期间,因此,诸暨公司和张某无权“随时解除委托合同”。[44]再如,(2020)豫03民终5122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虽然《合同法》第410条规定了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该规定“不是强制性规定,而是属于授权性规范”,据此,王某和投资公司在《表决权委托协议》中对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和排除的特别约定应为有效。[4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案例无论采用何种观点,主要仍是围绕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能否通过合意排除进行的分析论证,未能充分结合案涉表决权委托协议订立背景做出更为具体的分析。[46]基于前文对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合意排除的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的梳理,我们认为,若能在个案中结合表决权归集的商业背景,充分说明受托人具有通过行使表决权增强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或影响等重要利益,表决权委托协议任意解除权的排除约定的法律效力即有较大可能被肯认。
(四)孤立表决代理权任意撤回权的排除
如前所述,商业实践中,孤立代理权并不常见。经过检索,我们尚未发现明确通过孤立代理权授予的方式实现股东间一致行动的交易实例,但考虑到该方式仍有存在的可能性,我们也对孤立代理权任意撤回权的排除作简要的分析。
通说认为,孤立代理权的任意撤回权不得排除。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孤立代理权并无基础法律关系相伴,自然无法通过合意的方式排除撤回权。[47]另一方面,代理人在享有代理权的同时并不负担基础法律关系上的义务,容易使得代理人失去掣肘,使得被代理人处于不利地位,因而也不应允许被代理人抛弃其撤回权。[48]这背后的理念是社会一般秩序与意思自治原则之间的平衡,即认为当意思自治容易引起社会秩序的不安定时,应当加以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域外法上,有观点认为股东表决代理权的撤回权也不得通过合意排除。[49]
因此,在表决权归集的交易安排中,如果采用孤立代理权并约定不可撤回的方式,一旦发生争议,这种排除任意撤回权的约定效力将很可能会被否定,从而难以确保实现部分股东长期通过代理的方式行使其他股东表决权的商业目的。
(五)被代理人股东本人到场行使表决权的特殊问题
我们观察到,交易实践中,还有可能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即部分股东将其表决权授予其他股东代理后,又出席股东会/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且其表决内容与其代理人代为表决的内容存在差异(例如被代理人投同意票,代理人投反对票)。该情形下,表决内容应当如何认定即会产生争议。
若认为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性质为委托合同且认为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不得合意排除,则可以将委托股东出席股东会/大会并表决的行为解释为作出解除表决权委托的意思表示,根据有因原则,受托股东作为表决权代理人的代理权相应终止,其表决内容不应约束被代理人。例如,(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案中,最高法院查明副食品公司的5名股东与股东名册上记载的其余所有股东签订了“股东代表委托书”,约定由该5名股东“行使投资收益权外的股东一切权利”,据此,最高法院认定该5名股东可以代表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50]针对部分作为委托人的股东亲自到场行使表决权的问题,最高法院则认为,根据《合同法》第410条关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规定,这些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关系,因此,当这些股东亲自参加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时,应视为对委托关系的解除。最终,最高法院认定不应仅仅按照该5名股东的表决情况作为计票依据,而是应当将其他到场投票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一并统计在内。
更为疑难的是,若认为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性质为委托合同且认为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得以合意排除,或认为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性质并非委托合同而本就不产生任意解除权(且代理权的撤回权已被合意排除),此时代理权无法被终止,又应当如何处理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作出的矛盾意思?
对该问题,我国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均鲜有讨论。我们倾向于认为,当被代理人与代理人同时到场作出意思表示时,原则上应当以被代理人的意思为准。意定代理制度是对本人(被代理人)私法自治的扩张与补充,而非限制,代理人归根结底也只是本人的一种延伸。[51]因此,在有相对人的场合,若相对人同时受领被代理人与代理人作出的意思表示,似乎没有理由忽视被代理人而以代理人的意思表示为准。因此,在股东会/大会上[52],即便表决代理人的代理权尚存,但在被代理人到场且行使表决权的情况下,仍应以被代理人的表决内容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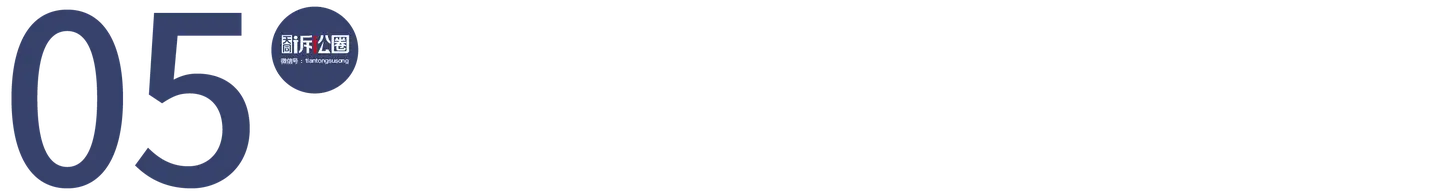
小结
报告第二篇中,我们结合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对表决权归集的代理模式作了系统性阐释,可以归纳以下结论。
第一,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具有可代理性,此系代理模式之基石。股东会决议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须通过股东行使表决权而形成,而股东表决权的行使系意思表示的作出,可通过代理方式予以实现。虽然《公司法》只规定了股份公司的表决权代理,但基于前述理论构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表决权同样具有可代理性。
第二,绝大多数表决权归集的商业实践通过一份交易文件同时设立基础法律关系并完成代理权的授予。鉴于代理权授予行为区分且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仅仅设立委托法律关系等基础法律关系,无法使得部分协议股东获得表决代理权。在发生争议时,协议约定的意思表示解释将发挥重要作用。从防范争议的角度,应当重视协议中关于双方基础法律关系和代理权授予等交易安排、交易目的的清晰准确表达。
第三,司法实践中,鲜有否定表决权委托与表决权代理效力的情况。但表决权委托的约定内容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会被认定实质为表决权转让,进而影响其效力评价,以及该代理模式是否有可能被认定属于“股东权利滥用”,从而影响表决权委托或表决权代理的效力,值得关注和思考,我们将分别在第三篇和第四篇中对此予以讨论。
第四,表决权代理模式下基础法律关系的任意解除及其排除(代理权的任意撤回及其排除),存有一定争议。我们认为,基础法律关系的解除通常可以引起代理权的终止(有因原则)。就司法实践通常认定的表决权委托性质为委托合同,因而得以适用任意解除权规范的观点,不无探讨与反思的空间。在表决权委托性质被确定为委托合同的前提下,当事人能否合意排除任意解除权也存在争议。我们倾向于认为,若能在个案中充分阐明表决权委托中的受托方利益,协议股东作出的排除任意解除权的约定效力有相当可能得到肯定。通说认为孤立代理权的撤回权不得通过合意排除,采用孤立代理权实现表决权归集的风险较大。无论认为表决权委托是否适用任意解除权规范、任意解除权是否能被合意排除,在委托股东本人(被代理人)出席股东会/大会且作出与受托股东(代理人)不同的表决内容时,应当以委托股东的表决内容为准。这也是通过代理模式实现表决权归集时,受托股东面临的最突出的风险点。
有效控制前述风险的一种可能方式为,协议股东通过转让的方式使得表决权的归属发生变化,进而使得受让表决权的股东以权利人的身份直接行使表决权。我们将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一致行动的模式称为表决权转让模式,并将在报告第三篇中具体予以阐述,敬请关注。
注释:
[1] 参见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7民终7006号民事判决书。
[2] 参见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6民终375号民事判决书。
[3] 关于有因原则及无因原则在法律效果上的区别,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以下。
[4] 支持无因原则的代表性观点,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239页(郝丽燕执笔);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载《法学》2017年第1期,第20页以下;尹田:《论代理制度的独立性——从一种法技术运用的角度》,载《北方法学》2010年第5期,第46页以下;陈华彬:《论意定代理权的授予行为》,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2期,第190页以下。
[5] 支持有因原则的代表性观点,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40页;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以下;汪渊智:《代理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以下;冉克平:《代理权授予行为无因性的反思与建构》,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第86页以下。
[6] 有学者指出,无因原则的制度价值体现在明晰法律关系、维护代理人的利益及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相对人)。参见迟颖:《意定代理授权行为无因性解析》,载《法学》2017年第1期,第26页以下。
[7] 在有因原则下,也能够通过被代理人追认制度、表见代理制度保护代理行为的相对人。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5页;冉克平:《代理权授予行为无因性的反思与建构》,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第94页以下。
[8] 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0页。
[9] 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28页。
[10] 参见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20)川1303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民终3513号民事判决书。
[11]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816页。
[12] 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36页。
[13] 《合同法》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14]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3民终5122号民事判决书。
[15] 参见崔建远:《论法律关系的方法及其意义》,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1页以下。
[16] 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17]【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18] 较为典型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该规定即体现了,若案涉合同体现的主给付义务为一方提供资金,另一方支付相应利息的,这与借款合同项下双方的主给付义务一致,法院可以认定案涉合同属于借款合同。当然,案涉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内容为何,本身也是意思表示解释之结果。
[19]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65页。
[20] 依邱聪智教授所言,“委任契约之概念,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举凡法律规定所未及劳务契约,均得认为委任,其结果使委任之概念容涵能力无限宽广”。参见邱聪智:《新订债法各论》(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21] 王轶、高圣平等:《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典型合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96页以下。
[22] 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786页(任我行执笔);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53页
[23] 类似观点,参见廖森林:《权利分置下的上市公司表决权委托探析》,载《济宁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第66页以下。
[24] 较为类似的,有学者指出,一些代理商合同虽然看似且冠以委托合同之名,但其商业实质与一般的委托合同大相径庭,不应定性为委托合同,亦不应适用委托合同中的任意解除权。参见武腾:《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与违约责任》,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2期,第75页。
[25] 《民法典》第563条第2款规定:“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26] 《民法典》第730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27] 关于民法典中规定的任意解除权的类型化分析,参见朱虎:《分合之间:民法典中的合同任意解除权》,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1018页以下。
[28]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3民终5122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投资公司于某次临时股东大会上代王某行使表决权,同意了目标公司实施破产重整的议案,而“公司破产重整必然导致原股东股权的让渡或增资扩股,该破产重整决议直接涉及股份转让、增资扩股及公司资产处理、转让等委托人所有股权的处分事宜”,违反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关于“行使委托表决权不得涉及委托人所持有股份的处分事宜”的约定,“而表决权是股东基于股权享有的权利之一”,投资公司的该项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29] 蔡恒、骆电:《我国〈合同法〉上任意解除权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110页。需要注意的是,本文认为,若基于立法论立场,应赞同“适当限制法定任意解除权的行使范围,在委托合同中对有偿委托合同或商事委托合同中的法定任意解除权可以适当加以限制,甚至可以考虑排除法定任意解除权的适用。”
[30] 尤其是在高层级法院案件中较为罕见。
[31]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91页;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四)》,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2529页。需要提示的是,最高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于2021年编著的《民事审判实务问答》却又采用了区分说的立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
[32] 参见吕巧珍:《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限制》,载《法学》2006年第9期,第80页以下;武腾:《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与违约责任》,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2期,第65页。
[3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50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签订的合同“预先对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进行了放弃……在法律没有对当事人放弃任意解除权作出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得到尊重”,据此,最高法院认定《合同法》第410条规定的任意解除权在本案中不应被适用。
[34] 王轶、高圣平等:《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典型合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59页以下;崔建远、龙俊:《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及其限制——“上海盘起诉盘起工业案”判决的评释》,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83页;仲伟珩:《有偿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20年第17期,第25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
[35] 参见韩富鹏:《民商区分视角下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载《财经法学》2021年第3期,第100-101页;蒋佳艺:《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基础及限制》,载《私法研究》第22卷,第110页。
[3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491号民事裁定书。本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合同法》之所以规定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主要是基于委托合同双方当事人存在人身信赖关系,一旦这种信赖关系破裂,合同便没有存续的必要,应允许当事人行使任意解除权。但是,在诸如本案这种商事委托合同的缔结过程中,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之间是否存在人身信赖关系往往并非是委托人选择受托人的主要考量因素,其更多的是关注受托人的商誉及经营能力。同时,受托人为完成委托事务通常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开拓市场、联系客户等等,为了防止对方行使任意解除权带来的不确定风险,故对解除条件作出特别约定以排除任意解除权的适用,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履行风险所作出的特殊安排,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且也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在此情况下,如仍允许委托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就会给受托人带来重大损失,且由于经营可得利益的不确定性,解除合同后受托人所能获得的损害赔偿往往与继续履行合同所能获得收益不相匹配,这一结果显然有悖公平原则。因此,鉴于商事委托合同的特殊性,当双方当事人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特别约定时,应当认定《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关于任意解除权的约定已经被排除适用。”
[37] 有观点谓之“允许任意解除的正当性越强,排除任意解除权的条款越容易认定为无效;反之,则更应认定为有效。”参见陆青:《合同解除论》,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298页。
[3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491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226号民事判决书。
[39] 崔建远、龙俊:《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及其限制——“上海盘起诉盘起工业案”判决的评释》,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78页。
[40]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页;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36页以下。
[41] 杨代雄教授指出,“撤回权的意定排除需要从基础关系中寻求正当性……如果基础关系表明代理人就代理权之存续具有自己的利益,则允许对撤回权予以意定排除”。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37页。
[42] 参见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7民终7006号民事判决书。
[43]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4548号民事判决书。
[44] 参见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6民终375号民事判决书。
[45]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3民终5122号民事判决书。
[46] (2017)京01民终4548号案中,一审法院一定程度地考虑了案涉交易的背景,即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基于双方即将协议离婚并分割财产的背景(《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大致可以归纳为,标的公司股权对半分,此外,转让方李某作为委托人,将其剩余的一半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委托于陈某且“不得撤销”。但是,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在即将与陈某离婚之时将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委托于后者,系基于对其之信任,该说理似有商榷余地。
[47]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页。
[48]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2页、第353页;汪渊智:《代理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页;【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4页。
[49] 转引自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37页。
[5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民事判决书。
[51] 德国法上,有学者指出“不可撤回代理权不具有超出意定代理权基本属性的效力”,“在不可撤回意定代理权的情形中,意定代理人所取得的也仅是代理权”。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7页。
[52] 在股东会/大会上,表决意思表示的相对人通常为股东会/大会的召集人或主持人。参见孔洁琼:《决议行为法律性质辨——兼评〈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9年春季卷)》,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