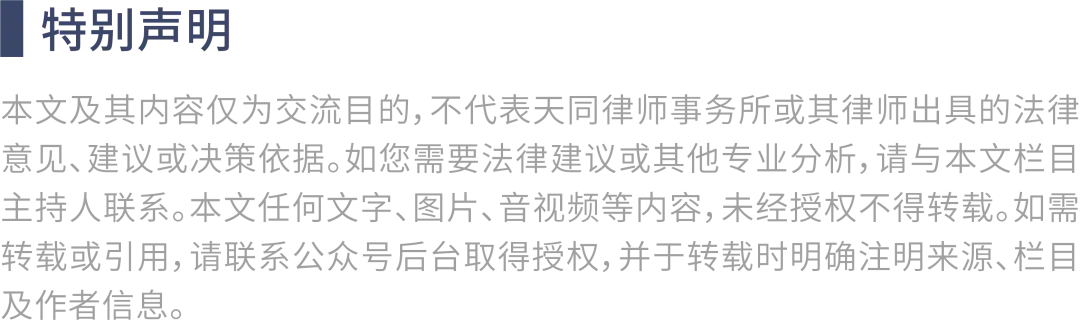文/杨骏啸 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丹丹 天同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姚一纯、余周洋、高西雅 天同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
一致行动是对一类现象的指称,大致可以理解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基于特定的关联关系而采取的一致行为。对一致行动的法律规制源于欧美的证券法领域,起初主要针对上市公司股权的联合收购,之后逐渐扩大到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其他协同行为。[1]例如,上市公司的非关联方股东通过签订一致行动协议来实现敌意收购(hostile takeover)或反并购(anti-takeover)。[2]
在我国境内,一致行动的规范概念亦源于证券领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于2002年制定的《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第9条[3]首次定义了一致行动人,证监会于2006年制定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83条第1款[4]则在前述基础之上,将一致行动界定为“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几经修订,但其对一致行动内涵的基本界定延续至今,其影响力还扩展到了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行业的股权监管领域。[5]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前述行业监管较为严格的特定领域,一致行动在一般的商事交易中也被广泛运用。不同的是,在有明确监管规范的领域,一致行动通常可以区分为协议型一致行动(即交易主体通过协议创设一致行动关系)与事实型一致行动(即监管规范根据特定的事实推定交易主体之间构成一致行动关系[6]);而在没有明确监管规范的领域则只存在协议型一致行动,且一致行动所指向的行为内容往往更为丰富,一致行动效果的实现方式亦更为多元。例如,近期引起广泛关注的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蚂蚁集团)控制权变更的背景即为,马云先生作为杭州云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云铂投资)的股东,曾与该公司的其他股东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从而实际支配云铂投资股东会与行使蚂蚁集团股东权利相关事项的表决结果”,进而通过云铂投资控制的两个公司“间接控制蚂蚁集团53.46%股份的表决权”;在本次蚂蚁集团的控制权调整中,一项重要的举措便是马云先生与云铂投资的其他股东通过协议方式终止了先前订立的一致行动协议。[7]
虽然一致行动在各类商业实践中已被广泛运用,但对其在法律层面的研究尚不深入,亦缺乏体系性。尤其是针对“强监管”领域之外的,却又极具适用普遍性的协议型一致行动,仍有大量空白亟待填补。例如,A公司的股东甲与股东乙约定甲将其对A公司的表决权“让渡”于乙,该协议所创设的法律关系为何?或者反过来看,该商业安排(表决权之“让渡”)需要/可以借助哪些法律制度实现?再例如,B公司的股东丙与股东丁约定,丙在B公司部分治理事项上的表决应当与丁保持一致,若丙在相应事项上实际作出了与丁相反的表决,丁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救济?
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协议型一致行动的法律适用往往横跨商法与民法,尤其是公司法与合同法上的交叉,在理论层面本身就属于较为疑难和复杂的领域。从司法实践来看,也存在裁判观点不统一的情形,例如,就相似的两份一致行动协议的解除,有法院认为当事人可以通过合意排除表决权委托的任意解除权[8];相反,有法院则认为表决权委托的任意解除权不得通过合意排除[9]。
本次研究报告中,我们将在对相关交易实践与司法裁判充分观察的基础之上,聚焦协议型一致行动的法律适用,对其构造、效力及救济方式等具体问题作体系研究,以期厘清其内涵与外延,为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与争议提供助力。
本次研究报告将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分篇推送,本篇为先导篇,主要介绍协议型一致行动在商业实践中的主要适用场景及参与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对协议型一致行动作进一步的类型化区分,同时阐明本次研究报告的主要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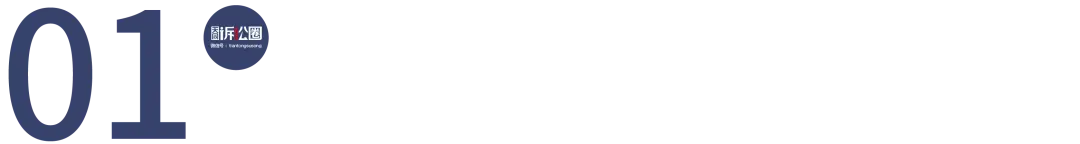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协议型一致行动的典型商业目的:增强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
通过数据检索以及实务观察,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协议型一致行动发生于公司的股东之间,其商业目的主要为通过股东经营管理权利行使上的一致性,增强个别或部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交易实践中常说的一致行动主要指的就是此类狭义情形。[10]另外,在一些不涉及公司治理的场合,交易主体也可能会通过达成一致行动来追求交易行为的一致性,例如同时处置财产权利或继续保持财产权利不发生变化。从广义上看,这类情形也属于一致行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更为多元,交易实践中往往也不用一致行动来代称。
(一)狭义而言,协议型一致行动的商业目的为通过股权行使上的一致性,增强个别或部分股东对目标公司的控制力
股权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股东获取经济利益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两个维度,其中,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又可以大致分为参加公司决策的权利以及选任公司管理者的权利。[11]股东的经营管理权主要依托于股东的表决权来实现,并且表决权的行使应遵循股权平等原则(即股东按照出资比例或股份持有数量享有、行使相应份额的表决权),只有在法律直接规定或法律允许公司章程另行约定的特殊情况下,股东的表决权才会受到限制或采用同股不同权的模式。[12]
在前述规制之下,公司的某个股东或部分股东若希望在不改变出资份额或持股数量、比例的情况下加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力,往往会订立一致行动协议,以达到表决权二次配置、集中行使的目的。
从“行动内容”来看,有的协议型一致行动涵盖了所有的股东表决事项。例如,某药业公司的股东实业公司与投资公司签订协议[13],约定实业公司将其持有的药业公司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及提名和提案权“独家、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全权让渡”给投资公司行使,包括但不限于:(1)股东提案权,提交包括提名、推荐或变更、罢免董事、监事等事项在内的任何股东提议或议案及做出其他意思表示;(2)召集、召开和出席股东会;(3)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一致行动协议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4)其他根据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一致行动协议授予的与表决权及提名和提案权相关的其他股东权利(权益)。[14]
有的协议型一致行动则仅针对特定的股东表决事项。例如,某公司的股东甲(出资额占比为42.85%)与股东乙(出资额占比为9.05%)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对公司今后召开股东会会议关于选举和更换执行董事、决定有关执行董事的报酬”的事项作出决议时,乙在表决内容上应当与甲保持一致。[15]
从“行动效果”来看,多数协议型一致行动所欲实现的目标为由个别协议股东支配其他协议股东的表决权。例如,前述云铂投资股东间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便使得马云先生得以支配云铂投资股东会与行使蚂蚁集团股东权利相关事项的表决结果,进而使得马云先生可以通过云铂投资控制的两个公司间接控制蚂蚁集团53.46%股份的表决权。[16]
少数协议型一致行动仅笼统体现为协议股东应当在表决权的行使上保持一致,或在协议股东之间创设了额外的表决机制,但并不追求其中个别股东的绝对支配效果。例如,某公司的股东甲、乙、丙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在公司每次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前,甲、乙、丙应当先行召开协商会议,甲应当与乙和丙最终确定的一致意见保持一致;但若乙和丙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则甲、乙、丙应当在三人内部进行一人一票的表决,以过半数所支持的赞成/反对/弃权意见作为三方在股东大会上的统一意见,若赞成/反对/弃权意见均未过半数的,则以反对意见作为三方统一意见。[17]从前述一致行动协议的具体约定来看,当事人并不希望甲、乙、丙中的任何一人能够支配其他两人的表决权。
但无论针对何种“行动内容”,以期何种“行动效果”,上述协议型一致行动的商业目的都是为了增强个别或部分股东对目标公司的控制力。另外,协议型一致行动也可能发生于公司董事之间,但通过公开信息检索,我们发现公司董事之间的协议型一致行动,几乎都发生在公司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下。例如,某家居公司股东甲和股东乙同时也担任该公司的董事,双方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应保持一致行动,并约定双方作为董事在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时亦应当保持一致。[18]
(二)广义而言,协议型一致行动的商业目的还包括在不涉及公司治理的情况下追求交易行为的一致性
在一些不直接涉及公司治理的场合,交易主体也可能会通过达成一致行动来追求交易行为的一致性,其表现形式也更为多元。例如,某公司的股东甲与股东乙签订协议,约定在甲将公司股权转让于丙的情况下,乙作为甲的一致行动人,也将股权转让于丙,且接受甲与丙之间股权转让协议的约束。[19]再例如,甲银行、乙银行等四家银行签订协议,约定协议各方不得“单方面对债务人采取任何债务追索措施……在重组期间发生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等风险事件,协议各方须信息共享,可通过召开债权人会议的方式,共同商讨相关事宜”。[20]
广义上看,这些情形也属于多个主体通过协议而达成的一致行动安排,只不过通常不直接涉及公司的治理,交易实践中也往往不用一致行动来代称,而是根据具体的交易模式冠以他名,例如“领售/强卖(drag-along)”“跟售/随卖(tag-along)”等。
整体而言,狭义的协议型一致行动的商业目标更为明确、集中,在商业实践中的适用也较为普遍,在法律适用上因横跨多个部门法领域而更为疑难复杂。因此,本次研究报告将狭义的协议型一致行动——通过协议方式实现并以增强个别或部分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为目的的一致行动——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如无特别说明,报告后文所称“协议型一致行动”“一致行动协议”等均作此限定)。另外,虽然合伙企业等非公司形式的营利法人也常常涉及协议型一致行动,但考虑到适用的普遍程度及合伙企业在内部决策程序上相较公司而言更为灵活的特点[21],本报告仍将以公司为一致行动的目标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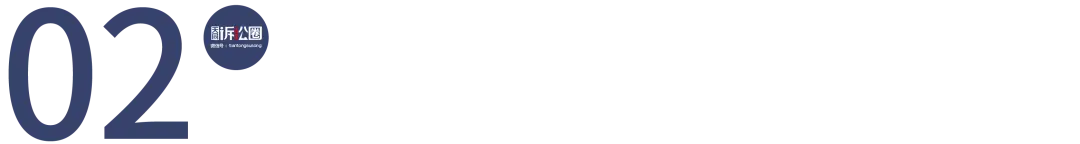
协议型一致行动的类型化研究:以表决权二次配置的方式为区分标准
如前所述,协议型一致行动的核心商业目标为增强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具体实现方式为,在不改变股东出资份额/持股比例的前提下,通过订立一致行动协议对协议方的表决权在协议方内部进行二次配置,使得个别协议股东支配其他协议股东的表决权,以增强该个别股东对目标公司的控制力;或使得协议方在表决权行使上保持一致,以增强全体协议股东对目标公司的共同控制力。总之,在股东以行使表决权作为其参与公司治理、决策核心方式的制度之下,股东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份额越多,对公司的影响力、控制力也就越大。[22]
我们认为,根据协议股东对表决权二次配置的方式,可以将协议型一致行动区分为两大主要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协议股东将其对目标公司的表决权交由其他协议股东行使,不妨将该类型称为“表决权归集”,相应的协议称为“表决权归集协议”。第二种类型为:协议股东在不交出表决权的情况下,与其他股东在表决权的行使上保持一致,不妨将该类型称为“表决权拘束”,相应的协议称为“表决权拘束协议”。
“表决权归集”和“表决权拘束”这两种类型的区分,本质上源于协议股东间拟实现的商业安排的差异——协议股东间拟在何等程度上对表决权进行二次配置。而这样的差异也导致了两种类型的底层法律构造有所区别,相应的法律适用也不尽相同。本篇中,我们将概要介绍“表决权归集”和“表决权拘束”这两种类型,阐明两者在交易实践中的基本表现形式以及面临的法律适用难点。
(一)表决权归集
表决权归集的主要特征为,目标公司的股东通过协议的方式,将部分股东对目标公司的表决权交由其他股东行使。交易实践中,表决权归集往往体现为“表决权让渡/转让”“表决权委托”“表决权代理”等外在形式。
例如,曾引发热议的“宝万之争”中,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科集团)的股东深圳市钜盛华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钜盛华)曾与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前海人寿)签订了《表决权让渡协议》,约定钜盛华将其直接持有的万科集团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不可撤销的、无偿让渡”于前海人寿;前海人寿有权按照协议及万科集团章程行使钜盛华直接持有的万科集团股份所对应的股东大会全部表决权;前海人寿在协议约定范围内“按照自主意愿”行使前述表决权,且“无需钜盛华另行授权”;对于钜盛华直接持有的万科集团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钜盛华将按照前海人寿的“行权指令”行使表决权。[23]
又如,某阀门公司的股东甲与股东乙签订了《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甲将其持有的阀门公司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予”乙行使,乙针对所有需要阀门公司股东大会讨论、作出决议的事项行使前述表决权;甲可以自行参加阀门公司的相关会议,但“不另行行使表决权”;甲应配合乙行使“委托权利(包括前述必要的股东大会授权文件等)”;委托期限为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甲不再持有阀门公司股份或协议终止之日或协议生效满36个月止;乙滥用甲所委托的表决权,给甲或阀门公司造成损失的,乙应当赔偿损失;乙接受委托不收取任何报酬。[24]
在上述两例中,表决权归集分别以“表决权让渡”“表决权委托”的形式呈现。但若仔细观察其内容,会发现协议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似乎并非如其名称(“让渡”“委托”)所示那么简单。比如,钜盛华与前海人寿之间的《表决权让渡协议》约定钜盛华将表决权让渡于前海人寿,且前海人寿行使该表决权无需钜盛华另行授权,但同时又约定钜盛华应按照前海人寿的“行权指令”行使表决权。那么,在该《表决权让渡协议》之下,前海人寿是基于表决权受让人还是表决权代理人的身份在股东大会上作出表决权行使的意思表示?抑或钜盛华仍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表决权,但其应当遵守钜盛华对表决权内容的指示?又如,根据前述《表决权委托协议》,甲在阀门公司的股东大会上“不另行行使表决权”,但若在某次股东大会上,获得甲授权的乙作出了同意某个议案的意思表示,而甲也亲临股东大会并当场作出了反对该议案的意思表示,应当以何者为准?
这些现实问题的背后都蕴含着更为抽象的底层法律问题:表决权的委托与表决权代理之间是何种关系?在委托关系、代理关系系主要基于受托人、代理人的利益而设立的情况下,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排除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被代理人向代理人授予不可撤销的代理权,其效力如何?代理人与本人就同一事项作出不同意思表示时,应当如何认定?表决权作为股权的一部分,能否脱离其他的部分而单独让与?
我们将在报告的第二篇及第三篇中,分别以“表决权代理”“表决权转让”为基本脉络,结合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阐述表决权归集模式下的几种法律构造,并在分析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说明每种构造对“增强股东控制力”这一核心商业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表决权拘束
表决权拘束的主要特征为,目标公司的股东通过协议的方式约定各自行使表决权,但部分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应当与其他股东保持一致。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未约定协议股东之间的主随关系,而仅是笼统约定协议股东行使表决权时应当保持决策上的一致。
例如,在著名的“华电案”中,江西华电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电公司)、华电公司股东胡某以及张某签订《股份认购协议》与《期权授予协议》,约定华电公司向张某定向增发股权,在华电公司股份上市交易前,张某承诺其所持华电公司股份的投票与胡某保持一致。[25]
本案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热烈讨论,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至少包括,《股份认购协议》与《期权授予协议》中“一致行动条款”到底创设了何种法律关系?进而,当协议股东张某明确表示其不愿遵守“一致行动条款”时,胡某能否依据“一致行动条款”要求张某实际履行义务,在股东大会上与胡某保持投票一致,抑或仅能以张某不履行义务为由请求张某赔偿损失?张某参加华电公司股东大会并在行使表决权时投了与胡某相反的票,张某所投之票是否具有效力,又是否影响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另外,若华电公司作为《股份认购协议》与《期权授予协议》的签约主体,其是否同样因“一致行动条款”而享有某种权利或负有某种义务?
这些问题的背后同样蕴含着更为抽象的底层法律问题:表决权拘束模式下,协议各方的给付内容到底为何?这样的给付内容是否可能会造成拘束协议的效力瑕疵?在部分协议主体不履行的情况下,其他主体能否请求实际履行(强制履行),程序法上是否有配套的保障制度?若其他主体请求赔偿损失,该损失应当如何界定?
我们将在报告的第四篇至第六篇中,结合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阐明表决权拘束模式下的基本法律构造,围绕合同效力、履行障碍以及违约责任等方面,分析表决权拘束中的具体法律适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说明表决权拘束对“增强股东控制力”这一核心商业目标的实现程度。
注释:
[1] 参见张斌、陈洪天:《上市公司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监管评述》,载《清华金融评论》2019年第9期,第51页;吴双:《一致行动认定论:概念重构与规范变革》,载《理论月刊》2020年第9期,第119页以下;王劲松:《论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一致行动问题》,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4期,第64页。
[2] 张洪辉、邹英、章琳:《非关联股东结盟与公司创新——基于一致行动人的经验证据》,载《证券市场导报》2021年第6期,第43-44页。
[3]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第9条规定:“一致行动人是指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关系等合法途径扩大其对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比例,或者巩固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在行使上市公司表决权时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前款所称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情形包括共同提案、共同推荐董事、委托行使未注明投票意向的表决权等情形;但是公开征集投票代理权的除外。”
[4]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06年施行)第83条第1款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5] 例如,《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2018年施行)第56条第4项将“一致行动”界定为“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2018年施行)第92条第1款将“一致行动”界定为“指投资人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人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保险公司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这两个规范对一致行动的界定,几乎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一致。
[6] 例如《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第83条第2款规定了11种可以推定具有一致行动关系的情形,《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2018年施行)第92条亦有类似规定。
[7] 《蚂蚁集团关于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的公告》,载蚂蚁集团官网2023年1月7日,https://www.antgroup.com/notices/1。
[8] 参见云南省个旧市人民法院(2020)云2501民初1514号民事判决书。
[9]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4548号民事判决书。
[10] 此外,就事实型一致行动而言,前述涉及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监管规范所规制的也只是投资者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可见,监管规范也是在狭义层面来使用“一致行动”的术语。
[11]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54-255页。
[12] 针对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针对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103条第1款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此外,《公司法》第131条规定:“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份,另行作出规定。”这为我国股份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法律依据,例如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6号)就提出了优先股制度,其中,优先股股东所持股份原则上无表决权,仅在修改章程等特殊事项中,优先股股东享有表决权。关于同股同权规则的反思,参见李洪健:《同股同权规则的再释义与我国公司股权结构改革》,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32页以下。
[13] 协议签订方还包括该药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一致行动人某典当行。
[14] 参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表决权让渡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载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官网2020年9月14日,http://www.kangmei.com.cn/uploadfile/2020/0914/20200914111149283.pdf。
[15] 参见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4民终1096号民事判决书。
[16] 《蚂蚁集团关于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的公告》,载蚂蚁集团官网2023年1月7日,https://www.antgroup.com/notices/1。
[17] 参见《300724 捷佳伟创: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载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bf0c797a-75cb-4b88-ab46-56bc9d9547f4。
[18] 参见《300616 尚品宅配募集说明书(注册稿)》,载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2023年2月8日,http://www.szse.cn/disclosure/listed/bulletinDetail/index.html?9e0d1acd-c083-444d-b972-f7a4af7e7f4a。
[1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607号民事判决书,本案中乙系通过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从甲处受让获得的公司股权。
[20] 参见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青民初109号民事判决书。
[21] 《合伙企业法》第30条第1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表决办法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22]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页;梁上上:《股东表决权:公司所有与公司控制的连接点》,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第114页以下。
[23] 参见《关于股东表决权让渡的提示性公告》,载万科集团官网2016年4月9日,https://www.vanke.com/upload/file/2016-04-09/90eb0d37-a0bf-4e1c-955d-3652f643f172.pdf。另外,《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表决权让渡协议》还约定钜盛华将其通过几个不同资管计划控制的万科集团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不可撤销的、无偿让渡”于前海人寿,并约定就该部分表决权的行使,应先由前海人寿对万科集团每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表决选择并书面通知钜盛华,再由钜盛华根据前海人寿的选择,以钜盛华的名义通知资管计划对应的各管理人,“以决定各管理人对该等议案的表决选择”。
[24] 参见《江苏神通: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载江苏神通官网2019年7月3日,http://www.stfm.cn/news/809.html。
[25] 参见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5民终12号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申367号民事裁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