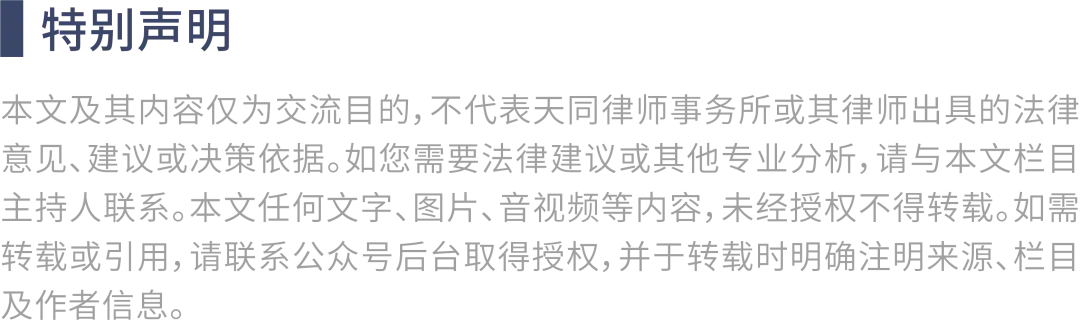文/民营企业纠纷解决报告课题组 王真 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郑杰 于胜 杜希 郑欣嘉 董悦 李振伟 天同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
编者按:最高法院在九民会议纪要上强调树立“穿透式”审判思维后,大量民营企业的融资合同被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经过几年的审判实践,穿透审理的审查规则、穿透后的法律效果已有实践规律可循,值得民营企业高度关注。此外,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数量也居高不下,如何准确识别、应对虚假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风险,同样是企业融资活动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聚焦以上两大问题,为民营企业梳理相关法律风险,提供相应防范建议。
【正文】
在民间借贷专题的上篇中,我们讨论了民间借贷合同本身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风险和防范措施。本篇为民间借贷专题的下篇,我们将探析企业各类融资合同被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的情形、涉嫌虚假诉讼的民间借贷纠纷情形,提示民营企业相应的法律风险,并提供相关应对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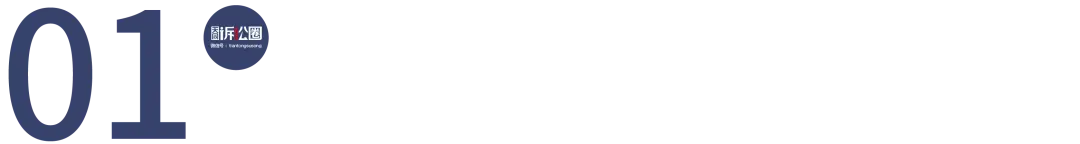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融资合同被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的风险
最高法院在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审理融资租赁、保理、信托等涉及多方当事人的多个交易纠纷案件中,要树立“穿透式”审判思维。此后,“穿透式”审查的应用就从金融监管领域向金融司法领域扩张。随着各级法院对《民法典》第146条的深入理解和熟练应用,“穿透式”审判思维也不断从金融纠纷向一般民商事纠纷渗透。
在民营企业融资纠纷中,“穿透式”审判的典型体现即是:企业参与签署的各种形式、名目的融资协议,最终被认定实质是民间借贷合同,适用民间借贷的规则认定合同效力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实践中,委托贷款合同、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的组合、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合资/合伙/增资合同等都有可能被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
(一)可穿透为民间借贷的合同类型
1、委托贷款合同
根据《贷款通则》和《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回的贷款。提供贷款资金的委托人可以是法人、非法人组织、个体工商户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受托人可向委托人收取代理手续费。
委托贷款通常通过商业银行向借款人发放,具有金融借款的外在形式。但在既往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以商业银行不承担任何贷款资金信用风险为由,将委托贷款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主流观点。刊登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1期的(2016)最高法民终124号案中,最高法院明确认为:“长富基金提供资金,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根据长富基金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并收回贷款,兴业银行武汉分行收取代理委托贷款手续费,并不承担信用风险,实质是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合同的效力和长富基金与中森华房地产公司之间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应受相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23年1月10日召开的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相关精神,委托贷款作为纳入监管的金融业务,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借用的“通道”行为存在本质区别。未来法院对委托贷款合同的性质认定将出现重大转向,不应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而是尊重委托贷款的金融属性,将其与金融借款合同作相同处理。[①]
2、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
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相继出台后,司法实践对涉及通道型信托的纠纷都较为敏感,往往积极地对相关合同进行穿透审查。实践中,通道型“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的交易模式有可能被法院穿透“信托贷款”的形式外衣,认定具有“委托贷款”实质意思,并进一步被穿透为“民间借贷”。
北京高院(2020)京民终36号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该案中,易光公司与中信信托签订《信托合同》设立4.4亿元单一资金信托,约定中信信托按照易光公司指令以自己的名义向长江建设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易光公司签署《信托指令函》,承诺其自行对借款人和保证人进行尽职调查,知悉并自愿承担借款人和保证人及该信托存在的经济和法律风险。中信信托与长江建设公司另行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约定中信信托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为易光公司的利益以自己名义向长江建设公司发放贷款4.4亿元。
北京高院分析认为:第一,根据《信托法》和《贷款通则》,出资人与金融机构间签订委托贷款协议后,由金融机构自行确定用资人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出资人与金融机构间成立信托贷款关系。出资人与金融机构、用资人之间按有关委托贷款的要求签订有委托贷款协议的,人民法院应认定出资人与金融机构间成立委托贷款关系。第二,虽然易光公司、中信信托和长江建设公司并未共同签订同一份委托贷款合同,但是先后签订的两份合同内容证明易光公司和长江建设公司对前者的信托资金用于向后者发放信托贷款均为明知。第三,易光公司通过《信托指令函》承诺自己承担信托贷款中原本应当由受托人中信信托承担的尽职调查、贷款资金监管等责任,中信信托公司并不承担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职责,有悖于信托法意义上的信托形式。因此,三方通过《信托合同》和《信托贷款合同》建立起了委托贷款合同关系,实质是易光公司与长江建设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的相关精神,上述交易结构下的穿透式审查也应予以限制。诚如刘贵祥法官指出,根据金融行业的通常理解,信托公司依法开展的资金信托业务与商业银行依法开展的委托代理业务均具有商业银行/信托公司收取约定的服务费用、不承担贷款资金信用风险、为委托人提供“贷款通道”的特点,均属于“委托贷款”的概念范畴,应与金融借款合同做相同处理。[②]
3、保理合同
现行法律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应当直接认定合同属于“名为保理、实为借贷”,仅仅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的第7条,对穿透审查保理合同的考虑因素进行了提示:“从是否存在基础合同、保理商是否明知虚构基础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方面审查和确定合同性质”。
实践中,法院多结合《民法典》第761条对保理合同的定义,考察交易是否与应收账款的转让、管理具有密切关联,以此为基础综合判断合同性质。
例如,(2019)最高法民终1449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龙盛公司转让给中原租赁公司的债权并未约定具体的债权到期日,且龙盛公司在中原租赁公司支付融资款后,随即按月向其支付利息并约定按期归还本金,而非在应收账款到期后无法收回时归还融资本息。龙盛公司实际上是依照固定的融资期限而非依照应收账款的履行期限偿还本息,融资期限与基础债权债务关系的履行期限不具有关联性”。据此,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又如,(2021)鲁民终2289号案中,山东高院认为,案涉“保理合同”没有关于保理人提供应收账款管理服务的约定,所载明的应收账款信息没有具体额度、到期日、对应的基础交易、还款形式等。因此,合同对融资数额、还款期间的约定与应收账款不具有关联性,案涉合同不具有保理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应为民间借贷合同。
再如,(2020)沪民申2186号案中,上海高院即认为:“杉德公司在明知《保理合同》所涉应收账款不存在的情况下,与博司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并交付款项,双方所作的意思表示应为名为保理实为借贷。”
据了解,最高法院或将通过金融审判会议纪要等形式对“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具体情形提供明确指引,不排除其将吸收既往法院实践中采取的审查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与商业银行签订的“保理合同”被穿透为借贷关系后应属金融借款合同;而民营企业与商业保理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被穿透认定为借贷关系后,是否属于民间借贷(而非金融借款)合同或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法释〔2020〕27号,简称《民间借贷解释适用范围批复》)规定“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商业保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因此商业保理公司签订实为借贷的合同,应当属于金融借款合同。但观察目前的司法实践,主流观点认为商业保理公司不是受批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其开展的交易如实际构成“发放贷款”,仍然属于法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应当适用民间借贷相关规定。[例如,北京高院(2019)京民终1432号案[③]、山东高院(2021)鲁民终2289号案[④]]。
4、融资租赁合同
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2号)第4条规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实为借款合同的,应当按照实际构成的借款合同关系确定各方的权利义务。”融资租赁合同与借款合同的核心区别是,前者在“融资”之外,还同时具有“融物”属性。缺乏“融物”特征的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应属于借贷合同。
实践中,缺乏“融物”特征的具体表现包括:租赁物虚假、出租人不享有租赁物所有权、租赁物价值虚高等。最高法院曾在(2014)民二终字第109号案中对此给予明确指引:“融资租赁交易具有融资和融物的双重属性,缺一不可。如无实际租赁物或者租赁物所有权未从出卖人处转移至出租人或者租赁物的价值明显偏低无法起到对租赁债权的担保,应认定该类融资租赁合同没有融物属性,仅有资金空转,系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贷之实,应属借款合同”。
在此前的融资租赁专题中,我们曾就融资租赁合同的穿透审查进行了详细探讨,感兴趣的读者可通过文末链接跳转浏览,此处不再赘述。根据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的相关精神,最高法院或将进一步明确融资租赁合同穿透认定为借贷的情形,不排除对租赁物具有可流通性、能够特定化、具有可使用性等基本标准进行细化。而就知识产权和不动产的资产受益权是否可作为适格租赁物等近期实践的焦点问题,我们也期待最高法院通过典型案例等形式予以指导、回应。
5、买卖合同
循环贸易是民营企业实现资金融通的隐蔽手段,通常由三方及以上的交易主体通过两两签订内容一致或高度相似的买卖合同构建贸易闭环,以货物交易的形式实现企业间借贷的目的。用资的民营企业通过“低卖”和“高买”分别实现资金“借入”和“归还”。实践中经常被穿透审查的买卖合同往往都是循环贸易中的一个环节,经穿透审查之后,用资企业与出资企业之间直接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
法院判断买卖合同可能涉及循环贸易、需要穿透审查的事实因素主要包括:第一,货物的最初出卖人与最终买受人是同一主体或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例如互为控股公司、具有相同的实际控制人或法定代表人等。第二,前述同一主体或关联主体存在“高买低卖”的异常行为。第三,上下游买卖合同除交易金额外,其他内容完全一致或高度相似。第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货物实际存在,包括没有货物流传凭证或者仅有货物流传凭证、没有交接凭证(即“走单、走票、不走货”)。第五,出资人存在越过上下游企业直接向用资民营企业追索“货款”的行为。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仅是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且离开整个交易链条无法查明案件事实并难以对当事人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及其效力作出认定的,应当告知原告将参与交易的其他当事人追加为共同被告。原告拒绝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是不影响其另行提起诉讼。”该等规定也透露出最高法院以查明事实真相为导向、对循环贸易纠纷进行穿透审查的倾向。
6、合资/合伙/增资合同
实践中,大量民营企业通过签订合资合同、合伙合同或增资合同等,引入外部投资以实现资金融通。部分合同可能具有“明股实债”的特征,可能被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第5次法官会议纪要指出:“名股实债并无统一的交易模式,实践中,应根据当事人的投资目的、实际权利义务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性质。……投资人目的并非取得目标公司股权,而仅是为了获取固定收益,且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权利的,应认定为债权投资,投资人是目标公司或有回购义务的股权的债权人。”
具有典型“明股实债”特征的合资/合伙/增资合同可能会直接约定保障投资方收回投资款,与股权投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原则相悖,从而被穿透为民间借贷。例如,(2021)最高法民终1236号案中,《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创联公司和珠禄公司按照储备土地挂牌出让成交后的毛利分成;创联公司收到珠禄公司投资资金后三年内返还全部本金;如果协议因故无法履行,创联公司十天内返还珠禄公司实际投资额并按照实际投资额年化30%的金额赔偿珠禄公司经济损失。据此,最高法院认为,“无论约定的土地最终能否收储、出让,创联公司均要返还珠禄公司全部投资款,还要保障其有所收益,珠禄公司存在只享有利润而不承担风险的情形,违背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投资交易原则,实际上是以投资名义签订的企业间借贷合同”。
部分合资/合伙/增资合同基于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具有“明股实债”属性,其核心交易安排是,投资方基于投资金额本身即可获取固定收益。例如,最高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682号案中,华金证券先签订《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成为与高安城投共担投资风险、分享投资收益的合伙人;又签订《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约定向高安城投转让所持合伙份额、高安城投按季度支付转让溢价款;双方同时约定《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效的前提是《合伙企业份额受让合同》签署、生效。据此,最高法院认为,华金证券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以设立合伙企业的同时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并收取固定溢价款形式,变相实现还本付息的借贷目的。
(二)被穿透为民间借贷的法律后果
1、合同可能因职业放贷、非法转贷等情形无效。借款人应当返还本金,如有过错,应赔偿出借人资金占用损失。
一旦前文述及的各类合同被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即应适用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简称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3条[⑤],如果存在非法转贷、职业放贷、出借人明知借款用于违法活动仍然出借,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情形,民间借贷合同将依法被认定为无效。进而,合同约定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等条款(如有)也随之无效,无需履行。但根据《民法典》第157条(如适用《合同法》则为第58条),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借款人应当返还出借人本金,借款人如有过错,应当赔偿出借人因此遭受的资金占用损失。
例如,(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齐商银行西安分行、红岭公司、巨富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实际是红岭公司与巨富公司之间的民间借贷;红岭公司贷款对象主体众多,从事经常性放贷活动、收取高额利息,未取得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扰乱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属于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应认定《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无效;巨富公司应当向红岭创投公司返还借款本金;鉴于借款事实成立且巨富公司实际将借款用于房地产开发,其应当向红岭创投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酌定为年化6%。
又如,前述(2020)京民终36号案中,北京高院认定案涉“单一资金信托+信托贷款”的交易结构实际是易光公司对长江建设公司放贷。法院进一步查明易光公司4.4亿元的借款资金源自工行五羊支行对易光公司母公司集团的银行贷款,经企业账户之间的资金划转流入易光公司账户;鉴于易光公司注册资金仅100万元,法院认为长江建设公司应当明知易光公司出借非自有资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简称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第2款,案涉资金信托合同和信托贷款合同无效。长江建设公司向易光公司返还借款本金、赔偿利息损失,利率酌定为一年期LPR。
再如,(2018)沪民初86号案中,上海高院查明,案涉钢材买卖交易构成循环贸易,认定出资企业中船物流公司与用资企业飙升公司之间形成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该院同时认为,仅本案纠纷所涉三个月期间,中船物流公司实际放款8笔,交易金额达到2.4亿余元,属于长期、反复以货物买卖为名开展企业借贷活动,并非出于生产经营需要,相关行为违反了金融法规及司法政策的规定,本案以买卖形式实际形成的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飙升公司作为实际用资人,应当承担归还借款之责,并补偿出借人合理的利息损失。
2、名为保理/融资租赁、实为民间借贷,法院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或有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对保理/融资租赁合同被穿透认定为借款合同的,由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同时,《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明确禁止融资租赁公司发放或受托发放贷款,实践中有部分当事人据此主张保理/融资租赁合同被穿透为借款合同后,借款合同也应无效。
主流司法观点认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仅指向未经批准“以借贷为业”的行为,应当考量同一出借人是否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不特定对象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贷款目的是否具有经营性,偶尔为之不能认定为经营,不属于该条禁止的范围[例如,北京高院(2019)京民终1432号案[⑥]]。《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借款合同无效[例如,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73号案[⑦]、上海金融法院(2021)沪74民终323号案[⑧]]。
但仍有部分法院会考虑相关部门规章对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贷款业务的禁止性规定,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9条进行宽泛理解,不认为该条仅禁止“以借贷为业”,进而认定保理/融资租赁合同被穿透为借款合同后,相应借款合同也应无效[例如,安阳中院(2022)豫05民终2350号案[⑨]、郑州中院(2020)豫01民终2851号案[⑩]、上海高院(2016)沪民申2374号案[11]]。
上述实践中的不同处理或将在未来归于统一。根据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的相关精神,最高法院应当倾向于支持融资租赁公司与债务人之间的借贷合同,如无其他法定无效情形,应为合法有效。
此外,考虑到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总有一定几率构成“名为融资租赁、实为借贷”,且银行信贷恰是融资租赁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否对融资租赁公司放宽职业放贷和非法转贷的认定标准,也值得探讨。
3、穿透为民间借贷合同后仍然有效的,“砍头息”要在本金中扣减,利率上限受到4倍LPR的限制。
如果融资合同被穿透认定为有效民间借贷合同,则应当根据民间借贷合同适用的本金、利息计算规则认定借款本息。相较于原合同约定,可能产生变化主要有两点:
一是,名为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的,通常有预先支付保证金、预收租金或预先支付融资顾问费等相关条款。如企业依约支付相应费用,则可主张其构成“砍头息”,应在本金中扣减[例如,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初1806号案[12]]。但是,针对融资顾问费等服务性费用,如有证据证明出借人提供了相关服务,相应费用也可能无法在本金中扣除。例如,(2021)京民终804号案中,北京高院认定案涉融资租赁合同实际构成民间借贷。借款人主张出借人放款前收取的管理费、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在本金中扣除。法院认为双方签署投资顾问协议约定相应费用,借款人出具融资服务接收确认书,载明确认出借人完全履行了投资顾问协议约定的义务,接收到出借人无任何瑕疵的融资顾问服务,故不支持相应费用在本金中扣减。
二是,根据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原合同约定的融资本金之外的溢价金额,经折算后的利率不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LPR的4倍(如适用旧《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则不超过年化24%)则予以支持,超出的部分依法调减。例如,(2022)豫15民终3608号案中,孙鹏与昱达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孙鹏向昱达公司提供20万元投资经营案涉项目,到期后收回本金20万元和收益8万元。信阳中院认定,孙鹏在合同下不参与案涉项目的经营管理,存在只享有利润、不承担风险的情形,案涉合同实际是以投资名义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协议约定的投资期限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4月30日实际为借款期限,收益8万元实际属于利息,但金额超出了按照LPR的4倍计算的利息上限,超出部分昱达公司无需向孙鹏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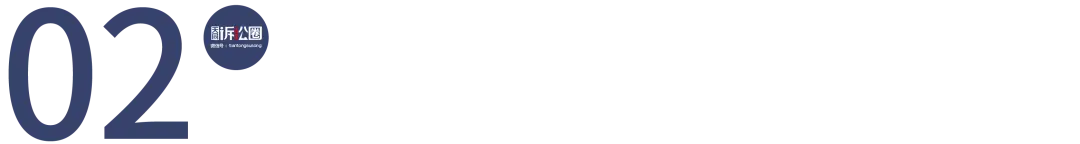
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风险
(一)虚假民间借贷纠纷的识别
民间借贷纠纷是虚假诉讼的高发领域。根据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8条,如下四大类情形出现时,民间借贷纠纷可能涉嫌虚假诉讼,应当由法院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综合认定是否确属虚假诉讼:
1、出借人不具备出借能力,起诉依据的事实理由明显不合常理,或者不能提交债权凭证/凭证涉嫌伪造;2、借贷双方一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或者对借贷事实没有任何争议/诉辩明显不合常理;3、任意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且代理人对借款事实陈述不清或前后矛盾,不正当放弃权利,或者在其他纠纷中低价转让财产;4、借款人配偶或合伙人、案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等。
(二)民营企业可能遇到的典型虚假民间借贷纠纷
1、出借人通过循环转账虚增借款金额。
此情形下,如出借人不能对短时间内通过多轮循环转账形成的大额借款债权进行合理解释,则很可能被认定为涉嫌虚假诉讼、移送公安。例如,(2020)豫民申7218号案中,出借人、借款人和案外人于短时间内在同一家银行完成18笔转账交易,借款人银行流水显示的最终借款金额高达900万元,远超过实际转入其账户的270万元。出借人对此未作合理解释。河南高院认为本案涉嫌虚假诉讼和“套路贷”刑事犯罪,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
2、债务人与关联方串通,虚构其对关联方的民间借贷债务,通过虚假起诉、虚假调解,使关联方抢先进入执行,以规避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划扣资产。
此情形下,债务人与关联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往往缺乏证明借款事实的相关证据,双方的庭审往往不具有对抗性,陈述通常高度一致,甚至不经庭审就快速达成条调解。部分情况下,债务人还可能与关联人直接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不经常规诉讼程序、直接进入执行。其目的就是让关联方取得早于债权人执行债务人财产的时间利益,避免真正的债权人划扣债务人资产。
例如,最高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案(最高法院2016年第14批指导案例之68)中,欧宝公司起诉特莱维公司返还借款本息。法院查明,第一,两公司的高管存在混同、普通员工也不做区分,实际共同服从王作新一人指挥,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第二,欧宝公司对其与特莱维公司的借款关系的事实细节陈述不清,对借款时间、借款数额的主张前后矛盾,起诉特莱维公司后仍然与之进行多笔资金往来等,存在诸多异常。第三,两公司均明确知道特莱维公司对案外人谢涛等欠付债务。欧宝公司对特莱维公司申请执行后,不同意法院拍卖查封房产、允许特莱维公司继续销售,并随着房产的销售成功而申请相应房产解封。最终,法院经案外人谢涛申诉,认定两公司系恶意串通起诉损害谢涛合法权益,构成虚假诉讼。
3、债务人与关联方刻意约定债权人申请执行债务人的法院所在地为双方借款合同的签订地,约定纠纷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
此情形下,债务人与关联方可能均与债权人申请执行债务人的法院所在地没有关联,而关联方对债务人的债权金额也完全由双方协商确定,唯一目的就是服务于级别管辖。通过精心设置,保证关联方能够与债权人在同一法院执行债务人;同时通过快速调解,保证关联方能够抢在债权人申请执行债务人之前,与执行法院建立联系,在执行程序规避对债权人的履行,尽可能为债权人实现债权创造障碍。
(三)参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法律后果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5条、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9条,当事人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法院将驳回诉讼请求、不允许原告申请撤诉,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6条,当事人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诉讼、仲裁、调解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条,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78条的规定,如下情形均属于应予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范畴:一是,当事人单独或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民间借贷债权债务起诉,导致法院因此采取保全措施、开庭审理、作出裁判文书、制作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基于捏造的债权债务作出的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书,或导致当事人自身因此被采取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或遭受刑事追究的;二是,当事人多次捏造民间借贷债权债务起诉的。
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因参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而可能受到的刑罚包括罚金、拘役、管制或有期徒刑(最高可达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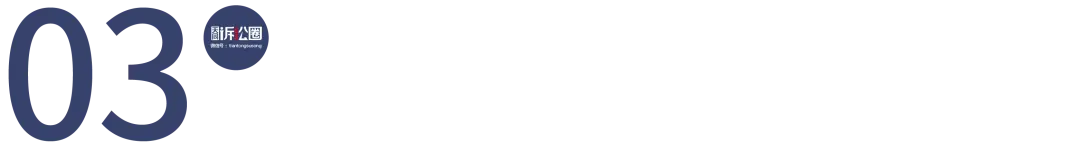
风险防范建议
(一)关于各类融资合同的穿透审理
民营企业作为融资一方签订各类合同时,应当特别注意合同约定的内容是否与合同名称载明的合同性质具有一致性。
1、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合同。可以预见的是,根据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相关精神,该等合同将较为统一地按照金融借款合同处理,再难被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目前,参考《民间借贷解释适用范围批复》对地方金融组织从事相关业务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态度,实践中,金融借款有更大的可能适用比民间借贷更高的利率上限(年化24%)。民营企业融资人未来在此类合同下要承担的利息偿还风险将进一步扩大。建议企业尽可能与出资主体充分磋商,考虑签订更为直接的企业借贷合同。
2、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民营企业通过保理、融资租赁业务获取融资的时候,应当特别注意保理合同是否与应收账款紧密关联、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具有“融物”的明确属性。
假设民营企业在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下被追索融资款,建议首先分析相应合同有无可能被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合同,如有,通过进一步挖掘保理商、融资租赁公司有无职业放贷、非法转贷等情形,或有机会争取合同无效、免于归还合同约定的融资利息。
当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被穿透为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建议民营企业积极主张预先收取的保证金、租金、服务费、咨询费等属于“砍头息”,应在本金中扣减,同时注意合同约定的融资成本是否突破了民间借贷合同的利率上限。
3、买卖合同。民营企业作为实际用资人通过循环贸易实现资金融通的,难以避免依据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向出资人承担还款责任。此时,建议民营企业关注出资人是否可能存在职业放贷或非法转贷情形,判断相应民间借贷合同有无可能被认定无效。
当民营企业作为出资人、用资人以外的主体参与循环贸易、协助完成资金过桥时,根据民营企业的具体签约内容、闭环链条上各方的实际履行行为,其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债务加入人[例如,最高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59号案[13]]、担保人[例如,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88号案[14]]或仅仅是资金通道方[例如,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03号案[15]]。
其中,资金通道方可能承担的责任最轻,其在配合上下游完成资金过桥后即履行完毕合同义务,在实践中往往仅基于对循环贸易的协助、促成而承担一定比例的过错责任(常见为补充责任)[例如,南京中院(2018)苏01民终5129号案[16]、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03号案[17]],甚至有机会争取免责[例如,最高法院 (2017)最高法民申1672号案]。
当民营企业系贸易闭环上非用资企业的中间人,为尽可能减轻企业未来的或有责任,我们建议的民营企业在签约、履行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以自有资金为垫付合同款项,避免让下游企业支付的合同价款在自有账户上趴账,避免向上游企业直接出具还款承诺文件或债务确认文件,考虑与上下游企业另行签订协议或向上下游企业出具单方函件,明确自身仅为资金过桥方。
4、合资/合伙/增资合同。民营企业因此类合同陷入纠纷的,如对方能够基于投资金额获得固定收益,不承担合资、合伙、增资的投资风险,无需履行相应的经营管理义务,应当积极主张相应合同的实质属于民间借贷,调减超出民间借贷法定利率上限的应支付“投资收益”。
(二)关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
参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纠纷将依法承担较为严重的民事甚至刑事法律责任,任何情形下我们均不建议民营企业参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
如果民营企业遇到债务人为逃废债而与关联方开展虚假诉讼、损害企业利益的情形,可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法发〔2021〕10号)第5条和第8条的规定,向检察院申请对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进行检察监督。
因民营企业并非虚假诉讼的当事人,相关虚假诉讼常采用调解方式结案,具有保密性,民营企业较难掌握实锤资料证明相应诉讼虚假,但仍可基于虚假诉讼常见的如下异常特点,摸查相关线索:
1、起诉时间晚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履约争议;2、标的金额较大,能覆盖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争议标的;3、案件不会经过管辖权异议程序;4、立案之后迅速调解、执行;5、债务人与关联方存在大量往来交易,进入诉讼后也不中断资金往来;6、关联方通常能够查封债务人各种类型的资产,且均极具价值;7、关联方往往选择优先处理债权人轮候查封的资产,以尽可能排除债权人受偿;8、关联方可能主动放弃查封债务人无价值的资产;9、关联方可能不同意采用司法拍卖的方式处置债务人资产,交由债务人自行处置。
注释:
[①] 参见刘贵详:《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载《法律适用》2023年第1期。
[②] 同注释[1]。
[③] 北京高院(2019)京民终1432号案。北京二中院一审认为:“上海邦汇公司与深圳恒波公司虽签有保理合同,但完全不符合保理法律关系的特征,保理合同的内容应为双方虚假的意思表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为借贷法律关系。,故案由相应变更为民间借贷纠纷。”北京高院二审认为:“关于本案案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上海邦汇公司不属于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法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
[④] 山东高院(2021)鲁民终2289号案。山东高院认为:“涉案《国内商业保理合同》不符合保理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本案真实法律关系为借贷法律关系。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根据晨鸣公司营业执照载明的营业范围,仅包括‘融资租赁业务’‘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两项金融业务及‘经营性租赁业务’等四项经营业务,而本案涉案业务系借贷法律关系,不属于晨鸣公司经营范围,故本案纠纷不属于晨鸣公司从事的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同时,晨鸣公司经营范围中亦不包括金融借贷业务,故本案应当依据民间借贷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⑤] 如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则为第14条。
[⑥] 北京高院(2019)京民终1432号案。北京高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上海邦汇公司不属于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一审法院认定本案系法人之间的资金融通行为,确定本案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认定无效。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出借人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即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对于以借贷为业的认定,应当考量同一出借人是否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向不特定对象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即放贷人未经批准,向不特定对象反复性、经常性放贷,贷款目的具有经营性。经营即常态模式,如果是偶尔为之,则不能认定为经营。据此,案涉合同是否无效,应当考察上海邦汇公司是否违反上述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事了向不特定对象反复性、经常性的放贷行为。”
[⑦] (2018)最高法民再373号案。最高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主张。华纳公司、大江公司主张案涉合同无效所引用的均不是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不符。工银公司如果违反监管规定,其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并不当然影响案涉民事合同的效力。华纳公司、大江公司无证据证明案涉合同具有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因此,华纳公司、大江公司、建行开发区支行关于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⑧] 上海金融法院(2021)沪74民终323号案。上海金融法院认为:“被告中民公司辩称,原告并非具有放贷资质的金融机构,故本案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中民公司从事的是单笔资金拆借,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原告存在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的对外放贷行为,故被告中民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商务部发布的《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虽规定:未经相关部门批准,融资租赁企业不得从事同业拆借等业务。但该部门规章尚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本案借款合同无效。鉴于本案借款合同并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故应认定为有效。”
[⑨] 安阳中院(2022)豫05民终2350号案。安阳中院认为:“关于案涉《融资租赁合同》《买卖合同》等的效力及法律效果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在经未批准的情况下,上诉人以融资租赁的形式向滑县仁和医院贷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上诉人与滑县仁和医院之间的借贷关系应属无效。”
[⑩] 郑州中院(2020)豫01民终2851号案。郑州中院认为:“本案各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实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鉴于上海安平公司是从事融资租赁的企业,并非有权从事经营性贷款业务的企业,故《融资租赁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从事金融借贷业务这一非法目的,且针对不特定的多人,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11] 上海高院(2016)沪民申2374号案。上海高院认为:“《管理办法》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等制定,依照国务院相关政策规定,区内商事主体开展商业活动应遵守《管理办法》。因涉案业务发生于《管理办法》有效期内,且《管理办法》第六条明确规定从事商业保理业务的企业不得从事发放贷款或受托发放贷款等业务,故二审法院据此认定卡得万利公司和佳兴公司之间名为保理实为借贷之借款关系无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12] 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初1806号案。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案涉交易缺乏‘融物’法律特征,本案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工银租赁公司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向中民租赁公司发放融资款,并按期向其收取成本及利息,符合借款法律关系。中民租赁公司与工银租赁公司因《融资租赁合同》签订《资产管理咨询合同》、《租赁结构安排及管理咨询合同》,并于2017年12月12日向工银租赁公司支付的咨询费、咨询安排费共计5,936,000元。因本案不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当事人也未举证证明咨询服务方提供过实质服务,故上述费用应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
[13] 最高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559号案。最高法院认为:北方风驰公司提供资金通道作用,《付款承诺函》系北方风驰公司同意就部分未支付的运费及超期滞纳金向天津华捷公司承担给付责任,系其自愿承担有关风险及法律后果的真实意思表示,北方风驰公司应当受该承诺函约束,与借款人包头禄祥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北方风驰公司虽然并非案涉借款的实际用款人,但其明知天津华捷公司与包头禄祥公司之间进行企业拆借,仍参与其中,原审依据北方公司出具的承诺判令其与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14] 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888号案。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宇航公司、中船公司、斯创姆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下付款、交货情况,结合二审中双方均认可无实际交货的事实,一审法院将本案认定为循环贸易式融资法律关系正确。各方以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买卖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以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融资法律关系并无无效事由,应为有效。斯创姆公司通过高买低卖,以买卖价差的形式向中船公司和宇航公司支付用款利息,宇航公司和中船公司因此而获取相应利息收益。即宇航公司是出资人,斯创姆公司是用资人,中船公司是中间方,实际承担担保功能。
[15] 最高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103号案。最高法院认为:当事人通过通谋的虚假意思表示规避法律并导致合同无效时,各方当事人均有过错的,应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康灿公司与蓝海公司成立民间借贷合同关系。工艺品公司、家具公司均认可案涉封闭式循环买卖实际系资金拆借活动,其参与案涉交易系为案涉借贷行为的完成提供帮助,分别与蓝海公司、康灿公司之间成立以协助、掩饰上述民间借贷行为为内容的事务处理合同关系。在民间借贷合同关系被确认为无效后,康灿公司作为借款人应将其收取的款项返还给蓝海公司,并向蓝海公司支付因其实际占用该款项而产生的法定孳息。工艺品公司等参与采购合同系为帮助、促成民间借贷交易而实施的虚伪意思表示,亦负有向蓝海公司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康灿公司返款借款并支付利息,工艺品公司对康灿公司、宁某、陈某某上述给付义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11%的补充赔偿责任。
[16] 南京中院(2018)苏01民终5129号案。南京中院认为:虽然各方均明知交易模式,但各方当事人在交易模式中的作用、地位不同,通道方与债务人的责任显然应当予以区分,否则不足以体现对价原则。通道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主要有两种构造方式:(1)以连带责任担保为构造。主要理由:其一,从交易模式的设置来看,对债权人而言,增设通道方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债务人的资信。其二,从该交易模式的构造而言,通常由通道方直接与债权人签订合同、向债权人承担责任。可认定通道方以自身资信为债务人提供担保。担保方式约定不明,应为连带责任担保。其三,通道方明知交易构造仍积极实施且获得收益。因此债务人应承担还款责任,通道方应承担连带责任。(2)以合同相对性为构造。主要理由:其一,通道方直接与债权人签订合同,是合同的相对人,且通道方无证据证明债权人明知实际借款人。其二,各方当事人未合意,如资金链中断,应由谁向债权人承担还款责任,或者债权人同意除实际用款人外,通道方免于承担还款责任。因此通道方应根据合同相对性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合同相对性构造的前提是债权人不明知实际借款人,在融资性贸易中,债权人通常是交易模式的发起人、设立人,其不知道实际借款人的情形显然不多。连带责任模式将通道方加入交易的意思表示认定为担保,明显违背通道方真实意思表示,也缺乏依据。鼎牧公司不仅仅是交易构成的一环,作为通道方,鼎牧公司应承担补充责任。理由如下:其一,各方均明知交易模式仍积极参与构造、履行,存在过错,但各方过错程度不一,应根据各方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其二,民间借贷中,债务人陈铸粮管所的还款责任是第一顺位,作为通道方的鼎牧公司,其过错轻于债务人,因此其责任不应与陈铸粮管所相同,不应承担共同或连带还款责任。其三,鼎牧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长期从事通道业务。其四,从收益分配来看,鼎牧公司收取的通道费用占债权人果品公司的利息比例长期维持在40%左右,比例较高。其五,从案涉交易模式构造上来看,鼎牧公司与果品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由鼎牧公司向果品公司支付货款。更为重要的是,鼎牧公司事先出具《收货证明书》,认可果品公司交付的货物符合约定,并保证在2016年11月17日前付清货款。可以认定果品公司借款本息未能如期收回的结果系债务人陈铸粮管所主动违约与鼎牧公司过错共同作用而产生。综上,根据鼎牧公司过错程度,其责任应低于债务人陈铸粮管所,高于中介或受托方,符合补充责任构成的一般法理。
[17] 同注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