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天同律师事务所深圳办公室担保实务疑难问题研究课题组:陈耀权、齐昕、何雅婷、王艺洁、唐思雨、黄晓林、陈琪
特别鸣谢:何慕宇、陈昕、袁荃
转发本文并扫描文末二维码提交信息,即有机会获取纸质版《公司担保争议解决双年观察》和《上市公司担保合规审查指引手册》(2022年修订版),此前已提交的无需重复提交。
重磅预告:我们将于2022年12月2日(周五)下午15点就“决议例外与无效后果”主题开展线上分享活动,届时可通过“无讼律师”APP搜索“公司担保疑难热点问题分析及风控处置”课程,或通过“腾讯会议”APP(会议号:232-305-288)参与。欢迎感兴趣的业界同仁关注和参加!
前言:
如授权有瑕疵而相对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担保并不必然归于无效,早在《九民纪要》时期,第19条就已引入决议例外,基于担保“符合公司利益”的大原则,在特定情形下推定担保系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在坚持以往政策取向的基础上,对“符合公司利益”的范围进一步限缩;结合案例,我们将会就规范之间差异、新规溯及适用效力以及新规适用要点进行探讨:
其一,主体类型差异可能影响到权限推定。法定基准之外,法院或从交易常识重定相对人信赖,从而扩张适用该等例外,其间尺度如何把握?其二,控制关系差异可能影响权限推定。新规尺度自第8条从“直接或间接控制”转为“全资”,当如何理解?是否及于间接控制的二、三乃至多级公司?其三,担保类型差异可能影响到权限推定。“三分之二以上”要求之下,针对关联担保,签字人员是否应当排除应回避股东?
如法院认定构成越权担保,又不满足决议例外,则担保合同终会被认定为无效,问题就转入无效责任应当如何认定及分配。
非上市公司场合,《担保制度解释》第17条对《九民纪要》第20条的一般模式与免责事由予以重整。针对公司担保而言,争议集中于:公司担保因越权代表而无效,担保人公司与债权人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除去过错,裁判实践中是否会、以及考量何种事实因素?本章结合案情背景、利益格局,还原法院就担保、公司内部、公司外部三层法律关系下对应因素的权衡与考量。
上市公司场合,《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第2款一概免除了担保无效时的公司责任,故比例分配仅在存量纠纷范畴有探讨意义。前述条款为创制性规则,基于对相对人合理预期的保护,原则上不应当溯及适用,但实践中也不乏以《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中“上市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表述为支点,而抗辩存量纠纷中担保人免责的观点。对此,我们将基于事实模型和裁判依据的不同,呈现法院的类型化、倾向性处置思路。
第一部分 公司担保的决议例外
第一节 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法》之所以规定担保须经决议,意旨在于:属于无偿行为的担保本不属于日常交易类型,且有着损害公司清偿能力的较大风险,法律在政策上将授权预先保留给法定机关。
但该等预设显然不适用于以担保为业的特定领域机构。《担保制度解释理解与适用》对此明确:
“以担保为业的公司不属于《公司法》第16条的调整范围。”[1]
出于该等考虑,《担保制度解释》以设定决议例外的方式对授权保留范围予以调整。然而,该等调整本质上仍须以惯常业务范围为限。以下分别就金融机构与担保公司进行讨论:
其一,区别于担保公司,最高院仅有限扩张地将金融机构的“保函业务”纳入例外。《担保制度解释理解与适用》对此明确:
“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无须决议,是由于保函业务属于金融机构的标准化业务,是金融机构从事的日常经营活动。”[2]
其处理思路与《担保制度解释》第11条第2、3款实质匹配:[3]
《担保制度解释》第11条第2、3款:“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在其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内开立保函,或者经有权从事担保业务的上级机构授权开立保函,金融机构或者其分支机构以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未经金融机构授权提供保函之外的担保,金融机构或者其分支机构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未经金融机构授权的除外。
担保公司的分支机构未经担保公司授权对外提供担保,担保公司或者其分支机构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未经担保公司授权的除外。”
《担保制度解释理解与适用》对此明确:
“(比照《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第1款第1项逻辑)如果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记载有保函业务,则应视为金融机构已对该分支机构进行了概括授权,其开立保函行为无须经公司决议授权……”[4]
然裁判实践中,基于个案事实,法院将相对人信赖因素纳入考虑,从而避免对上述限制的严格适用:
如(2021)新2825民初564号案中,某公司(担保人)向第三人(担保权人)提供担保。经查其经营范围并不包含担保内容,且所涉担保类型也并非保函。法院虽在主文中援引《担保制度解释》第11条,但并未遵循“保函”乃至经营范围约束,而认定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还原其背景,不排除原因在于,担保权人是农民,被担保债权本就是农民在此前农业合作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另如(2021)湘01民终14399号案中,为保证A公司(出租人)与杨某(承租人)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的有效履行,B银行(次承租人)为杨某在租赁合同下的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法院以B银行“系案涉房屋的实际使用者,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亦是直接向林某某(案涉房产产权人)支付租金”为由,认定林某某对案涉担保有合理信赖,担保有效。
其二,相较于金融机构的决议例外与其分支机构授权例外口径基本一致,担保公司虽有决议例外,但其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却一概需要取得特别授权。
从裁判实践情况看,法院对该等担保公司分支机构授权的把握是相对宽松的。如(2019)鲁民申4890号案中,山东高院认定:担保公司概括授权分支机构从事担保业务,分支机构无需再就单笔担保业务征求总公司的授权。
第二节 被担保人与担保人的利益高度一致
与上述“担保人身份特殊性”的机制不同,“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强调的是被担保人与担保人的利益高度一致。
此前《九民纪要》仅要求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存在控制关系即可(“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但控制关系不必然能够与收益的分配关系呼应,故不必然满足利益高度一致的预设。基于该等考虑,《担保制度解释》将标准从此前的“控制”提高到“全资”。
实践当中常见的问题是,所谓“全资子公司”,是否及于间接控制的二、三乃至多级公司?该概念在理解上,可以比照上市公司监管规则对全资子公司的界定,不以一级为限。裁判实践中亦有法院持此观点,如(2021)鲁02民初1116号案中,母公司直接持有子公司99.5%股份,并通过另一全资子公司持有该子公司0.5%股份。法院参考上市公司监管规则,认定子公司这一概念本就不限于一级子公司。
须注意的是,对于存量业务,仍有法院适用《九民纪要》规定处理,如(2021)京02民初309号案:
“根据合同签订时的法律规定,公司为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即便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没有公司机关决议,也应当认定担保合同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第三节 公司意思表示载体的实质替代
公司决议有着严格的召集、通知、表决及形成的程序要求,交易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严格遵循。基于该等考虑,现行《公司法》第37条第2款另外引入“决定”作为替代。但该等决定有着非常严格的适用要求:股东须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
《公司法》第37条第2款:“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因此,《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第1款第3项也并非对《公司法》第37条第2款项下“决定”的明确。而是在同意人数未达决定要求,亦未取得决议情况下的例外放宽。
其中的“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要求,是比照重大事项决议的绝对多数决而定。进而,引出以下问题:
其一,就“关联担保”而言,其“三分之二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的计算基数是否排除应回避的股东。《担保制度解释理解与适用》对此持肯定态度,[5]但在裁判实践中多有分歧,不乏计入应回避股东者,如(2020)豫0725民初3893号案。[6]
其二,《公司法》上重大事项表决比例为“就高不就低”,允许公司通过章程调高限制。在特约比例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推定公司意思便欠缺正当性。对此,我们认为,如特约比例超过三分之二,不应当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第1款第3项。
第四节 删除商业合作关系的兜底事由
商业合作关系兜底,根本上有违《九民纪要》第19条限制法院任意裁量的初衷;以所列举的相互担保为例,通常涉及诸多因素考量,类似商业判断不应由法院作出。《九民纪要》颁布以来,司法裁判在商业合作关系(特别是该项所明确列举的互保)呈现出了差异化观点,也正印证了这一规范模式的操作难度。[7]为克服裁量上的不统一,《担保制度解释》彻底删除了商业合作关系这一兜底事由。
在裁判实践中,针对存量案例,仍多见法院借此突破法定列举的严格限制,如(2021)粤06民终14327号、(2022)鲁15民终70号案;特别是针对历史遗留案例,交易之时各方对决议要求本无预期,为克服《九民纪要》相关规则对交易安全造成的消极影响,法院倾向于利用“商业合作关系”这一兜底事由去为相对人找补担保效力,技术处理上极具政策性,如(2021)甘民终155号案。
但与此同时,亦不乏严守立法目的从而限缩该兜底事由的尝试,如(2020)京民终700号(二审)排除互保商业合作关系对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的适用,在该案的再审审查程序((2021)最高法民申5089号)中,最高院对此一理解予以确认,“该规定(《九民纪要》第19条第3项)仅针对存在相互担保商业合作关系的非关联公司之间的担保法律关系。关联公司之间相互担保的情况较多,如果豁免公司机关决议,将容易导致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权益受到损害”。
第二部分 担保无效责任的认定与分配
第一节 非上市公司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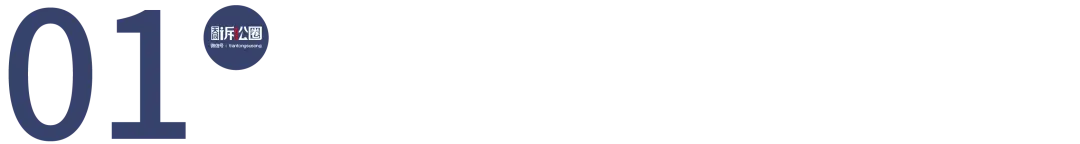
历史沿革
《九民纪要》之前,非上市公司担保无效责任根据《担保法解释》第7条和第8条处理。该两条根据主合同效力状态区别规定,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各方主体的过错状态,确定分配比例:[8]
《担保法解释》第7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担保法解释》第8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为配合公司担保纠纷处置模式的整体调整,《九民纪要》专就公司担保无效责任引入第20条。在延续上述一般模式的基础上,该条另设两项豁免担保人责任的特殊规定(即“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与“明知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从而形成了该阶段的公司担保无效责任规范格局:
《九民纪要》第20条:“【越权担保的民事责任】依据前述3条规定,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按照担保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关于担保无效的规定处理。公司举证证明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或者机关决议系伪造或者变造,债权人请求公司承担合同无效后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担保制度解释》发布后,其第17条(以下简称第17条)对前述规则做了根本性的调整:法定代表人作为法人机关,以公司名义越权担保,也意味着公司在选任监督上存在过错,其不得依据债权人的过错而免责,并因此删除了“债权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时担保人不承担无效责任”的规定:[9]
《担保制度解释》第17条:“主合同有效而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形确定担保人的赔偿责任:
(一)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二)担保人有过错而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三)债权人有过错而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主合同无效导致第三人提供的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其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因此,在非上市公司担保场合下,实践中涉及的主要争议问题便在于,如何确认担保人承担责任的具体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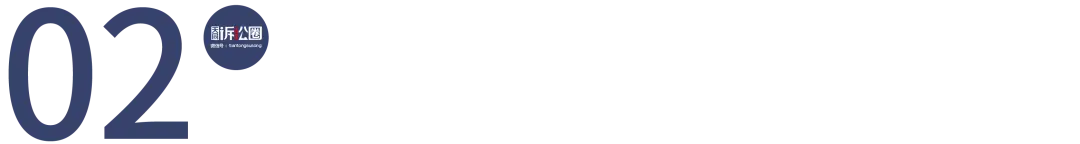
场景解读:如何确定担保人承担责任的具体比例
在非上市公司担保的场合,担保合同自身的效力瑕疵通常在于越权代表。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并非讨论重点;越权代表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以债权人与担保人均有过错为前提,原则上仅涉及第1款第1项的适用问题。
对此,最高院在多本释义中均强调,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仅仅是担保人责任的上限,具体责任比例应当视个案中债权人、担保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10]
裁判实践中,主体过错如何评价,过错之外是否另有规定文义未能包含的其他考量因素,我们将在下文中结合具体案例作类型化阐述:
(一)多数案例中,法院会直接按照二分之一责任上限下判,较难从正面反映出影响裁量尺度的因素
较为典型的认定思路是,公司对外担保不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决议要求,且存在公章监管不力、人员越权等内部管理问题,导致债权人对缔约外观产生了信赖;债权人未对决议尽到审查义务,故双方均有过错,公司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以(2020)最高法民申5944号案为例:
“本案中,案涉担保合同虽系无效,但A公司(担保人)相关董事就案涉担保事项出具了董事会决议,曲某(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作为A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在涉案《不可撤销担保函》《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加盖了私章及公司印章,并在《不可撤销担保函》中承诺为债权本金2亿元及利息、违约金等承担保证责任,对于上述对外实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A公司均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存在管理不当的过错责任,有区别于单纯由法定代表人实施的擅自对外担保行为,因此A公司应就因担保合同无效导致B公司(债权人、担保权人)信赖利益受损承担赔偿责任。由于B公司对担保合同无效也负有审查不严的过错责任,本院认为,二审法院判决A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为C公司(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50%,并无不当。”
(二)在担保人责任比例低于二分之一的案例中,结合事实背景、利益格局,印证法院说理,可还原影响责任比例的其他三重要素
第一层:担保法律关系与相对人过错
无效责任的本质是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损失。如果相对人未尽法定注意义务,并因此未对交易形成合理信赖,法律不能使其取得如同交易实际发生一般的经济效果。第17条第1款第1项规定“担保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是明确担保人基于自身过错所应承担责任的上限;上限之下,担保人责任比例,仍有可能受到相对人过错的影响而被进一步压缩。具体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相对人特殊身份
相对人为专业金融机构,如银行或担保公司,其熟悉担保审查中所需的资料与流程,有意识、有能力辨别案涉担保的效力瑕疵,却接受了存在明显瑕疵的越权担保。因此,其对于担保合法有效的信赖基础较弱,过错较重,担保人的责任比例也相应降低。
特别是在金融机构监管要求、行业指引乃至是相对人内部规程已对担保审查提出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法院极有可能会比照该等要求确定金融机构的注意义务。即便实际履行情况较市场通行操作并无过分偏离,但如以专业机构标准审视已有极端异常,过错认定仍会比照后者进行。
在最典型的场景中,法院直接将相对人的专业性与其过错程度绑定。如(2020)最高法民终1228号案,上市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未出具股东大会决议,法院认定,作为专业金融机构(银行)的相对人未尽到审查义务,应被“视为知道”案涉担保越权,对担保无效负“主要过错”,进而需对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承担10%的赔偿责任:
“A公司、B公司(上市公司、担保人)与D银行(债权人、担保权人)签订《保证合同》为C公司(债务人)提供担保,应当经过股东大会决议。但实际上,A公司、B公司均未召开股东大会对案涉担保进行决议。该行为不仅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也违反了公司章程。D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保证合同》是否经A公司、B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未进行审查,应视为其知道《保证合同》系A公司、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其不属于善意相对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该代表行为无效。……D银行在知道A公司、B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未经公司机关决议的情况下与两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对《保证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过错责任。A公司、B公司虽无需就《保证合同》承担担保责任,但其存在人员、公章等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对于《保证合同》无效亦有一定过错。综合考虑本案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一审判决酌情确定A公司、B公司分别对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债务向D银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维持。”
又如(2021)豫15民终2412号案:
“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债权人、担保权人)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负有更为审慎的义务,在知道某公司(担保人)对外提供担保未经公司机关决议的情况下签订案涉《保证合同》,对案涉《保证合同》无效负有主要过错。……综合考虑本案情况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某公司对上官某(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债务向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在部分案例中,法院虽然未明确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相对人过错程度较高,但在无其他特殊因素时下调担保人的责任比例,可以推断相对人特殊身份对责任比例的下调有着潜在影响,如(2021)苏0826民初4695号案(其他类似案例参见(2021)苏0826民初1741号案):
“原告(担保人)作为专业的担保机构,在被告未提供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接受被告某公司(反担保人)的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是非善意的,存在过错,被告某公司在反担保协议上盖章,但却未提供股东大会决议,导致反担保协议无效,也存在相应的过错,本院根据各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被告某公司承担不能清偿部分的五分之二的赔偿责任。”
相对人的过错是针对担保无效原因而言的,根据具体案情的不同,无效原因除了违反决议审查的要求外,还包括不满足约定生效条件。若相对人基于其专业性,本可大大提高条件成就的可能性,但因疏忽使得条件落空,则过错较重,应适当降低担保人的责任比例。如(2021)豫1522民初2915号案,公司作为反担保人对外提供反担保,约定生效要件为有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章,(接受反担保的)相对人未要求反担保人进行面签,导致签字系伪造,法院因此认定,相对人未尽到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结合本案实际情况”“酌定”反担保人承担三分之一责任:
“案涉反担保合同约定的生效要件是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公司公章或合同专用章,该反担保合同虽然加盖了A公司(反担保人)公章,但原法定代表人吴某签字经鉴定系非本人所签,且无证据证明该签名系吴某授权他人所签,故该反担保合同不符合合同生效要件,属无效合同。……本案中,原告B担保中心(担保人、反担保的相对人)在办理反担保合同过程中,安排由借款人持合同找反担保方被告A公司签字盖章,虽加盖了A公司公章,因原告对提供反担保的被告A公司没进行面签,导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的签名非本人所签,原告又不能证明反担保合同的签名系吴某授权,故原告在签订反担保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必要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对反担保合同无效的造成有一定的过错;反担保合同上所加盖的公司公章经鉴定系A公司的印章,说明被告A公司在公章管理上存在不当,对合同的签订亦存在过错。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定被告A公司承担1/3的补充赔偿责任。”
2. 授权瑕疵的明显程度
第17条虽排除了“相对人明知无权限”这一担保人完全免责的特殊事由,但相对人的明知状态对无效责任分配有颇为实质的影响。明知状态往往又得以通过客观上瑕疵的明显程度印证。因此,法院通常也会结合相关事实因素,酌减担保人的责任比例。
常见的,担保人自行披露授权瑕疵的情况,如(2022)豫1503民初1979号、(2022)豫1503民初1980号案中,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相对人,不仅未基于专业性而审慎审查,而是在《担保承诺书》明确提示“未经原行党委会决定”后,仍未要求担保人出具决议,在内外两个因素的叠加下,相对人的过错程度上升至“重大过错”,担保人的责任比例也进一步降低至30%:
(2022)豫1503民初1979号:“至于被告A商业银行(担保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责任比例:原告B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债权人、相对人)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贷款审查所需资料和流程是清楚的,然其作为贷款审批机构,明知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需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却未要求被告A银行提供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从涉案贷款档案内容可见,原告已要求债务人(被告C公司)提供《股东决定》,且被告A商业银行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也明确提示“未经原行党委会决定”字样。而原告B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仍然放任且未要求被告A商业银行提供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故此,B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怠于履行其审查职责,对担保无效存在重大过错,应减轻被告A商业银行的赔偿责任,故由被告A商业银行承担30%赔偿责任为宜。”
第二层:公司内部关系及股东权益保护
《公司法》第16条对担保授权予以保留,本旨在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因越权代表导致担保无效的情况下,中小股东利益仅能通过担保人责任的酌减来实现反射性保护。
因此,法院在分配无效责任时,往往将中小股东保护因素纳入考量,以酌减责任比例作为《公司法》第16条本旨的替代(即便是不充分的)实现方式。
其一,当法院说理涉股东利益保护这一因素时,又会有两种不同的呈现方式。第一种为直白地展现股东利益与担保权人利益冲突,并在过错及责任比例认定中体现法院的价值判断。典型如(2021)沪01民终3161号案,公司为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无决议。法院在说理中强调该越权担保“损害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认定未尽到审查义务的“担保权人存在较大过错”,并据此“酌减”公司责任:
“A公司(担保人)为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贾某某(债务人一,持股60%)及其成立的一人有限公司B公司(债务人二)对外提供担保,未经B公司其他有表决权的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进行担保,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公司法》第16条),损害了其他股东及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担保合同应认定为无效。……本案中,C公司(债权人、担保权人)接受A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股东贾某某及其成立的一人有限公司B公司的债务提供担保,但未依照法律明文规定,对该担保是否取得A公司其他股东形成有效的同意作出担保的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审核义务,存在较大过错,相应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担保无效的过错因素及过错程度,酌定A公司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范围应为上海星鲨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第二种相对委婉,法院将涉及其他股东利益的事实作为降低责任比例的依据之一。如(2021)京0115民初25921号案中,公司为股东提供关联担保,加盖公章,但未出具决议,法院提及另一股东未签字,并根据“本案实际情况”认定公司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三分之一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虽然某公司(担保人)在《收据》中盖章,但该收据仅有李某某(被担保股东、债务人)签字,并未有另一股东郑某某签字,且苏某(债权人、担保权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对公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善意情形,故案涉担保行为对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对于苏某要求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因苏莫、某公司对于担保合同无效均有过错,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确认某公司应承担李某某不能清偿债务部分的三分之一责任。”
可以推断所谓“本案实际情况”即为对另一股东的倾向性保护:一方面该担保未经另一股东同意,违反其意志;另一方面担保权人诉请公司承担责任,通常此时被担保股东已无力偿还债务,则偿债压力转移至公司,若让公司承担较高比例的缔约过失责任,则另一股东的利益也会间接受损。
又如(2019)川1503民初1355号案,公司提供非关联担保,加盖公章,一股东已签字同意,法院提及公章的使用未经其他股东同意、有其他股东时担保权人需审查决议,从而认定担保权人存在“明显过错”,并“酌情”认定公司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责任:
“蒋某某(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股东)作为某公司(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在没有经过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公司印章对外进行民事担保,其行为构成越权代表;债权人明知各方在签订《借款协议》时,担保人某公司有其他股东,其负有对担保人公司内部决议进行形式审查的义务,在蒋某某没有提供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与之签订担保合同,该担保合同无效。关于双方的过错问题,债权人对某公司是否提供股东会决议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存在明显过错。同时,公司印章作为公司意志代表的重要载体,任何公司对其公章均负有妥善保管以及用印授信管理的责任。本案中,某公司对公司印章的使用亦存在管理不当的过错。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因郑某(债权人)与某公司均存在过错,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情认定某公司对主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赔偿责任。”
我们认为,法院所斟酌的情理与(2021)京0115民初25921号案也并无二致。
其二,法院说理未能反映下调责任比例的影响因素,但在事实查明中强调公司的股权结构时,则表现为法院对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倾向性保护。如(2022)浙0212民初603号案:“另查明,某公司(担保人)的股东为叶某某及蔡某某(被担保股东,持股90%)”;又如(2021)京02民终11964号案:“一审经查,某公司(担保人)法定代表人为刘某甲,其中刘某甲持股93%(被担保股东),杨某某持股4%,刘某乙持股3%。”
第三层:公司外部关系及债权人利益保护
担保法律关系及公司内部关系之外,尚有相对人与担保人外部其他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担保合同无效后,相对人对担保人的赔偿损失请求权最终寄托于公司责任财产,因此其实现或影响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但相较于股东权益,公司外部债权人利益更为远隔,因此救济路径更为限定,原则上不依赖(也无从依赖)于无效责任酌减。虽不排除实践当中存在以之作为考量因素的案例,但情形也相对特殊。毕竟债权本属平等,其间的竞争清偿关系应是常态,法院没有政策介入的正当性。
如(2021)沪01民终3161号案中,公司为大股东及该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未出具决议,法院在说理中强调该越权担保除了损害股东利益外,也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认定未尽到审查义务的“担保权人存在较大过错”,并据此“酌定”公司承担三分之一责任。回查该公司在企查查的涉诉信息,我们发现,在本案裁判作出时,公司已涉案二十余起,未履行总金额近六千万。
特别是,担保人未(或不能)证明越权担保实质影响对外清偿,乃至公司对外有其他欠付债务的情况下,其他债权人因素的影响就更微乎其微,不宜过分强调。
实践中亦有反面案例,如 (2021)渝0237民初2964号案中,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提供关联担保,未出具决议,法院在说理中提及关联担保的决议要求是为了避免损害“众多不特定债权人的利益”,并将公司的责任比例降低至40%。根据公开信息,截止判决落款时间公司尚无其他债务的生效判决,故法院下调责任比例,似出于以下考虑:避免公司责任财产过分减少,以保持公司对不特定债权的清偿能力。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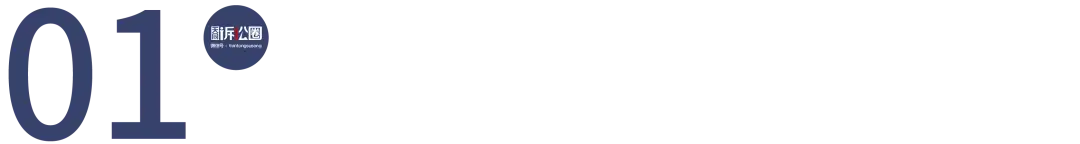
历史沿革
就上市公司担保无效后的责任分配问题,《九民纪要》及《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中并无清晰规定,《担保制度解释》出台后,其第9条第2款明确表态,即上市公司担保一旦被认定无效,其不承担任何缔约过失责任:
《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第2款:“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上市公司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且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由于该款为创制性规则,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理预期,最高院明确该规则不可溯及适用于《民法典》生效前的上市公司担保行为,就存量纠纷而言,即便担保无效,上市公司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11]在(2021)最高法民申1082号案中,最高院重申上述意见:
“民法典施行之前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被认定无效的,上市公司应当视情况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民事责任;民法典施行之后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被认定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的,上市公司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实操解读:存量纠纷是否溯及适用《担保制度解释》
上市公司越权担保,且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无效,就无效后果而言,有关观点认为,《九民纪要理解与适用》第22条解读中的表述为“上市公司不承担责任”[12],即意味着,上市公司不仅不承担担保责任,也无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如(2021)京民终724号案中上市公司所提出的抗辩:
“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2条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第十条之规定,结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多次使用“上市公司不承担责任”的表述,而非“担保合同无效”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之规定,更是进一步贯彻了杜绝违规担保的监管政策意旨,免除了上市公司的缔约过失责任,即进一步明确了上市公司既无需承担担保责任也无需承担担保无效后的赔偿责任这一裁判精神。”
但是,根据《担保制度解释理解与适用》的观点溯及,前述表述仅在担保责任的语境下使用,无涉《九民纪要》第20条项下无效责任的分配。[13]实践亦多持此观点,《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第2款对责任分配的规定属于新法,且有悖于当事人预期,不应溯及适用,典型如(2021)京03民终4329号案:
“本案中,A公司(债权人)与B公司(债务人)的借款法律关系以及C公司(担保人、上市公司)的担保法律关系均发生于民法典实施前,A公司尽管对于担保合同的无效负有责任,但合同无效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A公司仍有权主张无效情形下C公司的民事责任。因此,本案中但如适用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规定,则会背离A公司的合理预期,故本院认为,本案不适用上述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的规定。”
上市公司担保无效时,通常上市公司与相对人均存在过错,个案差异多在于上市公司能否主张《九民纪要》第20条第2句的免责事由。在主流处置思路中,基于事实模型和裁判依据的不同,可将存量纠纷划分为两类场景。
场景一中,上市公司与相对人均对担保无效有过错,法院依据《九民纪要》第20条第1句,认定上市公司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不超过二分之一责任。典型如(2021)京03民终4329号案中,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且在未经决议程序的情况下出具了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股东会决议。法院认定,相对人未审查有关决议的披露,上市公司违反决议和披露要求,双方均有过错,上市公司应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责任: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尽管A(债权人)并未根据B(担保人、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信息与其订立担保合同,涉案合同因此应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但这不影响本院对于B公司过错问题的审查。就过错而言,B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其在未经决议的情形下,向债权人出具《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书》并加盖公章,其合计持股50%以上的股东向债权人出具了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且其股东之一C公司目前已经持股超过80%,据此,本院认为,B公司及其股东对于对外担保应经过的决议程序更应知悉并遵守,该公司在未经决议并披露的情形下擅自对外提供担保具有过错。关于责任比例,一审法院认定欧浦公司应对D公司(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50%的责任,该责任比例的认定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又如(2021)最高法民申6970号案,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公司公章,但未出具决议,法院认定,相对人未尽到决议审查义务,上市公司内部公章管理不当,双方均存在过错,因上市公司未证明存在免责事由,其应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二分之一责任:
“本案中,一方面,A公司(债权人)未对郭某某以B公司(担保人、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保证合同》的行为审查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原判决认定A公司未尽到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并无不当;另一方面,B公司在《保证合同》上加盖公司印章,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却对外提供担保,原判决认定B公司在内部管理上存在重大过失,并无不当。因此,原判决据此认定B公司应对C公司(债务人)不能清偿A公司案涉债务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责任,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并无不当。B并未充分举证证明A公司明知法定代表人郭某某超越权限,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B公司对其无过错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B公司关于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申请再审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场景二中,债权人明知提供担保的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或机关决议系伪造或变造,法院依据《九民纪要》第20条第2句,免除上市公司的缔约过失责任。对于债权人明知证据存在明显瑕疵的案例,法院不仅会在裁判理由中强调其主观状态,并会据此确定责任划分。如(2021)粤01民终7597号案,上市公司为关联公司提供担保,未出具股东大会决议,债权人在案涉担保合同上注明“抽屉协议”,法院认定债权人明知越权担保,上市公司对担保无效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重要的是,A公司(债权人)在内部贷款审批文件上注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抽屉协议”,应封包保存,待B公司(债务人)还款后即退回。……按照通常理解,“抽屉协议”是指当事人之间私下签订,不便公开的协议。如果A公司在主观上对于《最高额保证合同》为C公司(担保人、上市公司)合法有效出具不持任何疑义,则完全没有必要将该协议作为“抽屉协议”来处理。相反,A公司在内部审批文件上的该表述足以证实A公司对于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属越权出具不仅是非善意,而且是明知的,C公司依法不应对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无效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此外,在部分案件中,债权人明知的事实特征并不明显,法院通常会叠加上市公司场合下对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特殊需求,进而仍倾向于按照债权人明知作出认定。如(2021)京03民初94号案,上市公司为股东提供关联担保,仅出具董事会决议,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亦未予以公告,法院认定,债权人明知案涉担保不满足《公司法》以及章程对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要求,即明知案涉担保系越权,担保无效,上市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A公司(担保人、上市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B公司(债务人)为A公司的股东,故A公司出具涉案《担保函》系为其股东B公司提供担保。本院认为,A司并非一般公司,而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提供担保与一般公司不同,往往涉及众多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法律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有信息披露的义务,其中担保事项也是必须披露的内容。因此,在上市公司提供担保时,对于债权人而言,应课以更高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债权人应进行实质审查。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根据A公司章程,A公司对股东提供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法》为公开施行的法律,A公司章程为公开披露的文件,C公司(债权人)接受A公司出具的《担保函》时对此应属明知,且A公司应就担保事项进行公告。而本案中,A就涉案担保事项,并未经股东大会决议,亦未予以公告,故此系属上市公司违规担保。C公司在明知上述规定以及A公司并未就担保事项进行公告的情况下,仅依据涉案董事会决议即接受A公司所提供的担保,并未尽到实质审查义务。由此可见,C公司对此并非善意,且C公司明知A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故该《担保函》无效,A公司无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C公司关于要求A公司就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但是,在极端个案中,也有法院持溯及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第2款的观点。如(2021)京03民终7029号案,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未经股东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一审法院认定担保协议无效,按照二分之一比例判定上市公司承担责任,二审溯及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第2款,改判上市公司完全免责:
“该司法解释(《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第2款)属于针对上市公司越权担保的特别规定。涉案越权担保行为虽发生于该司法解释颁布之前,因其时法律、司法解释并未就上市公司越权担保责任问题做出专门性规定,故本案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同时,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已经就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程序作出明确规定,该司法解释的适用,并不具有明显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合理预期的情形。某公司(担保人、上市公司)上诉主张《保证合同》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有合法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43页。[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71页。[3] 值得注意的是,《担保制度解释》发布前对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授权例外的把握相对混乱。有持宽松观点者,并未限于保函,如(2020)桂民申312号案;又有持与《担保制度解释》标准近似,但口径稍宽,且试图引入其他因素限缩概括授权者,如(2020)鲁民再2号案。该案中,银行分支机构对外提供保证,但保证交易文本不符合总行样式,且债务人未根据规定提供担保费用或者反担保。山东高院认定,即便保证属于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也不应认定案涉交易落入概括授权之中。虽然该案最终并未认定担保已获授权,但之所以称该案“与《担保制度解释》标准近似,但口径稍宽”,是因为:其观点以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为概括授权参考,即标准近似;但例外范围又不限于保函,谓之口径稍宽;并且最终其试图另外引入协议范本及合规要求作为概括授权再限缩的依据。[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71页。[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44页。[6] 相似案例另见(2021)晋0882民初1375号案。[7] 如在(2020)鲁民终1610号案中,山东高院认为“对于‘相互担保等商业合作关系’应理解为‘同一’提供担保的公司与‘同一’主债务人之间存在着长期、多次的‘相互’担保行为……‘相互担保’的事实应形成于提供涉案担保之时,不能以事后互保的事实反推此前的担保行为……在提供担保时,债权人对于此前主债务人与担保人之间存在相互担保的事实应为知情”。在(2020)沪民终285号案中,上海高院认为“如当事人之间长期存在有效的相互担保,担保金额基本相近,则此后某次欠缺决议的担保,有可能被法院仍认定为有效。但如果此前的相互担保就是无效的,就不能因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不断累积,导致此后的担保成为有效”。[8] 但是,上述规定遗留有两点问题:其一,未能明确担保人无过错时是否仍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其二,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且债权人无过错的场合下,由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会造成政策与体系的混乱。即便担保人有过错,让担保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方面未必与担保人的过错程度相符;另一方面,若担保人与债权人签订的是一般保证合同,保证合同有效时,担保人尚仅需对债务人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担保责任,保证合同无效时,反倒要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轻重失衡,与体系解释的要求相悖。但鉴于该等问题乃一般意义上的担保问题,本文不作专门论述。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刘贵祥:《担保制度一般规则的新发展及其适用——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为中心》,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5期,第61页。[9] 除此之外,《担保制度解释》第17条进一步对担保人承担责任的过错前提、责任性质予以厘清,明确规定了担保人无过错时无需承担责任;在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而非连带责任,以使得担保无效时的责任范围与担保有效时的责任范围保持一致,并使担保人最终承担的责任份额也获得适当降低。[10] 参见李国光、奚晓明、金剑锋、曹士兵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93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211页。[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52、160页。[1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98页。[1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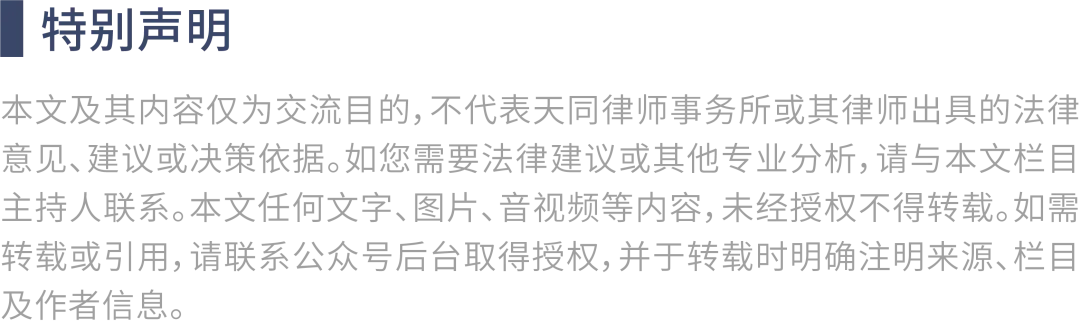
转发本文并扫描二维码提交信息,即有机会获取纸质版《公司担保争议解决双年观察》和《上市公司担保合规审查指引手册》(2022年修订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