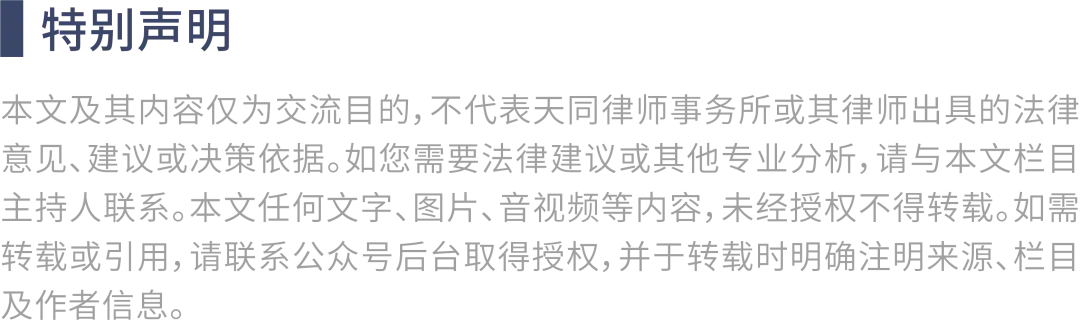文/杨骏啸 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丹丹 天同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姚一纯、余周洋、高西雅 天同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
我们在研究报告的第一篇,基于对商业实践的考察,根据表决权的二次配置方式,将协议型一致行动主要区分为两大类型——表决权归集和表决权拘束(详见报告第一篇:协议型一致行动研究报告(一):先导篇)。其中,表决权归集的主要特征为,目标公司的股东通过协议,将部分股东对目标公司的表决权交由其他股东行使。此类表决权归集往往被冠以“表决权委托”“表决权代理”“表决权让渡/转让”之名。就此,我们又将表决权归集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模式——表决权代理和表决权转让。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表决权代理模式下,表决权的归属不发生变动,仅是由部分股东以其他股东的名义行使后者的表决权;而在表决权转让模式下,表决权的归属发生了变动,进而使受让表决权的股东得以以权利人的名义直接行使表决权。
报告第二篇,我们将聚焦表决权代理模式,探讨该模式在实践中的主要风险点及其法律问题。先来看一个案例:
有限责任公司A的股东甲与股东乙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股东甲将其持有的A公司股权对应的表决权不可撤销地委托乙行使,甲无须另行向乙作出授权,乙可以根据其自主意愿行使表决权。两年后甲乙双方产生矛盾,甲口头通知乙解除上述协议,并在A公司召开重大决策事项的股东会议时到会投票,内容与乙的投票相反,双方因此次股东会决议内容和效力产生纠纷。
此案中,要确定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和效力,需要首先回答如下问题:
(1)《公司法》仅规定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表决权代理,而没有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决权代理,《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否会因标的内容不合法而无效?
(2)《表决权委托协议》仅约定了委托关系,甲并未向乙授予表决代理权,乙在股东会议上代理甲行使表决权是否无效?
(3)甲乙之间存在多重商业往来关系,《表决权委托协议》背后的商业逻辑是甲对乙的利益补偿,可否认定其实质为表决权转让,并因表决权性质认定《表决权委托协议》无效?
(4)《表决权委托协议》明确约定“不可撤销”的情况下,甲通知乙解除协议能否以及产生何等法律效果?
(5)甲乙同时出席股东会议并作出内容相反的表决,应当以谁的表决内容为准?
报告第二篇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讨论表决权行使的可代理性、表决权委托与表决权代理的关系、表决权委托与表决权代理的效力等;下篇将进一步讨论表决权委托的解除与表决权代理的撤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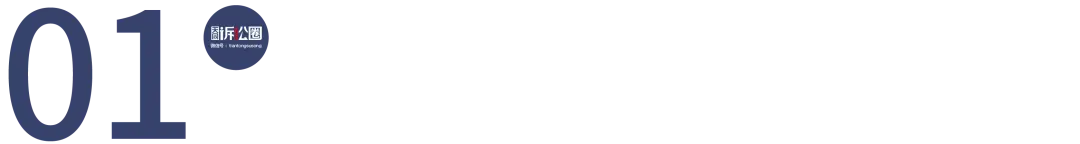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表决权行使的可代理性
表决权代理模式得以实现的核心基础在于,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通过代理的方式行使。针对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106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但《公司法》并未针对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同样的规定,由此产生的疑问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能否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该问题的结论直接决定了表决权代理模式是否能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场合。
(一)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观察
理论学说上,有观点认为《公司法》排除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表决权代理构成法律漏洞。[1]有观点则进一步指出,虽然缺乏《公司法》的明文规定,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也可以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2]
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表决权可以通过代理的方式行使。例如,(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案中,最高法院查明副食品公司(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的5名股东与股东名册上记载的其余所有股东签订了“股东代表委托书”,约定由该5名股东“行使投资收益权外的股东一切权利”。[3]就诉争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权计票方式,最高法院认为,基于“股东代表委托书”,该5名股东可以代表其他股东行使表决权。再如,(2017)京01民终4548号案中,法院查明李某与陈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李某将其持有的广告公司等公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于陈某,并约定李某将其享有的其余部分股权所涉股东表决权等权利“全部授权”给陈某,李某仅享有“股权财产权及收益权”。[4]就该“表决权授予”约定的性质,二审法院认为,“股东的权利虽不能与股东资格分割所有,亦不能作为财产性权利进行分割,但可授权他人代为行使”。可见,二审法院亦认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表决权可以由股东以外的他人通过代理的方式行使。
也有个别案例持相反观点。例如,(2020)浙0303民初2412号案中,法院查明阀门管件公司(该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孙某等三人与林某签订《合作协议书》,其中约定,待林某成为阀门管件公司股东后,孙某等三人“将股东表决权委托乙方(注:林某)指定的第三人行使”。[5]本案中,法院否定了该约定的效力,其理由为,根据《公司法》第42条[6]的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只有在章程另有规定时可以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阀门管件公司的章程“并未包含被告(注:孙某等三人)委托原告(注:林某)指定的第三人行使表决权的相关条款”,因此,《合作协议书》中关于表决权委托的相关约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依其逻辑,该法院的观点似乎认为,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否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表决权原则上须由本人行使,而不得通过代理的方式由代理人行使。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的可代理性之证成
我们认为,虽然《公司法》未明文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表决权可以通过代理的方式行使,但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本质上是股东对股东会所议事项(拟形成之决议)作出的意思表示,可以直接适用民法中的代理制度。因此,《公司法》未予另行规定,并不构成法律漏洞[7],更不能以此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的可代理性。
具体而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的可代理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层次予以说明。
1.股东会决议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行为
在《民法总则》施行前,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决议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曾具有不小的争议。[8]《民法总则》于2017年施行,其中第134条第2款[9]明确将决议行为纳入了民事法律行为一般规定,意味着实证法层面肯认了决议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法律行为,为决议行为的法律适用提供了基础规则供给。[10]《民法典》第134条保留了该规定。
2.股东会会议决策在性质上属于决议
根据《公司法》第37条[11]的规定,股东会原则上应通过股东会会议的方式行使职权。此外,根据《公司法》第42条的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行使表决权”。据此,股东行使表决权的场合为股东会会议,行使表决权而形成的结果为股东会会议决策。
或有疑问的是,除《公司法》第37条第1款第7至第9项目所明文规定的“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以及“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之外,就其余股东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例如第1项规定的“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所形成的决策,在性质上是否属于决议(是否能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对此,为了消除《民法典》《民法总则》与《公司法》因立法侧重点不同而带来的体系隔阂和概念使用差异,理论学说往往在解释论上扩大“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含义,认为只要产生一定的私法上的效果,就属于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从而将股东会会议在股东会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决策纳入决议(法律行为)的范畴。[12]司法实践通常也采取类似的态度,认为股东会会议作出的决策性质上均属于决议,可以适用决议不成立、决议撤销和决议无效等具体规范。[13]
3.股东表决权可通过代理的方式行使
决议作为法律行为,其成立也有赖于意思表示的作出。因此,股东行使表决权本质上就是股东针对相关议案所作出的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意思表示。[14]虽然《民法典》第161条第1款[15]规定通过代理可实施的是法律行为,但鉴于法律行为本身须借助意思表示而成立,因此代理所指向的内容实际是意思表示的作出与受领。[16]
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表决权代理原则上不属于《民法典》第161条第2款[17]规定的禁止代理事项。首先,《公司法》或其他法律并未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表决权必须由本人行使。前述(2020)浙0303民初2412号案的裁判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公司法》第42条针对的是股东行使自己的表决权,该条所述“章程另有规定”指的是章程约定部分股东享有与出资比例不同的表决权份额,针对的是表决权权利的分配及归属,并不涉及表决权的行使。因而《公司法》第42条不能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表决权代理限制的依据。[18]其次,“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主要是指遗嘱、收养、成年人意定监护等身份行为。[19]股东表决权的行使显然不属于此类情形。例如,(2013)兴民二初字第1272号案中,大酒店公司股东虞某主张“股东身份关系不能委托”,对此,法院认为表决权的行使不属于禁止代理的情形,并且《公司法》“亦未禁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因此,在公司章程没有相反约定的情况下,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行使表决权。[20]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决议系法律行为,股东行使表决权的实质为作出表决的意思表示。从这一角度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表决权的可代理性,并不存在实质差异,因而也不应被区别对待。根据代理制度的一般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表决意思均可通过代理的方式作出。因此,《公司法》第106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的代理规定更像是宣示性条款,不能仅以《公司法》未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表决权代理,作为否定或限制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表决权可代理性的规范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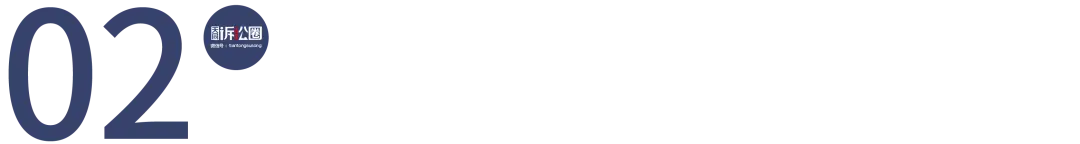
表决权委托与表决权代理的关系
如前所述,表决权代理模式实现表决权归集的方式为部分协议股东通过代理的方式行使其他协议股东的表决权。简言之,表决权代理模式的基石为代理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民法典》将代理权授予行为区分于基础法律关系,于总则编进行了单独规定,该区分原则亦为理论通说[21],也逐渐为近年来的司法实践所肯定[22]。但由于《民法典》在相关规范术语的使用上缺乏明确区分度[23],当事人在商业实践中经常混用“代理”和“委托”,从而引发歧义,甚至可能由于误解而选择了与商业目标不匹配的用语,从而引发争议。
当事人通过一致行动协议创设的是委托法律关系还是代理法律关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会决定具体的法律适用,更为重要的是影响表决权归集目的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商业实践中出现的不同约定的法律关系解释进行观察与分析。
(一)若协议被解释为仅设立委托法律关系,则无法实现表决权归集目的
股东之间仅创设委托法律关系,不足以实现表决权归集的商业目的。委托合同系《民法典》规定的有名合同,其核心特征(同时也是受托人的主给付义务)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24]委托合同仅能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设立债的关系,从而产生各自的权利或义务,例如受托人负有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的义务,享有请求委托人支付报酬的权利(有偿委托情形)或请求委托人偿还垫付的必要费用的权利(有偿或无偿委托情形)。有必要说明的是,即便受托人须以与他人实施法律行为的方式处理委托人的事务,在委托人未向受托人授予代理权的情况下,受托人亦不享有代理权,而只能以自己的名义与他人实施法律行为。[25]因此,若股东订立的一致行动协议仅设立委托法律关系,则受托人并不因此享有表决代理权,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行使表决权,原则上不应将该表决权的效果归属于委托人。[26]股东订立的一致行动协议设立其他基础法律关系的亦同。
需要说明的是,股东之间是否仅创设了基础法律关系,本质上属于意思表示解释问题,须结合一致行动协议的文义、目的及交易背景等多种因素予以判断。其中,文义解释是意思表示解释的起点[27],在解释作业中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股东在协议中约定作为受托人的股东在参加股东会之前应当另行取得委托人的授权,且委托人得以自行决定是否作出授权的,则有较大可能被认定该协议仅创设委托法律关系。
此外,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表决权的行使本质上是意思表示的作出,若协议股东仅就表决权的行使设立委托法律关系(即将投票作为委托事项)但不授予相应代理权,或被认为协议的约定缺乏可操作性。若结论如此,在解释相关一致行动协议时,裁判者可能会倾向于将其解释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含义[28]——即该协议应至少包含了代理权授予行为,而非仅设立委托法律关系。但实际上,表决权的行使可以在不授予代理权的情况下,独立成为委托法律关系中的委托事项。例如,股东甲(受托人)作为股东乙(委托人)的“使者”,将股东乙已经形成的投票意思传达于股东会会议的召集人/主持人,此时,股东甲本身并不需要以股东乙的名义作出意思表示,自然也无须获得代理权。[29]
因此,就表决权的行使,仅设立委托法律关系的做法虽然较为罕见,但也不一定总是缺乏现实意义。对于交易参与者而言,若希望通过表决权代理模式实现表决权归集,应在交易文件中尽量明确授予代理权的意思,以避免事后被认定欠缺代理权,影响“代理”效果,造成相关决议的效力瑕疵。
(二)若协议被解释为含有表决代理权的授予,则可以实现表决权归集目的
代理权授予行为与基础法律关系在法律构造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两者在承载主体上亦须泾渭分明。就采用表决权代理模式的协议型一致行动而言,我们观察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会选择通过一份交易文件(通常称为“表决权委托协议”),既创设基础法律关系,又授予代理权[30]。
如本文篇首给定的案例情形,《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甲无须另行向乙作出授权,乙可以根据其自主意愿行使表决权”,就有机会被解释为甲在与乙设立委托关系的同时,将表决代理权授予了乙。又如,某公司公告显示,股东甲和股东乙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甲将标的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乙行使,并约定了委托终止、争议解决等其他条款。此外,《表决权委托协议》亦明确表达了“乙方应按照其独立判断”“依据其自身意愿”,就公司股东大会所议事项“行使标的股份的表决权”,且“无需另行取得甲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再如,某公司的股东甲和股东乙、股东丙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书》,约定乙、丙将公司一定比例的表决权委托给甲行使,并约定甲“作为唯一的、排他的代理人”,在公司股东会上行使相应的表决权。[31]这两例中,从文义解释来看,协议股东均是通过一份交易文件,既创设了基础法律关系,又完成了表决代理权的授予。
还需要说明的是,代理权授予行为与基础法律关系的分离,意味着代理人的代理权可经由被代理人的授权行为而单独存在,即所谓“孤立代理权”。理论上,孤立代理权可以实现表决权归集的目的,并不一定需要委托合同或其他的基础法律关系。但由于代理权授予系单方法律行为,不能为相对人设立义务,因此在孤立代理权场合,代理人享有代理权的同时并不负担义务,往往就会使授权人(被代理人)处于不利地位。[32]因此,在交易中,孤立代理权并不常见。
(三)以将来授予代理权为委托人义务的特殊情形
个别情况下,当事人有可能先创设基础法律关系作为交易基础,并约定在特定情形下委托人有义务向受托人另行对具体事项授予个别代理权。有必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在此类交易安排中,基础法律关系能否保障部分协议股东在将来获得代理权。例如,某公司股东甲和股东乙约定,鉴于公司定期于每年6月15日及12月15日召开股东会,甲最晚应当于股东会召开前的60日向乙授予表决代理权。若甲未在约定期限内作出授权的,乙是否可以诉请甲实际履行?
对此,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合同可以将实施法律行为或作出意思表示约定为主给付义务,预约合同便是典型例证。[33]因此该问题的实质为,代理权的授予作为需受领的单方意思表示,是否属于《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34]第2项规定的“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情形,从而排除原给付义务,也就不得请求实际履行。由于该问题与表决权拘束模式下的实际履行问题相似,我们将在报告第五篇中一并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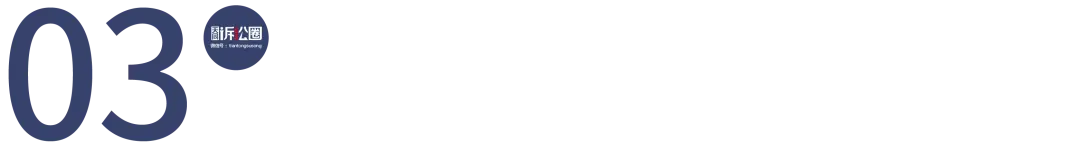
表决权委托与表决权代理的效力
从我们检索的案例来看,除前述(2020)浙0303民初2412号案外,司法实践中鲜有案例否定表决权委托或表决权代理的效力。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案件的争议焦点通常都不直接涉及表决权委托或表决权代理的效力,而是法院在评价当事人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否可被任意解除(或表决权代理是否可任意撤回)或其他争议时,对案件所涉表决权委托或表决权代理的效力作出了中间性判断,理由通常较为笼统。例如,(2020)豫03民终5122号案中,河南投资公司与王某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二审法院在认定王某能否行使解除权之前,认定“《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35]
虽然目前我们未见到否定表决权委托及表决权代理效力的倾向性裁判意见,我们认为,仍有以下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第一,如果当事人订立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委托方将其表决权委托给受托方行使,而受托方需要向委托方支付一定的价款或给予一定的经济利益,该表决权委托协议的法律关系有可能经由意思表示解释,被认定为表决权的转让而非表决权委托或表决权代理,进而引发表决权转让法律关系所涉的效力评价问题。更为常见的是,如本文开篇给定的案例情形,当甲乙之间存在多重商业往来关系,《表决权委托协议》背后可能被挖掘的商业逻辑是甲对乙的利益补偿时,对于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是否会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将在报告第三篇中作进一步的分析。
第二,目标公司的多个股东通过协议方式,使得部分股东得以行使其他股东的表决权,是否有可能被认为构成“股东权利滥用”,从而影响表决权委托或表决权代理的效力?就该问题,已有学者在表决权拘束模式下予以讨论[36],我们也将在报告第四篇中予以分析。
报告第二篇下篇中,我们将继续讨论表决权委托的解除与表决权代理的撤回等问题,敬请关注。
注释:
[1] 施天涛:《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51-352页。
[2] 王军:《中国公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16页。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182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4548号民事判决书。
[5] 参见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3民初2412号民事判决书。
[6] 《公司法》第42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7] 法律漏洞,是指法律体系上违反计划的不圆满状态。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7页。
[8] 参见徐银波:《决议行为效力规则之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164页以下。
[9] 《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规定:“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
[10] 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37页以下。
[11] 《公司法》第37条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十)修改公司章程;(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12] 有学者将股东会法定职权所涉及事项的私法效果区分为“内部发生的私法效果”“发生或影响外部的私法效果”和“发生介于内外部的私法效果”。参见李建伟:《决议的法律行为属性论争与证成——民法典第134条第2款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2期,第79页以下。较为类似的观点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以下。但值得注意的是,杨代雄老师认为,“批准董事会或监事会报告的股东会决议通常不导致社团内部关系发生变动,所以不是法律行为,但此类决议表达了社员对董事会或监事会工作的共同认识或态度,是表示行为的一种,与观念通知、意思通知等准法律行为类似”。
[13]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民终18375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中,某公司股东会会议作出了选举王某为公司执行董事的决策,对此,法院适用了《公司法》第22条关于决议无效、撤销之规定予以审查,说明了法院认为股东会就《公司法》第37条第1款第2项“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带人的董事、监事”而作出的决策在性质上属于股东会决议。类似案例参见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10民终2764号判决书等。
[14] 孔洁琼:《决议行为法律性质辨——兼评〈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9年春季卷)》,第140页;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以下。
[15] 《民法典》第161条第1款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16]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3页;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92页。
[17] 《民法典》第161条第2款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18] 此外,表决权是否可以通过代理方式行使,与部分股东将表决权代理权授予其他股东(以及与此相关基础法律关系)是否可能具有效力瑕疵,系不同层面的问题,本案裁判观点对此也有所混淆。
[19]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26页;杨代雄主编:《袖珍民法典评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139页(杨代雄执笔)。
[20]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3)兴民二初字第1272号民事判决书。
[21]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2页;汪渊智:《代理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3页以下。
[22]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815页;杜丹、达燕:《代理权授予与其基础法律关系的甄别》,载《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第2期,第65页。参见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072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20)川1303民初383号民事判决书。
[23] 例如《民法典》在代理制度的规范中采用“委托代理”指代理论学说中的“意定代理”,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定代理法律关系与委托合同法律关系的混淆。
[24] 《民法典》第919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25]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页。
[26] 当然,若符合相应构成要件,也有可能适用表见代理规则,从而使表决权行使的效果归属于委托人。
[27]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872页。
[28] 有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合同或合同条款可能具有两种合理的推定解释,“其中之一会使它充满意思,而另一种解释则使它无实际意义”,那么裁判者有可能会采纳前者,这通常被称为“推定每一条款具有意思与目的”的解释方法。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释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页。
[29] “代理人在为法律行为,传达人在服事实上之劳务”,转引自汪渊智:《论代理行为中的意思表示》,载《晋阳学刊》2014年第1期,第125页。关于代理与传达的区别,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01页以下;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93页以下。
[30] 此类协议中授予的代理权,多为类别代理权。所谓类别代理权,是指就某一类行为(例如行使表决权)授予的代理权,区别于就某个特定行为授予的个别代理权,及针对所有行为而授予的概括代理权。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10页以下。
[31] 参见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6民终375号民事判决书。
[32] 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42页。
[33] 《民法典》第495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预约合同。”有观点认为,预约合同的标的(给付内容)为“作出特定的意思表示”。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93页。
[34] 《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
[35] 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3民终5122号民事判决书。较为类似的情况参见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6民终375号民事判决书。
[36] 李潇洋:《组织框架下表决权拘束协议的体系规制》,载《法学论坛》2020年第3期,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