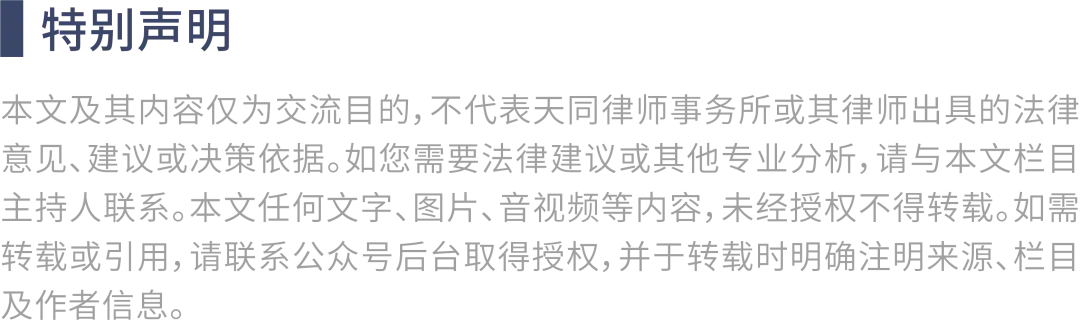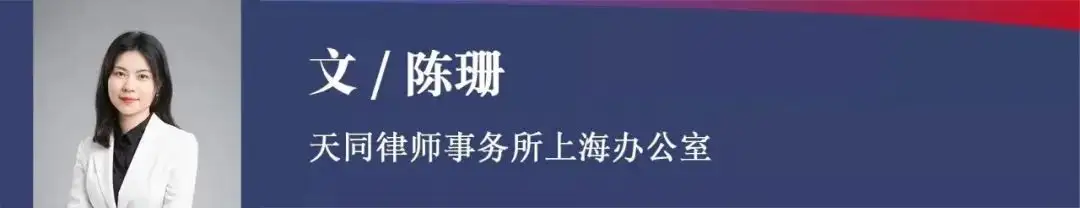
导语
商业诋毁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其客观表现形式主要为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等不正当手段,诋毁、贬损竞争对手商誉。实践中,对于“虚假、误导性信息”“编造传播”“诋毁后果”的认定,通常是案件争议焦点所在。基于此,本文拟对商业诋毁的客观要件认定要点进行梳理,望为实践提供有益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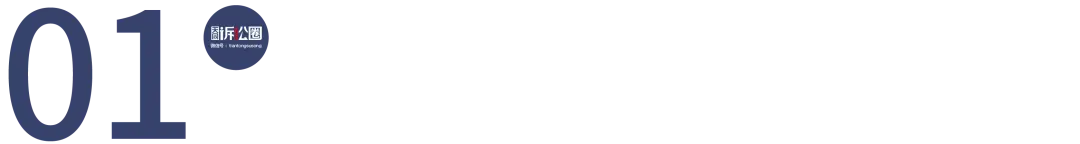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虚假、误导性信息的认定
(一)虚假信息
虚假信息是指内容不真实、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信息,即这些信息是无中生有、凭空编造而来的。[1]
虚假信息的认定难点主要集中在举证责任的分配方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原告针对其他经营者传播的虚假信息提起商业诋毁诉讼时,理应就传播信息的不真实性承担举证责任。但在实践中,考虑到被告捏造并传播的信息通常是原告不法、不誉等积极事实。此时,令原告承担“证伪”的责任可能较为困难。因此,部分法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信息传播者,由其提供传播言论具有真实性的依据,否则承担不利后果。如在“百奥泰国际会议(大连)有限公司与大连四叶草会展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被诉侵权方作为讼争信息的来源方及散布者,更容易掌握信息来源的证据。相关言论涉及的内容是否真实,应当由发布相关言论的被诉侵权方承担举证责任”,并据此要求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
而在被告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传播信息具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部分法院会综合考量原告的举证能力,令原告提供相反证据,进而对涉案言论的真实性做进一步审查。[3]
(二)误导性信息
误导性信息是指内容虽然真实,但仅陈述部分事实、容易引发错误联想的信息。[4]不同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但由于误导性信息同样能够产生贬损、降低其他经营者商誉的效果、损害经营者权益和竞争秩序,故仍有规制必要性。[5]而在对误导性信息做出认定的过程中,往往涉及对客观事实的价值评判,故实践中对于误导性信息进行认定的难度也较大。
1.误导性信息的表现形式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误导性信息应当包括“真实但片面的信息、真实但无关的信息、以及真伪不明的信息”三种类型。[6]其共同特征在于采用的表达方式或内容能够造成受众对于信息的理解,与全部事实真相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具体而言:
(1)真实但片面的信息
全面、准确地获取市场信息,是经营者或消费者做出合理商业决策的前提。在商业活动中,即使某一信息是真实的,但由于行为人对其进行了片面、不公正、不准确的陈述,仍会对竞争对手的商誉造成损害、构成商业诋毁。
如在“杜康”商标案中,洛阳杜康公司在其产品外包装上印制了“杜康商标唯一持有企业”语句。而事实上由于特定历史背景原因,涉案争议产生时市场中“杜康”注册商标和含有“杜康”二字的注册商标均合法存在。法院认为,尽管从字面上来看,洛阳杜康公司关于“杜康商标唯一持有企业”陈述为真,但该表述易使相关消费者产生白水杜康公司及其商品与杜康没有关系的错误认识,进而产生对白水杜康公司相关商品的质疑或否定性评价、影响消费者选择。最终,法院认定洛阳杜康公司的行为构成商业诋毁。[7]
(2)真实但无关的信息
经营者在商业活动中可能利用消费者的选择偏好,发布对手某些与商业活动无关的信息,从而达到破坏对手的商业形象、提升自己竞争优势的目的。[8]此类信息可能包括经营者财务状况、违法记录、员工生活作风、政治、宗教等。尽管该等信息可能确有其事,但由于其内容本质上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质量无关,并可能引发信息受众对于竞争对手经营能力、商品质量等方面的负面联想,进而不恰当影响受众选择,故具有不正当性。如在“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等与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广药集团发布广告、突出加多宝董事长行贿潜逃的事实,并将前述信息与“王老吉之争”联系起来。法院认定,广药集团该等表述方式势必会造成公众对于加多宝公司认知和评价的负面影响。最终认定广药集团构成商业诋毁。[9]
(3)真伪不明的信息
受制于科技发展水平或查明真相所需周期,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可能难以在短时间获得有效辨别。更何况,现实中很多信息的真假本身就难有定论。在此情况下,若经营者将尚未定论的信息当成已经定论的事实公开宣传散布,则可能构成商业诋毁。如“广东碧鸥投资有限公司、钟利民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经营者对于未定论的事实,没有客观公允地表述其‘未定论’的状态,而是故意将未定论的状态作为已经定论的事实来进行宣传散布,误导公众产生误解,造成竞争对手商誉贬损,这种情形亦属于前述条款的捏造、散布虚假事实”。[10]
2.误导的理解与认定
(1)传播信息对受众认知的影响
商业诋毁认定的根本要件,在于传播信息是否以误导的方式影响受众的认知和决策。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之一是确保市场竞争由商品或服务本身力量(如质量、价格、服务等)所推动。[11]而经营者通过发布误导性信息,干扰受众原本应当依据经营者商品或服务信誉做出的决策、削弱对竞争对手商品或服务的购买意愿,进而使得市场调节机制失灵。如在“成都好房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小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二审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指出,正当的竞争应围绕降低成本、改进技术、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等方向展开。而经营者通过发布误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不当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抢夺本属于竞争对手的商业交易机会。相关行为构成对市场竞争秩序的扰乱和扭曲。[12]
进一步而言,若行为人传播的信息不会导致受众认知的变化,则难以成立商业诋毁。从前文所述商业诋毁规制目的出发,认定误导性信息的重点并非在于相关言论真实与否的客观状态,而在于该等信息对于受众主观认知的影响。基于此,若信息的内容和表述方式不会造成受众的认知发生扭曲,则不构成商业诋毁。如经营者在传播信息中明确区分事实和评论部分,或明确相关言论系一家之言、能够让受众明白立场的,[13]抑或是传播信息与事物发展趋势吻合,则不容易造成受众认知扭曲。如,在“为你读诗(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尚客圈(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尚客圈公司拟针对为你读诗公司搬运、模仿其公众号的行为提起诉讼。尚客圈公司对外发布公开声明,称“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事实上,尚客圈公司在前述声明发布两个月后,才正式向法院起诉。为你读诗公司认为尚客圈公司声明起诉在先,实际起诉在后,构成商业诋毁,遂诉至法院。该案中,法院审查尚客圈公司为提起诉讼准备的公证书、代理材料等,认定尚客圈公司准备诉讼属实。并认为尽管《声明》关于提起诉讼的时间并不完全客观,但考虑到被告确已准备诉讼,法院最终认定《声明》内容并未达到捏造、散布虚假事实,以致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后果,不构成商业诋毁。[14]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经营者直接贬损性措辞或侮辱性言论的情况,尽管该等言论也能起到贬损竞争对手商誉的效果,但并非通过影响受众对事实的逻辑认识基础实现的,故不属于商业诋毁的调整范畴[15]。尤其,当受众能够认识到贬损性或侮辱性表述源于传播者主观意志时,该等信息更难以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如在“东莞市森威电子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迈测公司在宣传报道《来自灵魂深处的叩问:抄袭能改变测量方式吗!》中对森威公司采用了“妖孽!偷我迈测S7产品的模样,廉耻何在”的表述,并配有“孙悟空棒打妖孽”、“亲子鉴定”图文。森威公司认为前述表述无根据并具有讥讽性,构成商业诋毁。法院认为,迈测公司在“抄袭”报道中的“妖孽”言论具有较强的贬义色彩,但由于森威公司的确存在未经许可实施迈测公司外观设计专利的行为。故前述言论并不属于“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也未产生误导,不构成商业诋毁。[16]
(2)信息受众认知水平的确定
在判断传播信息是否对受众认知造成误导时,还可能涉及采用何种标准认定受众认知水平的问题。实践观点普遍认为,应采用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标准,认定涉案信息是否造成误导。[17]但如何界定“一般消费者”,仍存在模糊地带。
事实上,由于商品或服务的终端(ToB或ToC)、受众对象所处交易层级等差异,“一般消费者”实际并不局限于使用商品或服务的终端群体(即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者),还可能包含制造商、经销商、合作客户等经营主体。并且,囿于所处行业的差异,不同受众的辨别能力和认知水平也存在一定区别。因此,在认定“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标准时,仍需要结合受众所处行业的特征、知识背景、消费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一般认为,产品经销商的判断能力较弱、避险意识较强。当产品经销商收到诋毁信息时,更容易受到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影响。因此,经营者在向经销商发函时,应尽到更高程度的谨慎注意义务,充分、客观地披露侵权判断所需的必要信息。[18]
(3)判断信息是否具有误导性的时间基准
应以何时点下受众的认知状态作为判断传播信息是否具有误导性的依据,也是商业诋毁司法实践中较具争议的问题。客观世界是变动、发展的。特定时期内不真实或真伪未定的信息,在未来可能演变或确认为真。故在不同时点下评价同一信息是否具有误导性,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以经营者发送知识产权侵权警告函的场景为例,由于知识产权侵权(尤其是技术类案件)的判断具有复杂性,不同层级法院对侵权与否做出不同认定的情况并不罕见。如若坚持以终局性的侵权判定作为虚假或误导性事实的认定因素,那么依据一审法院侵权发出的警告函,则可能构成商业诋毁[19]。
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生效裁判作为判断传播信息是否对受众造成误导的依据。该观点的核心理由在于现行诉讼程序设置下,生效裁判对于争议事实认定结果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如在“东莞市森威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迈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虚假、误导性判断的客观依据不能将最新发生的事实排除在客观事实之外。而根据诉讼法对诉讼程序的设置,最新的生效诉讼结果也更接近于最公平正义的法律评价,在是否侵权这一事实的判断上更有权威性。[20]类似地,在“扬州市龙卷风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圣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未生效法律文书所涉的事实和法律认定属于司法未决问题。进而认定圣敏公司在一审文书尚未生效的情况下散布“假冒品牌!打假成功案件!”标题,将导致相关公众产生误解,构成商业诋毁。[21]
与之相对的,也有观点认为,应以行为人发送侵权警告函时的实际情况,作为判断是否构成误导的依据。其核心理由在于被诉言论所涉侵权事实是否成立,并非商业诋毁案件的审理范畴。而应以诋毁行为发生的时间为节点,重点审查传播言论与实际情况的偏离程度[22]。如“天津欧妆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德国万事乐德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法院提出不能因为司法机关尚未对此作出认定,就禁止市场经营者对可能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采取其他维权措施先行救济,亦不能要求只有侵权投诉得到司法的最终侵权判定方可认为是合适、合理的投诉。[23]类似地,也有法院提出,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不再苛求以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判断传播信息是否具有误导性的依据。如当经营者发出的侵权警告对于侵权事实的判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并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时,则不能再苛求只有生效判决认定的侵权事实才能作为判断依据。[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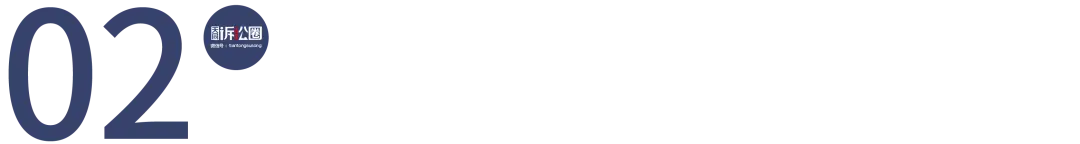
编造、传播的认定
(一)编造、传播的内涵
编造意为凭空捏造,既包括无中生有、凭空虚构的,也包括恶意歪曲、以偏概全或虚构部分内容的情形[25]。传播则意指信息的对外散布。实践中,典型的传播行为既包括召开新闻发布会、社交网络公开评论、短视频、直播、自媒体撰稿等,也包括发送律师函、警告函、告客户书、印制宣传册等途径。甚至部分法院认为,经营者向有关管理部门举报、投诉的行为也是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在相关行为符合商业诋毁其他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可以构成商业诋毁。[26]
就编造、传播的行为关系而言,单纯的编造行为不构成商业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指出,“虚伪信息只有经过传播后才有可能构成商业诋毁,只编造信息而未将编造的信息进行传播则不构成商业诋毁”。[27]如前文所述,商业诋毁的根本机理是通过传播虚假或误导信息、影响受众认知和决策。在此过程中,虚假、误导性信息只有作用于第三方受众时,才可能产生否定性评价,造成市场资源错配的后果。[28]基于此,发生在经营者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也不会对外降低竞争者的社会评价,不构成商业诋毁。如“东莞市利拿实业有限公司与东莞市阳宏机械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中,法院指出,“传播的结果是要让上述相关公众了解和知悉虚伪事实。仅发生在经营者与竞争对手两者之间一对一的传播行为,不会导致相关公众降低评价,不属于传播行为”。[29]
(二)编造、传播需满足特定指向性
编造、传播行为还要求具有特定的指向对象。即,受众能够根据接受的信息,分辨出行为人指称的具体对象,并能够对被诋毁者产生清晰的印象记忆。[30]特定指向性不要求行为人必须直接指出具体诋毁对象的名称,但需要指向对象具有可辨别性[31],包括“明确确定”和“可依据客观条件准确推定”。具体而言,经营者通过对市场关联主体的具体化、特征化描述,使受众根据一般理性能够知晓指向对象的,也属于具备特定性指向的情况[32]。如“广东康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德玛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上诉案”中,康宝公司认为德玛仕公司在京东官方旗舰店多款消毒碗柜产品介绍中,使用了“不锈钢升级款抗氧化耐腐蚀容易清洁卫生符合健康标准”与“压花铝板淘汰款铝高温容易挥发铝离子容易让人衰老造成智力缺陷”的表述,损害包括康宝公司在内的铝内胆消毒碗柜市场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德玛仕公司则认为其宣传中未提及、标注康宝公司的商标、品牌、字号等可识别康宝公司的商业标记。即,不具备特定指向性。对此,法院认为尽管德玛仕公司宣传描述中未直接提及康宝公司,但宣传中关于“压花铝板淘汰款”的描述,能够让相关消费者分辨出指称的产品是铝内胆消毒碗柜,指向了包括康宝公司在内的使用铝内胆的消毒碗柜生产企业,对该类企业及其相关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产生负面影响。最终,法院认定德玛仕公司的相关宣传构成商业诋毁。[33]
此外,特定指向性并不要求传播对象的数量特定。传播的对象既可以是不特定公众,也可以是特定客户群体。实践中,法院对于“传播”的认定标准的把握,存在一定分歧。部分法院认为,向有限数量的对象发布诋毁信息的行为,构成传播行为。如“无锡晶美精密滑轨有限公司与江苏星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等商业诋毁纠纷上诉案”中,江苏星徽公司抗辩其仅针对晶美公司的四家合作企业发送侵权函,不构成在竞争市场上“传播”的行为。对此,法院认为四家收函客户在相关市场具有重要地位,且函件涉及的地域范围亦较广。故江苏星徽公司向四家企业发函,足以对该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34]但也有法院认为,向有限数量受众发布信息的行为,并不构成传播行为。如“天津欧妆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德国万事乐德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涉案律师函的接收者仅为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京东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律师函的内容没有向涉案商品的相关公众以及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传播。[35]
笔者认为,向有限的受众发布信息的行为同样构成传播行为。其一,从文义解释角度,《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并未采用“公开传播”或“向公众传播”等措辞,表明传播行为并无公开性的要求。现行法律体系中可供描述“传播”行为的法律用词包括“传播”、“公开传播”、“向公众传播”等。[36]在法律体系中存在多个含义不同、可供选择的语词素材情况下,基于词义精准性及词句使用的效率性因素考量,应承认不同措辞的含义存在差异。因此,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传播”而非“向公众传播”措辞的情况下,难以将受众不特定性解释为传播行为的构成要件。其二,从目的解释角度,规制商业诋毁行为的目的是,防止经营者通过散布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的方式来损害竞争对手的商誉并以此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37]而商誉作为一种观念上的认识和看法[38],其受损与否并非取决于传播信息受众数量多寡。向特定核心群体(如经营者的合作伙伴、潜在客户等)传播虚假或误导信息,同样可以起到贬损商誉的效果。此等行为,也应当纳入商业诋毁的规制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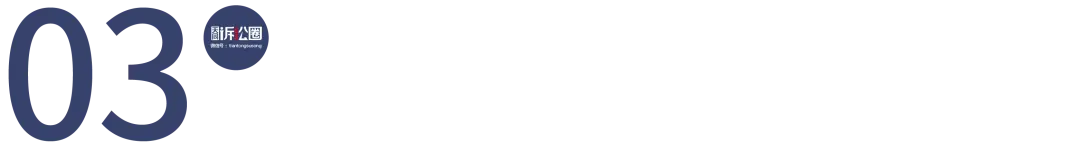
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认定
商业诋毁的结果是使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受到损害,即造成竞争对手在商业形象或商品形象方面的社会评价降低。[39]社会评价降低不仅包括可以是已经实际产生的商誉损害,也可以是可能造成的损害[40],包括交易机会丧失、议价能力降低等。[41]就商誉损害举证方面,通常需要关注诋毁信息中指向商誉、与消费者交易选择及意愿密切相关的信息。[42]具体来说,该等信息可以涵盖商品质量、商品价格、交易条件、企业形象、生产经营状况以及竞争对手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健康状况、信用状况、能力、品质等。[43]
而就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证明标准而言,需要较充分的证据证明虚假或误导性信息造成不良影响。如在“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青岛软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上诉案”中,腾讯公司举证用户负面评论,以证明软媒公司发布的文章损害腾讯公司的商业信誉。法院认为,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的认定,需要有较为充分的证据证明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确实对社会公众产生了不良影响导致其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下降或受到损害,而不能仅以少数人的评论来推定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商誉。法院认为,腾讯公司举证的相当数量评论内容未批评腾讯公司,数量上和微信用户数量相比也微不足道。故不能仅依据涉案文章的用户留言或负面评价就简单的认定软媒公司损害了腾讯公司的商业信誉。[44]
注释:
[1] 参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
[2] 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2民终5033号判决书。
[3]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579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第十一条规定。
[5] 参见陈中山、廖慈芳:“商业诋毁的判定”,载《人民司法》杂志社2022年第8期,“人民司法杂志”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14日发表,https://mp.weixin.qq.com/s/YhrZsRrh_rdxOvvfQY1ieA。
[6] 参见陈健淋:“论商业诋毁诉讼中的误导性信息”,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
[7] 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民终154号民事判决书。
[8] 参见陈健淋:“论商业诋毁诉讼中的误导性信息”,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
[9]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终106号判决书。
[10]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517号判决书。
[11] 参见陈中山、廖慈芳:“商业诋毁的判定”,载《人民司法》杂志社2022年第8期,“人民司法杂志”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14日发表,https://mp.weixin.qq.com/s/YhrZsRrh_rdxOvvfQY1ieA。
[12]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民终4332号民事判决书。
[13] 参见王晓明:“虚假宣传、商业诋毁与正当商业言论的界限”,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11期。
[14]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6)京73民终76号民事判决书。
[15] 参见王晓明:“虚假宣传、商业诋毁与正当商业言论的界限”,载《人民司法》2021年第11期。
[16] 参见(2019)粤民终2837号民事判决书。
[17] 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民终4332号民事判决书;陈中山、廖慈芳:“商业诋毁的判定”,载《人民司法》杂志社2022年第8期,“人民司法杂志”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14日发表,https://mp.weixin.qq.com/s/YhrZsRrh_rdxOvvfQY1ieA。
[18]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终274号民事判决书。
[19] 参见李双利、何震:“商业诋毁案件中‘虚伪事实’的认定”,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4期。
[20]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民终2837号民事判决书。
[21]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6)沪73民终132号民事判决书。
[22] 参见陈中山、廖慈芳:“商业诋毁的判定”,载《人民司法》杂志社2022年第8期,“人民司法杂志”微信公众号”2022年4月14日发表,https://mp.weixin.qq.com/s/YhrZsRrh_rdxOvvfQY1ieA。
[23]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445号民事判决书。
[24]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民终418号民事判决书。
[25]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解与适用》,中国工商出版社2018年版。
[26] 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知民终614号民事判决书。
[27] 参见王瑞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28] 参见陈健淋:“论商业诋毁诉讼中的误导性信息”,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
[29]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三申字第13号裁定书。
[3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190号民事判决书。
[3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508号民事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
[32] 参见龙俊:“商业诋毁构成要件研究——兼评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载《河北法学》2019年第4期。
[33] 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6民终12302号民事判决书。
[34]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苏民终919号民事判决书。
[35]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445号民事判决书。
[36] 参见张伟君:“我国著作权法中传播、广播与转播的含义之辨析”,“知识产权与竞争法”微信公众号2021年4月10日发表,https://mp.weixin.qq.com/s/snQvaZOAyztIgh8J9RBy3g。
[37] 参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20)沪73民终160号民事判决书。
[38] 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领域的表达自由:保护与规制”,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
[39] 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反不正当竞争法理解与适用》,中国工商出版社2018年版。
[40]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知民终字第0112号民事判决书。
[41]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民终382号民事判决书。
[42] 参见黄浩:“商业诋毁行为客观要件的认定”,“知产财经”微信公众号2022年12月23日发表,https://mp.weixin.qq.com/s/P8A9xU8cgO1A-USPxX2lqw。
[43] 参见《浙江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2022修订)》第十六条。
[44]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579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