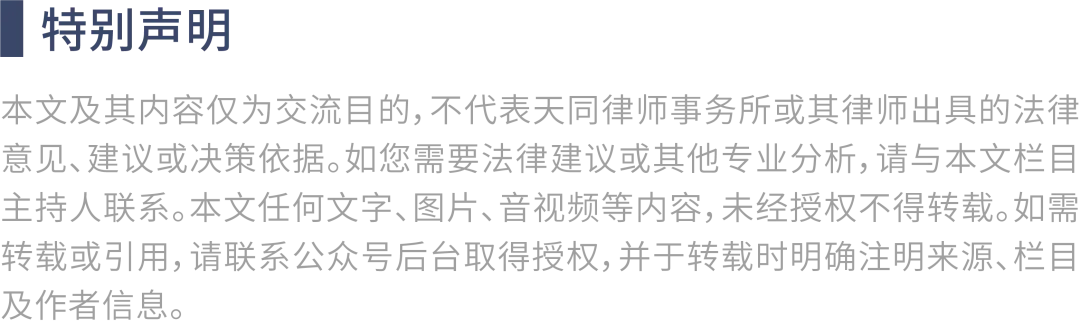注:本文系日本上智大学田头章一教授2022年11月5日在东亚破产与重组协会举办的第十三届东亚破产法论坛上的发言稿,微信推送时略有修订
栏目主持人池伟宏按:主债务人的破产对保证人影响几何?保证人如何免除或减轻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参与破产程序的权利如何协调?日本的经验值得参考。其中针对企业家个人对企业经营债务提供保证产生的责任应对上,一方面政府支持由非政府机构主导设立同步化解主债务和保证债务的一体型债务重组程序(但是移植这一制度难点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在鼓励、倡导各类机构提供不依赖于个人保证的融资,强化设立经营者提供保证时的提示说明义务,避免发生经营者发生个人破产。

译 /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 张亚晖目录
引言
一、民法中保证制度相关法条的修订与《经营者保证准则》的渗透
(一)民法中保证制度相关法条的修订——以2017年修订(2020年4月实施)为中心
(二)《经营者保证准则》的渗透
二、“受理时现存额主义”相关问题
(一)主债务人被裁定受理破产的情形
(二)主债务人等被裁定进入民事再生/公司更生程序
三、倒产程序中与保证相关的问题
(一)集团企业破产的特殊问题
(二)主债务人的重整计划中保证人的免责
(三)其他的问题点
四、结语
引言
保证人根据保证协议,在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承担相应的履行责任(参照民法第446条第1款,本文中的民法是指《日本民法典》)。在日本的民法中,尽管保证债务是民法典第3编第1章第3节规定的“多数当事人之债权及债务”的一种,但很明显,保证的实质机能是以保证人的自身信用为主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由于保证具有这种所谓“人的担保”的性质,民法典和与倒产相关法律都对此作出了规定,以确保债权人能够充分享有担保利益。特别是倒产程序中除了要保护债权人利益,还涉及作为求偿权人的保证人的地位、与其他破产债权人间的利益调整等复杂多样的问题。
民法中保证制度相关法条的修订与《经营者保证准则》的渗透
关于保证制度,最新的民法修正案在将个人保证视为独立类型的基础上,完善了对个人保证人的保护对策,使保证的一般规则更加合理。此外,随着民间组织制定的《经营者保证准则》等各种实务性应对措施的出现,不依赖个人保证的融资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实务中对经营者保证债务的处理逐渐形成了一套对策,这种对策通过与主债务人企业的早期重建同步进行的保证债务处理程序,使得企业重建更加容易。鉴于上述保证制度的法律修订及实务发展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破产程序中保证债权的处理,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首先,民法针对个人根保证(即个人最高额保证)中保证额上限的设定进行了一系列规则的修改。根保证(即最高额保证),即针对将来发生的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债务的保证。对于保证人来说,若把将来发生的债务也纳入主债务,可能会为其带来承担过高担保债务的风险。
因此,2004年的民法修正案中已经规定,设定保证额上限是以贷款等为主债务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生效要件(旧民法第465条第2款)。2017年民法修订后,该条不再仅限于“以贷款等为主债务”,而是扩大适用至以租赁合同中的租金债务等为主债务的全部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由于保证合同一般以书面等形式作出(民法第446条第2、3款),因此最高额保证合同中保证额上限也要求以书面形式作出(民法第465条之2第3款)。
第二,民法规定,为因经营活动而负担贷款等债务提供个人保证(包括最高额保证)时,须签订公证书。尽管经营活动相关债务一般数额较大,但依然会出现对主债务人的业务内容不了解的个人轻易为其提供保证的情形。因此,除主债务人为法人且其董事作为保证人等情况之外(民法第465条之9),保证人必须于保证合同订立前一个月内签署《保证意思宣明公证书》(修订后民法第465条之6)。据此,保证人的担保意思经公证人公证后,保证合同才生效。再者,委托自然人为因经营活动而产生的主债务(不限于“贷款等债务”)提供保证时,主债务人有义务向受托人(即保证人)提供自己的财产情况、是否有除主债务以外的债务及其数额等信息(民法第465条之10第1款、第3款)。如果主债务人怠于行使该义务,致使保证人对主债务人的财产状况产生错误认识从而订立保证合同,且债权人对信息提供义务懈怠之事实知道或应当知道时,保证人有权撤销保证合同(民法第465条之10第2款)。因此,即使是债权人,民法也要求其留意主债务人是否向保证人提供了准确信息。
第三,无论受托保证人是法人还是个人,民法都明确规定债权人对其负有提供信息的义务。如保证人提出请求,债权人须立即向保证人提供主债务的本金、利息等信息以及是否有不履行等相关情况(民法第458条之2)。
此外,在个人保证中,主债务人享有的期限利益丧失时,债权人应自知道该利益丧失之时起两个月内通知保证人(民法第458条之3第1款)。债权人未履行该义务时,不得向保证人请求通知实际到达前产生的延迟损害金(同条第2款)。
日本商工会议所和全国银行协会主导设立的“经营者保证准则研究会”,主要针对企业经营者为中小企业金融债务提供保证(经营者保证)的情形制定了《经营者保证准则》(本节以下简称“准则”),并于2014年起实施(2019年制定并公布了《以企业继承为焦点的〈经营者保证准则〉特别准则》)。准则虽然包含“推动不依赖经营者保证的融资的发展”等在保证合同订立阶段实施规制的内容(参照准则第4-6项),但本文将集中介绍与处理保证债务相关的准则(准则第7项)。准则规定的处理保证债务的程序分为主债务与保证债务一并处理之情形(即一体型),以及仅就保证债务进行处理之情形(即单独型,参照准则第7项(2))。
一体型是指,利用准则型法庭外债务重组程序(中小企业活性化协会提出的程序、特定调解程序等),将主债务和保证债务一并处理的程序。与之相对,单独型的典型情况是,主债务人企业通过破产程序等法定程序处理债务时,将保证债务分离出来(但须与之密切关联),利用准则型法庭外债务重组程序对其进行处理。
此外,准则规定的程序与法院的特定调解程序(一项特别的调解和债务清偿程序,旨在帮助无法清偿债务的法人或个人实现经济上的再生,其法律依据是《关于促进特定债务等调整的特定调解法》)的结合运用也十分引人注目。日本律师联合会(日辩联)针对申请特定调解程序前的谈判步骤、适用特定调解程序时的注意点等,制定了将其规范化的指引。
经过2020年的修订,目前该指引主要包括《作为企业事业再生支援手段的特定调解方案利用指引》(事业再生与准则的保证债务处理的“一体再生型”相对应)、《基于经营者保证准则作为保证债务整理手段的特定调解方案利用指引》(保证债务整理“单独型”)、以及与前述准则2019年追加的特别准则部分相对应的《作为企业的停业·清算支援手段的特定调解方案利用指引》(企业顺利停业、清算与处理保证债务一体进行的“停业支援型”)。[1]综上,准则并未局限于经营者保证债务处理,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与企业作为主债务人时债务整理(清算、再建、停业)程序相互关联乃至一体化的程序。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着眼于特定调解的日辩联所提供的方案也显示出与准则相同的方向[2]。根据金融厅的资料,2021年度基于准则成立的保证债务处理案件中,民间金融机构作为主银行(主银行的定义由各金融机构自行定义)的案件有224起[3]。虽然对于案件数量是否充足这一点评价有所分化,但随着新冠疫情下作为经营支持政策而实施的“无息和无担保贷款(零零贷款)”偿还工作的全面展开,在可预见的未来,企业倒产仍将持续增长,基于该准则的程序也许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受理时现存额主义”相关问题
(一)主债务人被裁定受理破产的情形1.受理时现存额主义
假设A向B提供了100万日元贷款,由C为债务人B提供连带保证,而后主债务人B被裁定进入破产程序。破产法第104条第1款规定,如本案中的主债务人B和保证人C,在“多人均承担全部履行义务的情况”(即同时存在多个负有全部清偿义务的债务人)下,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被宣告破产,债权人可以“以其在破产宣告之时拥有的债权全额”参与破产程序(受理时现存额主义)。即在前述案例中,A有权作为100万日元的破产债权人参加B的破产程序,即使保证人C在B被裁定破产后向A偿还了80万日元,A在B的破产中依然可以行使100万日元的破产债权(无需将债权申报额减少为20万日元)(参照第104条第2款)。受理时现存额主义的基础是,债权人通过设置多个清偿义务人将责任财产集聚,以确保该债权的实现,即使是在破产程序中也要尊重该制度的目的。此外,将债权申报额确定为破产受理时的债权额也能使债权的处理简单化、效率化。
2.将来求偿权人的地位
前文案例中,即使在B被裁定破产后连带保证人C的担保债务未清偿,C也可以作为“将来可能行使求偿权的主体”参加B的破产程序(破产法第104条第3款)。但是如果A参加B的破产程序,A优先获得清偿,C将不能再行使求偿权(该款但书)。如果B被受理破产后C向债权人进行了清偿,则仅在全额清偿该债权时,C才能在其求偿权范围内以破产债权人的身份行使债权人所享有的权利(该条第4款)。此外,如果C是以自己拥有的所有物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则C并非负有全部清偿义务的债务人。但是破产法第104条第5款规定,B被受理破产后物上担保人C的部分清偿、将来求偿权等参照适用保证人相关规定,即参照适用同条第2-4款。
3.受理现存额主义相关判例的主要问题
(1)对全部义务人存在数笔债权的情形
假设A对其主债务人B拥有3笔债权(各为100万日元),B被受理破产,在该程序进行期间内B的债务的连带保证人C向A偿还了150万日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多笔债权视为一笔债权(300万日元),则属于部分清偿了全部债权(总债权单位说);与之相对,如果将三笔债权视为不同的债权,则是全额清偿了第一笔债权、部分清偿了第二笔债权、未清偿第三笔债权(笔单位说)。第一种学说下A可行使的破产债权额为300万日元,第二种学说下则是200万日元。最高裁在该问题上采取了笔单位说(最判平成22·3·16民集64卷2号523页,尽管该案是关于主债务人破产时物上担保的清偿案例)。该判决认为,从立法本意来看,采用受理现存额主义的破产法第104条第1款和第2款认可破产债权存在“破产债权额与实体法上的债权额的乖离”。而且,既然同条第2款所指“其全部债权”并未规定为“破产债权人拥有的总债权”,则应当理解为每笔债权相加后的总额。如遵循该判例采用的笔单位说,则会产生的以下相关问题,即,如债权人与破产人达成清偿抵充合意(民法第490条)对各笔债权按份进行清偿抵充,是否对各笔债权都分别适用受理时现存额主义。最高裁在与上述判决类似的案件(连带保证人破产案件)中,最高裁认为,清偿超过一年直到提起上诉才进行抵充会显著损害法的安定性,以此为由否定了抵充权的行使(最判平成22·3·16判时2078号18页)。不过,最高裁的观点是以接受清偿的债权人及时行使清偿抵充的行为有效为前提的(但否认清偿抵充协议在破产程序上效力的说法也十分有力),因此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应及时恰当行使基于清偿抵充协议所享有的抵充权,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受理时现存额主义。
(2)本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害金债权是否为独立的债权
从前文已经介绍的最判平成22·3·16的一案所采用的笔单位说观点进一步展开思考,如果对主债务人发生的破产债权是由破产受理前产生的本金债权、利息债权和损害金债权构成的,则需要判断实质上具有不同性质的各债权是否已经“全额消灭”(破产法第104条第2款)。在保证人破产的案件中,若主债务人在法院受理保证人破产后清偿债务,则会遗留一些问题。民法第447条第1款规定,“保证债务包括与主债务相关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及其他从属于其债务的全部债务”。如果将该款理解为其将保证人的债务定义为一项概括性的债务(民事诉讼中针对诉讼标的物通常采取这样的观点),那么就会出现以下质疑,即,分别偿还本金债权或利息债权等各单独部分债权就有可能被认定为部分清偿全部债权。但破产法对全部义务人破产时债权人的地位作出规定时,并未区分主债务人破产和保证人破产的情况。综合考虑前述采用“笔单位说”的判例和学说对受理时现存额主义的适用作出了限缩性解释,主债务人在保证人破产后清偿的情形中,似乎也应将主债务本金、利息和损害金的部分理解为独立债权。在未公开的大阪地堺支部判平成29·2·10判决中,裁定了如果主债务人在担保人的破产程序开始后偿还全部本金债权,则保证债权人将因此无法参加破产程序(破产法第104条第2款)[4]。
(3)分配额超过债权人债权额的处理
依照前文介绍的最判平成22·3·16的观点,采用受理时现存额主义意味着认为“破产债权额与实体法上的债权额存在乖离”。于是,假设负担100万日元主债务的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担保人清偿了80万日元,此时尽管实体上仅剩余20万日元的债权,债权人依然能行使100万日元的破产债权,其结果是,当清偿超过20万日元(20%)时,就会产生所谓的超额分配。因此,受理时现存额主义理论上包含了超额分配的可能性。关于如何处理超出的部分学界存在争议,但最决平成29·9·12民集71卷7号1073页(案件争议点为是否基于破产法第104条第5款的规定适用该条第2款)一案认为受理时现存额主义允许债权人获得超过实体法上债权额的分配,超过部分应当分配给该债权。但该判决的附带意见认为,接受了超额分配的债权人有可能构成不当得利,从而对其他求偿权人负有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后来求偿权人也确实提起了不当得利返还之诉,法院判决不当得利成立(大阪高判令和元·8·29金法2129号66页)。总结上述判例可知,受理时现存额主义这一破产法上的立法主义会导致超额分配的出现,在倒产程序内暂时无法处理这一问题,制度上可能仍存在改良的空间。就实务上的对策而言,还是应当在破产程序中寻求该问题的解决方式,比如破产管理人可以推动债权人向求偿权人转让超额部分的分配请求权等。
根据民事再生法第86条第2款和会社更生法第135条第2款,破产法第104条适用于这两种程序。但是由于可以通过计划(再生计划与更生计划)进行权利调整和清偿,有一些地方与破产有所不同。本文将以民事再生程序为例简要论述。
第一,在主债务人的再生程序中,即使保证人进行了部分清偿,再生债权人也可以按裁定再生时的债权额行使权利(适用破产法104条第2款)。执行再生计划期间,如果保证人全额清偿再生债权,则其有权代位该再生债权人参与清偿(适用同条第4项)。破产程序中出现的“超额分配”在重整程序中表现为以下形式:假设债权人A就1000万日元的再生债权同意了将20%的债权(200万日元)分4次(各50万日元)清偿的计划,收到第一次清偿的50万日元后,担保人B向再生债权人清偿了920万日元,此时A能否继续收下第二次清偿的50万日元?如果A收到了第二批的清偿,则其实体法上剩余的30万日元债权与第二次清偿的50万日元之间出现了20万日元的差额,进而产生超额清偿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理论上与破产程序中的超额分配相同,该超额清偿合法,实际利益的调整可以在事后适用不当得利制度调整。实务上一般提倡在再生计划中预先设置“适当条款”,以确保保证人能够代位行使超额清偿部分的债权。
第二,保证人在民事再生程序开始时有一些特殊问题。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对保证债权适用受理时现存额主义,因此以受理重整时的保证债权额为基准按照再生计划清偿债权后,再生债务人(保证人)依清偿额对主债务人享有求偿权。另外,即使针对担保债权达成了清偿计划,如果主债务人没有不履行债务,则应暂时中止依照再生计划清偿债务,如果主债务人失去了期限利益,则应一并偿付在此时之前按照再生计划已到期的保证债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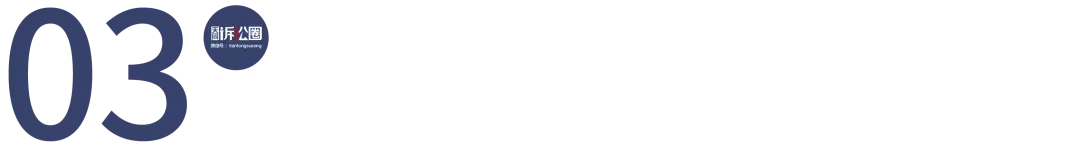
倒产程序中与保证相关的问题
(一)集团企业破产的特殊问题
在日本,通过资本关系等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企业集团成员,共同制定商业战略、筹措资金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在集团企业之间通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且在与外部开展交易和与金融债权人的往来关系、存在保证担保、财产担保和抵销等各种担保关系极为常见。因此,当整个集团企业陷入经营危机而进行事业再生时,必须在集团层面上整体掌握集团企业倒产债务人的财产,促进破产债权人实质上的平等、公平。美国联邦破产法以判例法的形式发展出了“实质合并原则”,尽管在日本很难贯彻这一点,但实务中已经参考了该原则。集团企业再生(庭内重组或庭外重组)的具体对策包括,统一集团内各企业的重整计划的清偿比例(即所谓的帕累托清偿条款),关联公司间债权的劣后化等。本文将聚焦于保证这一主题,并探讨以下问题。假设A银行向构成集团企业的B、C、D中的B公司提供1亿日元贷款,C公司为该笔债务提供连带保证,结果B、C、D公司破产,目前正在制定该集团企业的整体重整计划和清偿计划。这种情况下,如果A银行对其交易是建立在集团整体信誉的基础上的,那么就有可能将A银行对B公司的债权和对C公司的保证债权视为对整个集团的债权。关于保证的具体处理办法,一般包括:
(1)将主债务及保证债务相关债权视为“重复债权”,保证债权予以消灭;
(2)在清偿计划中针对保证债务设置比主债务更低的清偿率等方式。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以有关各方的合意为基础的庭外重组暂且不论,在民事再生程序等庭内重整程序中,存在与作为法的基础理念的受理时现存额主义相冲突的一面。因此,无论是采用庭内重组还是庭外重组,为了使这种处理方式具有正当性,必须考虑A银行取得担保的过程,以集团整体业务和财务状况为基础的信贷管理为前提,并且必须谨慎地向处于不利地位的债权人作出解释。
(二)主债务人的重整计划中保证人的免责
美国联邦破产法同样规定,破产程序中债务人的免责效力原则上不及于担保人等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参照美国联邦破产法第524条(e))。但依照第11章重整程序,重整计划中可以设置包括保证人在内的第三人免责条款,且存在承认其效力的判例。然而,日本学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不十分活跃。但就像先前介绍过的,主债务人企业和基于经营者保证准则的经营者保证人的债务整理程序的一体化处理实际上也正在实践。虽然这与在主债务人的重整·清偿方案中直接规定保证人的方法不同,但在将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债务整理程序联系起来处理这一方向性问题上是共通的。
(三)其他的问题点
虽然有点牵强,但在涉及保证的其他破产法问题中,最高裁判例反映出一些问题点,在此简要提及如下:
第一,破产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未取得对价而提供的保证是否属于无偿否认(破产法第160条第3款)的对象。最高裁的判例(最判昭和62·7·3民集41卷5号1068页)中,判决了主债务人(所谓的“同族公司”,即由家庭成员等特定的控股股东掌握经营权的公司)的代表人兼实际经营人提供的保证属于无偿否认的对象。其依据是:
(1)无偿性判断仅针对破产人作出即可(不要求针对受益人,对债权人而言也具有无偿性);
(2)经营人的破产程序是独立于公司的个人的破产,因此即便本案保证是由同族公司的经营人个人作出的,其本身也不构成否认其属于无偿否认的理由。
第二,如果主债务人(个人)根据免责许可的裁定而被免除了对破产债权的清偿义务,保证人能否援引主债务的诉讼时效进行抗辩。关于这个问题,最高裁判决认为,成为免责对象的债权已经不能通过提诉请求履行,也不能被强制执行,已经无法确定“能够行权的时间点”(民法第166条第1款第2项)这一时效起算点,也不再存在时效的观念,因此保证人不能再援引其诉讼时效(最判平成11·11·9民集53卷8号1403页)。
最高裁针对免责效果采用了自然之债的立场,否定了该债权的诉讼时效可能性本身,因此不允许保证人援引诉讼时效。另一判例的立场是,当破产人(主债务人)是法人时,破产程序终结,法人格消灭,公司负担的债务也随之消灭,因此保证人也不能援引主债务的诉讼时效(最判平成15·3·14民集57卷3号286页)。但是,如果主债务不是因为破产免责,而是根据再生计划而获得部分豁免,保证人可否就免责部分援引相关事项。虽然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直接判例,但通过再生计划批准部分免除重整债权,其效果应当认为和破产免责相同,因此基于该立场可以得出结论,该种情况下应当同上文的主债务成为破产免责对象债权一样,保证人也不能援引诉讼时效抗辩。
第三,保证人通过清偿代位(参照民法第501条)取得与主债务相关的原债权(财团债权或共益债权),此时保证人能否将原债权作为财团债权等行使。现有判例认为,转移至代位清偿人的原债权是“以保障求偿权为目的设立的具有附属性的债权”,因此有观点认为保证人取得的原债权不应具有超过其求偿权(破产债权)的优先性。但是最高裁在保证人的代位清偿为争论点的民事再生案件中,认为(1)原债权是为保障求偿权而设立的一种保证,(2)即便认可代位清偿人的优先权也不会对其他再生债权人造成不当的不利影响,以上述两点为理由认可了作出了代位清偿的保证人能够将原债权作为共益债权行使(最判平成23·11·24民集65卷8号3213页)。在破产程序中也是与之相同的结论(最判平成23·11·22民集65卷8号3165页,虽然不是关于保证的案例,但与上文最判案例判旨大致相同)。
最后,如果保证人在主债务人受理破产后清偿,是否可以将由此产生的求偿权(破产债权)作为主动债权,将破产人拥有的债权作为被动债权,两者予以抵销(破产法第72条第1款第1项的禁止抵销是否妥当)。最高裁在一起未受破产人委托提供保证的保证人实施抵销的案件中认为,“允许将求偿权作为主动债权进行抵销,等同于允许非因破产人的意思或法定原则无理由地在破产程序中优先处理债权”,不承认对抵销的合理期待,通过类推适用破产法第72条第1款第1项禁止了抵销。该判决的附属意见认为,针对受到主债务人委托的保证人,将求偿权作为主动债权进行抵销的合理期待应受到保护。由于破产程序中有禁止抵销的规定,受委托保证人和未受委托保证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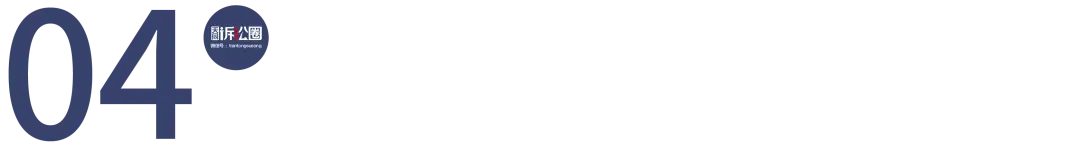
结语
在探讨破产程序中的保证问题时,我们再次看到保证制度在处理个人和企业破产的情境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应当足以说明保证在倒产程序中的重要性。日本正在针对作为企业主体增信的一大支柱——物的担保制度进行担保法律制度的修订,目前法制委员会正在进行审议[5]。虽然随着对集合债权、动产担保等更全面的把握,担保法律制度逐步完善,保证制度的实践做法或许也需要再完善,未来破产程序中保证相关法律问题的释明也将依然重要。
参考文献:
中田裕康『債権総論〔第4版〕』(岩波書店、2020年)小林信明=中井康之編『経営者保証ガイドラインの実務と課題[第2版]』(商事法務、2020年)松下淳一=相澤光江編集代表『事業再生・倒産実務全書』(金融財政事情研究会、2020年)「倒産と担保・保証」実務研究会編『倒産と担保・保証〔第2版〕』(商事法務、2021年)
注释:
[1] https://www.nichibenren.or.jp/activity/resolution/chusho/tokutei_chotei.html(日本律师联合会HP,2022年9月9日最后登录)。
[2] 最近受到政府的《成长战略实行计划》(2021年),民间组织“中小企业事业再生研究会”制定的《中小企业事业再生准则》(2022年4月起实施)也实行主债务与担保债务的一体化处理。“经营者保证准则研究会” 为在主债务人企业倒闭时能够适用经营者保证准则,在前述《中小企业事业再生准则》公布的同时,总结了《停业时〈经营者保证准则〉的基本思考》。关于以上各种准则(包括Q&A)请参考https://www.zenginkyo.or.jp/adr/sme/(全国银行协会HP,2022年9月9日最后登录。)
[3] https://www.fsa.go.jp/news/r3/ginkou/20220623-2.pdf(金融厅HP,2022年9月9日最后登录。)
[4] 参考盐路广海《关于担保债务履行请求权的宣告时现存额主义的适用》,银行法务21.824号30页。
[5]https://www.moj.go.jp/shingi1/housei02_003008.html(法务省HP,2022年9月9日最后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