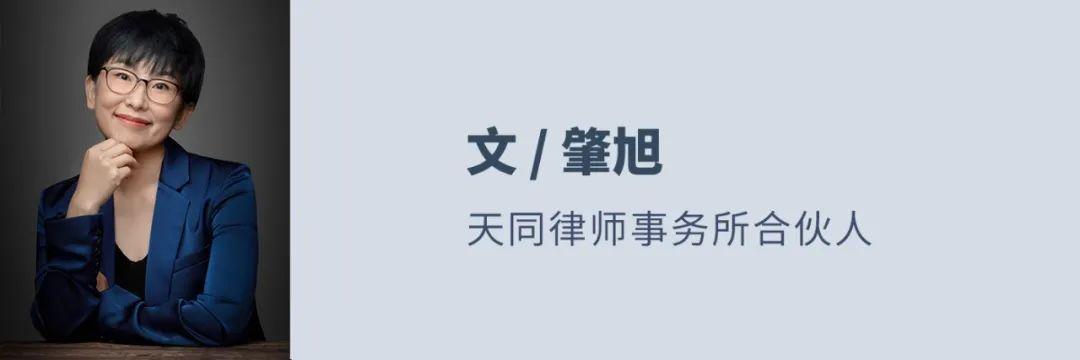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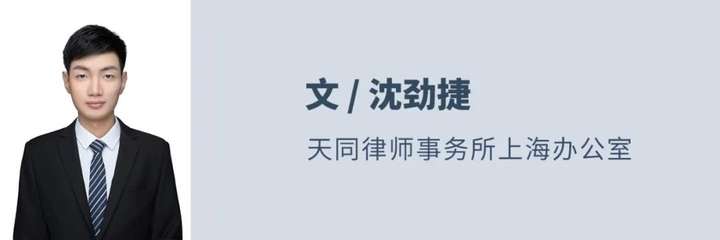
本文共计3,688字,建议阅读时间7分钟
实践中,员工为充分举证,可能会将企业的商业秘密作为证据在诉讼程序中加以利用。员工的该种行为是否侵犯商业秘密?目前法院给出的回答并不统一。
“深圳光汇云油电商有限公司与黄郑苏侵害经营秘密纠纷案”[1](下文简称“光汇云油案”)中,被告为证明自己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现与工作内容,在此前进行的劳动仲裁中向仲裁委提交了八页涉及公司商业信息的证据。法院认为,一方面,原告并未对案涉商业信息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进而不构成商业秘密。另一方面,即使案涉商业信息构成商业秘密,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保护也应让位于对被告充分举证权利的保护。其原因在于,原告享有的商业秘密是实体法下的权利,被告享有的充分举证权利是程序法下的权利,本着程序法优先于实体法的原则,即使被告提交的证据涉及了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也可得到豁免。
“土巴兔(深圳)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聚豪建筑工程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2](下文简称“土巴兔案”)中,被告(项目经理)涉嫌将案涉项目信息透露给项目工人(案外人),以便该工人将其作为证据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进行举证。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市场正当经营秩序、规范经营者诚信经营,本案中,被告并未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使用原告的商业信息,并不具有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竞争利益的目的,因此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行为。
“佛山华丰纺织有限公司与朱汝南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3](下文简称“华丰纺织案”)中,被告在任职期间采用非法手段窃取了原告的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财务资料,并将上述资料作为证据在其他民事诉讼案件中使用。法院认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被告的行为属于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商业秘密的侵犯。
可见,法院在分析“员工为举证而利用商业秘密是否侵犯商业秘密”这一问题时的切入角度并不统一。“华丰纺织案”的审理法院从《反不正当竞争法》文义的角度切入,认为为举证而利用商业秘密的行为符合文义解释,构成侵犯商业秘密。“土巴兔案”的审理法院从竞争秩序的角度切入,认为该行为并未给商业秘密所有人带来竞争损害,也未对竞争秩序造成破坏,故不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光汇云油案”的审理法院从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的角度切入,认为即使该行为属于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也存在相应的抗辩事由使得员工得以免责。
从以上裁判观点中可归纳出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如本文题目,员工“为举证而利用商业秘密”是否侵犯商业秘密?其二,进一步地,如果员工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是否存在相应抗辩事由?本文将针对这两点分别进行分析。
一、员工“为举证而利用商业秘密”是否侵犯商业秘密?
尽管世界各国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模式不尽相同,美国也一再敦促我国将商业秘密制度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剥离出来,采用单独立法的模式进行保护,[4]但我国现阶段对商业秘密仍采取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的保护模式。[5]其原因在于,行为人侵犯他人商业秘密,目的在于损害他人竞争利益,从而使得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为优势的地位。因此,保护商业秘密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联系紧密,[6]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不应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孤岛,而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其他不正当行为同样对待。即,判断某种行为是否侵犯商业秘密时,不仅要考察该行为是否满足《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具体要件,也要考察该行为是否在实质上破坏了市场竞争秩序,给经营者和消费者带来了不合理的损害。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类型主要包括非法获取、披露及使用三种。更具体地,员工出于充分举证的需要,可能采取如下行为:其一,以提交证据为目的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其二,为他人在诉讼程序中使用,而向他人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其三,直接将商业秘密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
就“以提交证据为目的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而言,笔者以为,不能仅因该行为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构成要件就直接判定其侵犯商业秘密。从立法论来看,“非法获取”行为本身并不会对商业秘密所有人的竞争优势带来直接损害,然而法律仍然将其规定为一种独立的商业秘密侵犯形态的原因在于,立法者推定不正当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人会进一步披露、使用该商业秘密,[7]从而给商业秘密所有人带来竞争损害。如果员工可以证明其非法获取商业秘密的目的在于提交证据,其行为将导致商业秘密被不当披露、使用的推定即被推翻。换言之,该情形下,“非法获取”作为一种独立的侵犯商业秘密形态的合理性基础被推翻,企业若想证明员工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则需要进一步证明,员工除了打算将非法获取的商业秘密作为证据在诉讼程序中使用外,还可能将商业秘密不当披露或使用,进而对市场竞争秩序以及企业的竞争优势造成威胁。
就“为他人在诉讼程序中使用,而向他人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而言,首先,笔者认为,该行为属于“披露”,而非“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披露”行为是指使得信息溢出原有存在范围的行为[8]。“使用”行为则是指会导致行为人在市场竞争中获益或使得商业秘密所有人在市场竞争中遭受损害的行为,如直接利用商业秘密生产产品、使用商业信息吸引客户[9]以及以商业秘密为研究起点辅助研究等。“为他人在诉讼程序中使用,而向他人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显然不符合“使用”的定义,其与市场竞争无涉,即使该行为导致企业败诉进而对其产生损害,该损害也不是竞争损害。
其次,法律对披露行为进行规制的原因在于商业秘密的价值部分倚重于其秘密性,披露很可能会减损商业秘密的交易可能性以及其被交易的价格。[10]对商业秘密的披露还会增加商业秘密被他人使用的可能性,使得商业秘密所有人在竞争中受到不合理的损害。即,向他人提供商业秘密,即使出于为他人在诉讼程序中使用的目的,该行为仍可能减损商业秘密的秘密程度,导致商业秘密被他人不当使用,进而使得商业秘密所有人的竞争优势受到损害,给市场竞争秩序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该行为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披露行为。
就“直接将商业秘密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供”而言,如前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不当披露的原因在于该行为会增加商业秘密被他人不当利用的风险,对商业秘密所有人的竞争优势造成损害。然而,若诉讼采取不公开审理等方式,使得商业秘密只向诉讼参与人员披露,鉴于诉讼参与人员对接触到的商业秘密负有法定的保密义务,该种形式的披露并不会增加商业秘密被他人不当利用的风险,故而不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披露行为。
二、是否存在相应抗辩事由?
进一步地,当员工为举证而侵犯了企业的商业秘密时,可以何种事由抗辩呢?我国现行法对此并未规定。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公共利益抗辩或许值得探讨。
公共利益抗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以其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为例,一路经历了“对不法行为进行抗辩”“以正当理由进行抗辩”以及“以利益平衡为考量主线”三个历史阶段。[11]在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形成之初,该制度只适用于存在不法行为的情形。如1856年的Gartside v. Outram案[12],被告作为原告的前雇员,将原告的商业欺诈行为公之于众,原告以被告违反保密义务为由将其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决认为不存在阻止披露不公正行为的保密义务,[13]该判决表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胜过私人义务的履行。[14]然而,单纯的对不法行为的抗辩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公共利益抗辩的外延不断向外拓展,进而逐渐形成了“以正当理由进行抗辩”的制度。[15]如1966年的Initial Services Ltd v. Putter案[16],法院判决认为公共利益抗辩不应仅限于犯罪与欺诈行为,而应扩张至任何涉及公共利益的不当行为。此后,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继续发展,逐渐形成了现阶段以利益平衡为考量主线的判断标准。[17]
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在美国也展现出了极其丰富的外延。如2000年的Westcode, INC. v. Daimler Chrysler Rail Systems INC.案[18],美国法院认为尽管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但颁布禁令会使得地铁车辆返修工作延期,从而影响乘客乘坐地铁出行。据此,美国法院以关乎公共交通便利与公共安全为由,拒绝颁发禁令。由是观之,公共利益抗辩制度发展至今,其外延是十分宽泛的,除了存在违法行为、欺诈行为、危及公众健康的行为等较无争议的可以构成公共利益抗辩的行为外,其他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行为也有可能借由利益平衡的桥梁进入公共利益抗辩的事由范围。
就本文讨论的“为举证而利用商业秘密”的行为而言,从微观来看,该行为是对个体举证权利的维护,从宏观来看,该行为亦是对诉讼制度落实与正常运作的保障,与公共利益存在关联,有适用公共利益抗辩制度的空间。且从比较法上来看,“基于司法程序的利用”与“基于公共利益的使用”往往密不可分。譬如加拿大《统一商业秘密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了两项对侵犯商业秘密的抗辩,其一是基于司法程序的利用,其二是基于公共利益的使用。又如德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对著作权的限制,其标题便为“司法与公共安全”。可见,“基于司法程序的利用”与“基于公共利益的使用”往往密不可分,“为举证而利用商业秘密”似乎有纳入广义的公共利益抗辩进行考量的空间。
本文系天同(上海)知识产权团队的《商业秘密研究报告》系列文章之一,后续文章与最终报告将陆续通过本平台发表,敬请期待。
注释:
[1]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91民初5537号。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粤03民终1461号。
[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604民初15572号。
[4]USTR: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5]马忠法、李仲琛:《再论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模式》,载《电子知识产权》2019年第12期。
[6]孔祥俊:《商业秘密司法保护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7]黄武双:《商业秘密保护的合理边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
[8]朱谢群:《商业秘密法中“不可避免披露”原则的规范性分析》,载《科技与法律》2003年第4期。
[9]Restatement (Third) of Unfair Competition§40, comment c.
[10]同前注,黄武双书,第73页。
[11]黄武双:《英美商业秘密保护中的公共利益抗辩规则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知识产权》,2009年第2期。
[12]Gartside v. Outram (1856) 26 L. J. Ch. 113, 114.
[13]尹腊梅:《知识产权抗辩体系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50页。
[14]何雨:《商业秘密保护中的公共利益抗辩规则研究》,2015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5]同前注,黄武双文。
[16]Initial Services Ltd v. Putter, (1968) 1 Q. B. 396.
[17]同前注,黄武双文。
[18]Westcode, Inc. v. Daimler Chrysler Rail Systems (North America)Inc., 123 F. Supp. 2d 819, 825 (E.D.Pa., 2000).
免责声明
本文及其内容仅为交流目的,不代表天同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建议或决策依据。如您需要法律建议或其他专业分析,请与本文栏目主持人联系。本文任何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需转载或引用,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取得授权,并于转载时明确注明来源、栏目及作者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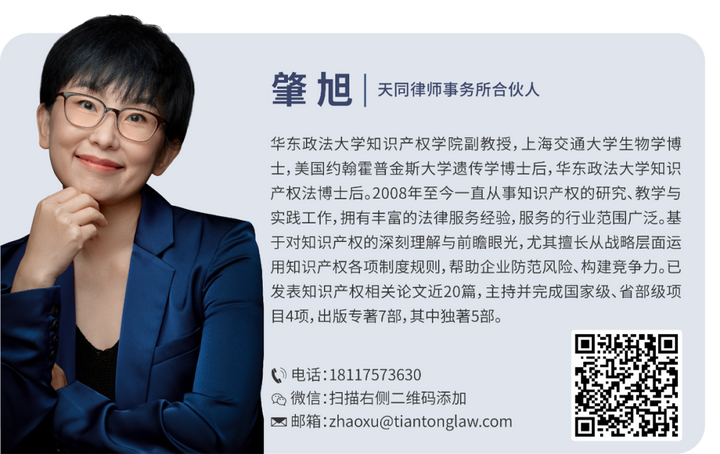

天同说知产!一同说知产!“同说知产”栏目聚焦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我们希望借此栏目搭建知识产权理论与法律实务、商业实践的衔接、交流互动平台。如您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点击文末留言。
向“同说知产”栏目投稿,欢迎发送邮件至:
zhaoxu@tiantonglaw.com
suzhifu@tiantong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