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尽管数字货币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新事物,但是,民法的法教义学具备一定的开放性,足以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针对货币规则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适用于数字货币这一核心问题,可以根据数字货币发行主体和采纳技术的不同,将其分别涵摄到不同的权利类型下,以提供相应的解释方案。首先,法定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以数据为载体的现金货币,直接适用货币规则。其次,非法定数字货币基于技术,可以区分为非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法定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法定数字货币,前者是债权,后者是绝对性财产权。最后,两种非法定数字货币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类推适用货币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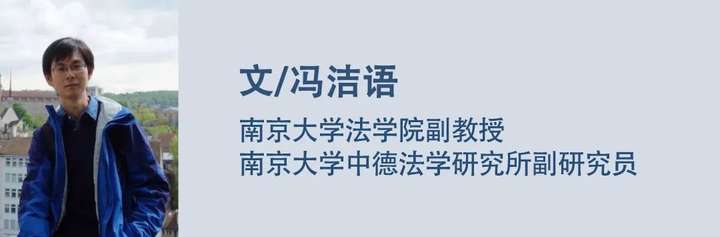
注:本文发表于《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7期。本文共计20,126字
内容提要:根据发行主体,可以将数字货币区分为法定数字货币与非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也即目前试点的数字人民币,其性质为以数据为载体的现金。相反,非法定数字货币欠缺法偿性和强制受领力,根据技术的不同,可以分为非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传统数字货币(Q币为代表)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数字货币(比特币为代表)。前者的法律性质为债权,后者的法律性质是绝对性财产权。而在货币规则的适用问题上,数字货币能否适用“占有即所有”的货币物权法规则,取决于是否发生混合。在货币之债规则的适用方面,不论是何种数字货币,在交易中均起到部分货币的作用,数字人民币原则上得适用货币之债的规则;非法定数字货币则必须在个案中考虑类推适用货币之债的可能。
关键词:数字货币;区块链;货币之债;占有即所有;履行不能
目录
一、问题的提出
二、技术与法律研究现状
三、数字货币的私法定性、归属和保护
四、货币私法规范在数字货币中的适用与类推适用
五、结语
自2008年中本聪提出比特币以来,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技术带来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尽管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等7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第1条第2款否定了非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在我国境内作为货币的流通性。但是,区块链、数字货币尤其是比特币是目前货币银行学和法学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也一直致力于人民币的“虚拟化”。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苏州等地区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与比特币相比,由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具备国家主权的担保。而在比特币之前,已经存在了其他种类的数字货币,如Q币等。三者之间的区别引人关注。另一方面,因比特币而产生的案例逐渐显现。例如,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日本,均发生了比特币交易平台与比特币持有人之间的权利归属纠纷案件。[1]在交易平台破产以后,在平台享有比特币的人对于平台是否享有取回权存在争议。此外,尽管我国央行禁止比特币的流通,但是我国法院并不禁止使用人民币购买比特币。[2]
由此可见,围绕数字货币大致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法律定性层面,法定数字货币和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在法律定性上是否存在差异;比特币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与Q币等非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在法律定性上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如果不同数字货币的法律定性存在差异,那么是否影响规范适用。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货币之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类推适用于数字货币的交易。与这一问题相关,区块链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对于传统货币之债、买卖合同等法律规则在何种程度上会造成影响,同样值得进一步深思。
根据所采技术可以将数字货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第二类为不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
第一类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其典型代表为比特币,特点在于去中心化。此种去中心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比特币没有发行机构;第二,比特币在移转过程中依赖区块链技术,没有中间商。前者的含义较为简单,后者则必须结合比特币交易过程加以理解。比特币是一种存在于点对点网络(P2P)中可以转让的价值单位,在移转过程中,比特别的交易双方需要使用“比特币钱包”,钱包内有比特币地址,而地址是通过比特币公钥推导得出的。[3]比特币公钥和比特币地址的概念基本重合,仅仅是不同的形式,[4]其作用在于受领比特币,类似于银行账户的功能。[5]在公钥以外,比特币交易还需要私钥,私钥起到授权交易的作用,[6]持币人通过私钥对比特币进行加密,加密以后,得以证明交易真实,交易人对自己的发出的交易信息不得抵赖。[7]比特币的交易并非依赖传统的单个中间商,而是存在于整个比特币网络,记录于每台装有比特币程序的计算机。比特币此种去中心化的网络,每十分钟创建一个区块,内含这段时间内全球所发生的交易,并且也包括前一个区块的ID,形成了完整的交易链条,因此被称为区块链。[8]区块链可以分为公有链、联盟链和私有链,其区分标准是写入数据的权限,公有链对所有人开放权限,是完全的去中心化;联盟链次之,而私有链仅一家机构享有写入的权限。[9]比特币所基于的区块链是公有链,但在未来也可能出现选用联盟链或私有链的数字货币。
区块链一方面使得所有的比特币交易均得到了完整的记录,另一方面,也使得特定交易得到了认可。例如,假设在交易1中,甲、乙、丙和丁各有10枚比特币,如果甲想要将自己的1枚比特币移转给丙,那么甲必须先填写丙的公钥和1枚比特币的来源,然后通过私钥对其加密,将该交易信息发送到全网(乙和丁),乙和丁收到该信息后进行解密,验证私钥等,如果符合,则认可该交易,丙随即取得1枚比特币。之后,发生交易2,丙将1枚比特币移转给丁,丙填写的信息中,必须包括交易1的信息,随后加密并发送全网。最终的结果是,甲拥有9枚、乙拥有10枚、丙拥有10枚和丁拥有11枚。在交易2中既包括交易1的信息,也包括交易2的信息。也就是说,每个区块均与上一个区块相连,从一个区块可以溯源至最初的区块,由此形成所谓区块链。[10]并且由于交易信息必须公示全网,在全网中,该交易信息由全网所有的其他用户按照比特币的基本规则(“共识规则”)进行审核,其中包括二重买卖(重复支付、“双花”)等问题,最终根据多数决,确认交易,由此,区块链也使得特定交易得到了认可。[11]例如,甲同时用私钥加密同一枚比特币,用以完成两笔交易,两笔交易均同时发送至全网,那么,哪笔交易有效,取决于哪笔交易先取得全网认可,达到51%的认可。
第二类不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实际上早已存在日常生活中。例如,腾讯公司发行的Q币,可以在腾讯商城中购买其他虚拟财产。此外,与人民币之间存在兑换关系。与比特币相比,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存在中心,Q币等传统数字货币由腾讯等公司发行,存在中心发行人。2010年文化部颁布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2条第3款在定义网络数字货币时同样体现了中心发行的特点,该款指出网络数字货币由“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发行”。[12]
目前,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构建同样没有完全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首先,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我国人民银行发行的,[13]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仍然是存在中心。[14]而在流通过程中,是否采区块链技术,在何种程度上采区块链技术仍然存在疑问。[15]而就目前试点的数字人民币技术来看,数字人民币交易采账户松耦合的方式,交易双方均离线状态下也能交易,但交易数据仍需通过中间人(商业银行或者具备服务能力的商业机构)。[16]这就意味着,尽管我国央行没有否定在流通层面引入区块链技术,但就目前所采用的技术来看,基本没有体现区块链技术所强调的去中心化构造。
我国目前关于数字货币私法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定性和货币规则的适用展开。我国目前的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不论是法定数字货币还是如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在法律性质上,均属于货币[17]或者至少在私人之间认可其具备货币的属性。[18]其理由主要在于第一,从比较法来看,各国均通过立法或者司法判例的形式,确定了比特币是法定货币;第二,数字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记账符号,并且在区块链中具备信用;第三,处于交易便捷的需求,应当承认数字货币是货币。[19]第四,比特币等非法定货币固然没有强制流通性,但如果私人之间认可比特币的流通性,那么比特币至少在特定主体之间构成货币。[20]第五,如果不认定比特币是货币,则有保护不周之虞。[21]
对于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认定为货币自然毫无争议。但是,对于Q币、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定性,相比学说的激进态度,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仍持保守态度。针对Q币等传统非法定数字货币,2010年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第1项限定了网络游戏数字货币的使用范围,禁止其在其他交易中充当货币的功能。此种立场延续到了对比特币等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中。2013年颁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第1条一方面在公法层面否定了比特币的货币定性,另一方面明确了比特币是虚拟商品。而2017年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第1条第2款又一次强调了比特币在我国境内不具备强制法偿性和流通性等货币属性。尽管如此,对于比特币能否作为商品买卖,持有比特币的人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我国法院观点不一。有法院认为,由于比特币等非法定货币不是货币,因此买卖比特币等形成的债是非法债务,不受法律保护。在“金晨与北京火币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不论是一审法院还是二审法院均根据《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第1条第2款认定当事人所购买的数字货币并非货币,所形成的债务是非法债务为由,裁定驳回了原告请求赔偿投资损失的诉讼。[22]相反,在部分典型案例中,法院认可了比特币买卖合同的效力。在“陈某诉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中,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尽管比特币不具备流通性,但比特币可以作为商品买卖,[23]换言之,当事人之间购买比特币的合同有效。在“冯某诉A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法官在针对该案的“法官提示”部分中更明确表示,“比特币属于合同法上的交易对象,具有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民事利益’”。[24]
相较于能否买卖比特币的问题,我国法院对于比特币的不当得利返还和侵权保护态度又是统一的。在“李建锋与北京葡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尽管交易平台系违法设立,但不影响比特币的不当得利返还。[25]而在比特币的侵权案中,法院同样认可了比特币是侵权的客体,例如在“北京乐酷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绥化市华辰商贸有限公司,彭泉泉侵权责任纠纷案”中,原告起诉比特币交易平台不作为侵权导致其比特币被盗,法院认可了原告的主张。[26]而在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比特币侵权案件中,法官同样认可了比特币作为“虚拟商品”受侵权法保护。[27]
综上所述,我国法学理论对于数字货币问题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主流观点认为不论是法定数字货币还是非法定数字货币,在法律定性上均为货币,适用货币之债的规则。相反,我国金融监管机关区分了法定数字货币与非法定数字货币,对于后者持谨慎的态度,否定其货币的流通性。此种态度继而影响了我国法院的司法裁判,而司法实践中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比特币买卖合同的效力,以及比特币的保护问题。
1. 货币的定义与分类
对货币做法律上的定义存在困难,因为对于货币做法律上的定义很难脱离货币的经济功能。基于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对货币做不同的定义,其范围也有所不同。[28]我国目前的通说综合了法律规定与经济功能两个方面的因素,将货币分为现金货币与存款货币。[29]现金货币是因国家主权而具有货币功能,具备名义价值的动产。[30]现金以存款方式存入银行,同样具备交易媒介和支付结算的功能,因此,尽管存款货币在定性上是对银行的债权,但我国学说同样将其作为货币对待。[31]不论是从比较法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将存款货币归为货币均是妥当的。对于货币的法律定性,无法脱离货币的经济功能,在转账交易日趋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存款货币具备交换工具、计价单位等现金货币的作用。此外,由于存款保护规则的存在,也没有给债权人带来额外的风险,因此,存款货币是去物质化的货币。
更进一步来说,存款货币的去物质化过程,也体现了抽象货币与具体货币的分离。从萨维尼开始,学理上就区分抽象货币与具体货币。抽象货币是可度量的财产权力(messbare Vermögensmacht),是具备价值的一般等价物。[32]具体货币则具备有体性的货币。二者在规范适用上,存在差异。存款货币是典型的抽象货币,相反,现金货币由于客体有体,因此属于具体货币。[33]
2. 货币在物权法中的教义学构造
学界通说认为,货币是特殊的动产,其所有权适用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具体而言,货币所有权变动与占有统一;对于货币,权利人无原物返还请求权;货币所有权的取得无须适用善意取得,而是由货币的占有人直接取得所有权;对于货币无法成立间接占有。[34]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货币是高度替代性的种类物,只是价值的体现。[35]当然,学界对此多有反思,新近有力学说认为,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本质上是动产混合规则的适用,并且其适用领域也应当限于法律行为领域,在其他领域中,必须具体分析货币的特定性是否已经丧失。[36]也有观点指出,货币的高度替代性不必然排除货币的特定性,这一方面体现在货币也可以物理特定,另一方面更体现为价值的特定性。[37]
3. 货币在债权法中的教义学构造(货币之债)
以给付一定数额之金钱为标的之债,是货币之债(金钱之债)。[38]尽管货币之债是重要的债法概念,但其规则散见于《民法典》、特别法、司法解释与学说中,有进一步整理的必要。
第一,《民法典》第514条规定了货币之债的基本内容,即除当事人另有约定以外,货币之债的给付内容是债务人所在地的法定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3条规定了人民币的强制支付力。这就意味着,我国货币之债的给付客体是人民币。
第二,《民法典》第511条第3项第1句前半句规定,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货币之债的债务人应当在受领货币一方的住所地提供货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8条第2款同样认为受领货币一方所在地的法院具备管辖权。因此,货币之债在我国原则上是赴偿之债,[39]这就意味着债务人须承担货币的在途风险和迟延风险。例如,债务人在履行期届满之前转账,因银行过错导致履行期限届满以后,债权人才收到货币,债务人同样构成履行迟延。此外,由于货币之债无履行不能,因此,债务人无资力或者无法取得预期融资等原因也不构成不可抗力。[40]但学界少数说认为应当区分在途风险和迟延风险,债务人仅承担在途风险。[41]
第三,《民法典》第579条结合第580条规定了货币之债在履行方面的特殊性,即货币之债无履行不能。这一规则是货币之债最为特殊的规则。我国通说认为货币之债的特殊之处在于实际履行,一方面,货币作为特殊种类物,具备高度的可替代性和流通性,因此无不能;另一方面,货币作为可替代物和流通物,可以转化为违约金或损害赔偿等货币之债,但货币之债本身不能转化。[42]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说进一步认为,货币之债不是种类之债,不存在特定化的问题,故而无履行不能。[43]
由此可见,这一规则源自货币的特殊性。给付特定数额的货币,给付标的指向的是抽象货币,也即特定价值。我国学说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货币之债就其本质而言,不是种类之债或特定之债,而是提供一定数额的货币单位,以创造一定的价值为给付内容的债,学理上也将其称为“价值创造之债”。[44]一方面,由于所有的货币是同一的,因此货币之债无客观不能,总有人拥有货币。另一方面,从概念来看,货币之债有主观不能的可能性。例如,债务人在订立合同以后,陷入经济困难而无法履行,由此构成嗣后主观不能,或者在侵权之债发生时,债务人无资力,由此构成自始主观不能。此种情况下,如果是种类之债或者特定之债,则原给付义务转化为损害赔偿的次义务,但货币之债没有转化的问题,因此主观不能原则上不影响货币之债的存续。[45]
第四,由于货币是统一的价值单位,因此,一方面,通常情况下,货币之债是有偿合同的主给付义务,例如,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典型有偿合同均以货币之债为给付义务。另一方面,其他给付义务可转化为货币之债。例如,买卖合同中出卖人的给付义务,可以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
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至第30条作为借款合同的补充,规定了货币借贷的利息问题。具体而言,货币之债履行迟延,如果当事人约了利息,即使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作为迟延损害。并且利息之债也受到利息规制的限制。
综上所述,货币在私法体系中的特殊规则受到其本身特性和法偿性的影响。就货币本身的特性而言,由于货币是一种同一的价值单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微乎其微,因此,在物权变动中,货币之间极易发生混合,对于货币所有权人而言,也无利益取得与原来货币物理上完全一致的货币。货币之债不论是履行还是违约救济方面,也与给付物的债有所不同。就法偿性而言,货币是部分典型合同中法定的给付,并且迟延会产生利息。货币规则能否适用于数字货币均需要进一步检讨。对此的前提问题则是三种数字货币的定性。
我国目前的学说将三种数字货币均归为(准)货币。其理论焦点有三,其一,法定数字货币属于货币自不待言,但其与传统货币分类之间、与非法定数字货币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有待明确;其二,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定性是否妥当,需要进一步检讨;其三,不同的法律定性也决定了不同数字货币的归属和保护方式。
与其他数字货币不同,我国目前试点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定的法定货币,不具备狭义上的“去中心化”,而且存在国家信用的保障,因此,在私法定性上,数字人民币与其他人民币无异,均为货币。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数字人民币与目前流行的其他支付方式中的货币(例如,微信、支付宝支付中的货币)和现金货币是否存在差别。
与其他支付方式中的货币相比,从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设计来看,数字人民币起到替代现金的作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人在使用时,无须开设账户。这一点不同于目前流行的其他支付方式,并且直接影响了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定性。从法律定性来看,金融机构的存款、其他支付方式中的货币则属于存款货币。正如上文所述,存款货币是通过存款合同形成的,存款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国家主权没有对此种债权的实现提供担保。在支付交易中,支付存款货币基于付款人和支付银行之间的支付委托合同、收款人和托收机构之间的托收委托合同发生。[46]相反,数字人民币由央行发行,是主权货币,而非通过存款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形成的债权。根据目前的技术设计,在数字人民币的所有权方面,其采与账户松耦合的技术,也就是说,不要求数字人民币的持有人在商业银行开设账户。也就是说,数字货币的持有人与银行之间并无法律关系。在数字人民币的支付方面,数字货币的支付采双离线模式,付款人与收款人完成支付均无须联网。这就意味,银行在支付过程中,不起到履行辅助人的作用。因此,数字人民币在定性上更类似现金,是具体货币。但是,与通常的现金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的载体特殊,是以数据为载体的现金。
我国目前的学说将非法定数字货币,尤其是比特币同样定性为货币。诚然,基于意思自治,当事人可以约定以货币以外的标的物为给付对价,但是该说始终存在疑问,第一,货币的定义固然无法脱离其经济属性,但是,即使以受到从社会认可角度定义货币,也没法赋予非法定货币作为法定支付手段的效力。[47]第二,货币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认定非法定货币同样属于货币,那么其与其他货币是怎样的关系,是否是一种新的货币表现形式有待明确。第三,将非法定货币定义为货币,进而认为货币之债的规则可以直接适用于非法定货币是概念法学的结论。货币之债的特殊性在于货币是法定的支付手段,在欠缺此种特性的情况下,认为非法定货币是货币,可以适用货币之债的规则欠缺检讨。货币之债的规则能否适用于以非法定货币为给付标的的情况中,必须进行个案判断。第四,我国学说对于非法定货币的法律定性的意义并不明确。非法定货币的定性直接影响的是其能否受到侵权法保护。如果认为非法定货币非绝对权的客体,那么不受一般侵权的保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讨论非法定货币的法律定性是有意义的。鉴于上述疑虑,在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流通性得到广泛认可以前,不应将其认定为货币。而应当从归属、保护和货币规范的适用三个方面,进行个案的检讨。[48]
1. Q币等非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法定数字货币
非基于区块链的非法定数字货币存在中心化的发行人,以Q币为例,其发行主体为腾讯公司。《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第1项将网络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限定于网络游戏运营企业自身的服务或网络游戏产品。除了网络游戏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以外,在2017年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出台以前,我国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也会以发行人的身份,发行虚拟货币。[49]我国学说倾向于将Q币等传统数字货币归为虚拟财产,并认为虚拟财产构成数据。[50]此种观点或许对于其他虚拟财产,如游戏账号等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传统数字货币意义不大。因为传统数字货币的价值源自于作为发行人的认可,而非数字文件本身。换言之,数据文件本身对于持币人而言,没有价值。这一点与债权文书相同,债权文书之上虽然同样存在所有权,但债权文书的法律意义在于证明债权存在。在学理上,固然可以认为传统数字货币是数据,因此持币人可以基于数据文件请求发行人返还物权。这一点在法定数字人民币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法定数字人民币的数据取回以后,该数据反应的信息仍为货币金额。但是,对于Q币等持币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其因持有数字货币而对发行人享有的、请求提供服务或游戏产品的债权。[51]在这意义上,网络虚拟货币之所以能够购买发行人的服务或游戏产品,是因为发行人对其价值的认可,换言之,网络虚拟货币是持币人对发行人的债权。[52]
2. 比特币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法定数字货币
在对其定性之前,需要解决的前提问题是,我国央行否定了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流通性,这是否意味着否定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权利性。一方面,尽管罗马法将非流通物排除出了私法的客体,但目前民法学说均同样认可非流通物是民法的客体,只是其流通性受限。[53]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比特币的持有人仅享有事实上的排他地位,无法进行法律上的处分。[54]此种观点的依据是,比特币的成立以比特币协议为事实根据,再寻找规范根据是无必要的重复。[55]如果以该说为前提,则比特币无法成为一般侵权保护的客体,对于比特币的利用会起到抑制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此种观点是一种消极的态度。[56]事实上,即使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也仅为了指出比特币不属于物或者其他知识产权,并非认为比特币不受保护。例如,其同样认为持有比特币和利用比特币的可能性构建了具有财产价值的地位,而此种(事实)地位可以作为整体转让。[57]因此,没有理由否定比特币的归属的权利属性。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非法定货币的权利性。首先,非法定数字货币不是物,因为民法上的物限于有体物[58],持有比特币也不构成所有权。有疑问的是,比特币等区块链技术支持的非法定数字货币是否等同其他数据?在数据文件上成立所有权的前提是数据文件现实存在,并且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控制数据文件,并与其他数据文件相区分。此外,普通的数据文件不论是存储于电脑还是存储于云端服务器,至少均有数据的本体。但比特币技术则非如此,比特币技术中的公钥和私钥均不是比特币本身,而仅仅是进入账户的手段,而账户内有多少比特币,则须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中读取。由于去中心化的设计,比特币的信息存在于区块链中,也存在于每一台安装了相关软件的电脑中。在这个意义上,比特币至少不是数据文件,在比特币上不成立所有权。[59]
其次,比特币与存款货币或传统非法定数字货币不同,不是债权。我国通说认为,区块链去中心化特质不要求发行人承担法律义务,因此不存在与发行人或者第三人之间的债之关系,比特币不是债权。此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学说上仍有观点认为,在私有链或者联盟链中,由于仅特定人有权限,因此,私有链或联盟链中所有的参与人之间具备共同的目的,形成了合伙关系,而相应数字货币是基于合伙关系产生的债权。[60]也有观点将比特币归为证券化的债权(所谓的“价值权[Wertrecht]”),其认为此种价值权是指作为支付手段,使用该数字货币机会。并且该说考虑到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设计,认为比特币的移转不同于证券,而是以债权让与的方式进行。[61]比特币债权说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与债权的定义相协调。债权是指对特定人得请求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62]债权说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即使是在私有链中,也很难认为所有的用户都有法律拘束之意思,因为用户只是希望将数字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愿彼此之间负担一物;[63]其二,在公有链还是私有链中,持有比特币的人均没有可以请求的对象。在公有链中,由于彻底的去中心化,没有数字货币的发行人,也即没有债务人。[64]在私有链或者联盟链中,即使存在发行人,发行人也并不担保数字货币的兑现,这一点与存款货币不同,存款货币之所以可以被认定是债权,是因为存款银行作为债务人负有支付现金的义务。因此,比特币不构成债权。
最后,比特币的价值本质上源自区块链全体成员的合意,比特币的本质是“受到他人认可而持有的单位数,此种单位可以移转给其他参与人。”[65]此种合意由于不具备拘束意思,固然不能等同于传统合同法意义上的合意,但是应当指出的有两点,一方面,此种合意更类似共同行为的合意,另一方面,此种合意不论范围如何,但基本的合意包括认可比特币的价值和可以将比特币移转给他人。[66]此种类型的权利固然不属于债权或物权,但不容否认,比特币是民法中的客体,是所谓的“其他财产权”(或称为绝对权属性的虚拟财产),应当受到类似绝对权的保护。[67]
当然,对此也存在反对观点,其认为比特币等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不具排他性。此种观点体现在2015年日本法院在MTGOX株式会社破产案中。作为被告的MTGOX是比特币交易平台的经营者,其于2014年2月28日提交破产重整申请。原告是该交易所的用户,主张基于所有权取回其在交易平台账号中的比特币。日本东京地方否定了原告的诉请,其理由一方面在于比特币不是物,不具备物权属性,另一方面,更进一步否定了比特币具备排他性,因为比特币交易需要区块链中其他成员的参与解密,确认比特币交易的效力,换言之,与银行存款不同,某一账户内比特币的变化,是根据全网上与该账户相关的比特币全部交易的计算差额得出的。比特币也没有如同数据之类的记录。因此,即使是拥有私钥的人,也无法排他性支配账户中的比特币。[68]此种观点是存在疑问的,日本学者虽然均支持该判决的结论,但东京地方法院的说理没有受到学者的认可。[69]另一方面,否定用户取回权的原因不在于比特币本身不具备排他性,而在于用户与交易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此外,按东京地方法院的观点推论,那么,其他需要登记变动归属的数据等均不具备排他性,因为这些数据同样存在于网络,移转须登记机关参与。
三种数字货币的性质各不相同,也决定了其归属和侵权法保护的不同。就归属问题来看,实践中,三种数字货币的持币人均通常依赖交易平台的账号,那么在交易平台破产以后,是否能取回存在疑问。就侵权法保护问题来看,不论哪种数字货币均可能受到他人不法侵害。
1. 与现金货币相比,数字人民币是无体物,没有物理上的载体。但与比特币相比,数字人民币不存在去中心化设计,并且就目前的交易来看,没有采区块链技术。因此数字货币是以数据为基础的现金。我国学界有力说区分数据文件与数据信息,在数据文件上得成立所有权,因此,在云存储的情况下,如果提供云存储的公司破产,那么数据文件的所有人得行使取回权,取回数据文件。[70]在这个意义上,数字人民币的权利人对于数据文件享有所有权,而该数据文件的信息则是货币的金额,相比之下,传统现金货币的物权载体是纸张。目前,数字人民币存储于各商业银行提供的账户中,但是正如上文所述,持币人和银行之间并无债之关系,因此,数字人民币直接归属于用户。这就意味着,在商业银行破产时,持币人无须通过《商业银行法》第71条第2款通过存款优先权获得保护,而是直接根据破产取回权,取回数字人民币。
在认定数字人民币是数据为载体的现金货币以后,对其侵权法保护的问题也可以适用数据文件保护的规则。由于数据文件是绝对权,因此故意或过失侵害数据文件,均构成侵权。[71]
2. 在传统数字货币中,这一问题较为明确,持有数字货币人的用户与作为发行人的平台之间形成了债之关系,持币人是债权人。这就意味着,如果发行人破产,持币人只能作为一般债权人请求参与分配,而不能直接取回。此外,在是否受侵权法保护这一问题上,《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是我国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该条未区分权利与利益,进行一体保护。学界目前有力说认为,在《民法典》的解释论背景中,应当重视第1165条第1款提供的基础性评价框架进行整体衡量。[72]在此种见解下,债权固然不是绝对权,但是如果侵害行为的违法性极强或加害人故意的情况下才能构成第三人侵害债权。[73]司法实践中,仅有的侵害传统数字货币的案件均是以故意方式侵害其归属,[74]过失侵害传统虚拟货币的情况较为少见,也没必要通过侵权法保护。例如,在“李攀登、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被告腾讯公司以原告使用外挂为由,冻结了原告的游戏账户,其中涉及相关虚拟货币。法院在审理腾讯公司是否有权冻结账户时,其裁判依据是双方的服务合同。[75]由此可见,将虚拟货币定义为债权,通常情况下,通过合同法保护,在例外情况下,通过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保护已经足够。[76]
3.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则有所不同,其归属和保护问题有待明确。与日本MTGOX株式会社破产案反映的情况类似,我国实践中,大量的比特币交易同样通过比特币交易平台进行。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冯某诉A公司合同纠纷案”中同样涉及比特币在用户与交易平台之间的归属问题。该案中,由于比特币分叉,比特币的持有人可以获得与其持有的比特币数额相对应的比特币现金,因此,被告交易平台发出公告,承诺将给予用户相应的比特币现金,原告之后发现其未能取得相应的比特币现金,遂起诉被告履行合同。海淀区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请,饶有趣味的是,法官在针对该案的说明中提到,比特币等虚拟财产不是物,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比特币上不成立物权,因此原告不得基于物权请求交付比特币现金,只能基于合同请求交付比特币现金。[77]此种理由与前述日本MTGOX株式会社破产案中,东京地方法院的观点是类似的,只是我国法院没有进一步否定比特币的排他性,而是以物权法定为由,否定了原告享有物权性请求权。
上述中日两个案件中否定原告有物权性请求权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从该说明来看,法院否定原告原物返还请求权的理由在于比特币本身的性质,由于比特币不是物,故而无法适用原物返还请求权。正如上文所述,比特币固然不属于物权,但仍为“其他财产权”,同样存在绝对权意义上的归属问题。因此,单纯从比特币的性质出发,否定原告的诉请存在疑问。
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实质是受他人认可、并可移转给他人的持有单位数,而持币人通过公钥和私钥控制数字货币,其中,私钥起到加密移转比特币的功能,因此,私钥也是取得比特币权利的关键所在。就目前比特币交易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关系来看,用户为了交易比特币,会在交易平台开设账户,之后的交易在平台上进行,此种情况下,即使用户账户里比特币,但没有实际掌握比特币的私钥,因此,仅对交易平台享有权利,需要在交易平台中进行交易,换言之,此种交易实际没有在比特币的区块链中进行,在比特币交易的区块链中,只有交易平台是唯一享有私钥,享有排他性权利的人。相反,只有在用户提币并拥有私钥以后,比特币才真正归属于用户。而在这之前,用户仅享有对平台的债权。[78]因此,不论是“冯某诉A公司合同纠纷案”还是日本MTGOX株式会社破产案,比特币均归属于交易平台。
按照本文观点,非法定数字货币是其他财产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受侵权法的保护。当然,在常见的侵害比特币案型中,由于行为高度违法性和过错程度极高,因此,即使认为比特币不构成权利,也足以构成侵权。例如,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比特币涉外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中,被告通过暴力殴打的方式,逼迫原告移转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此种情况下,被告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悖俗侵害他人,因此,必然构成侵权。此外,在通过暴力或非法拘禁手段侵害比特币的案件以外,更多的案件则是通过黑客技术获取比特币的私钥。我国刑法实务往往认定此种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79]尽管法院定罪的前提是否定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的财产属性,但是刑法上数据概念的较为宽泛,同样可以涵盖比特币等非法定数字货币。由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保护的是个别公民的利益,因此构成侵权法上的保护性法律,这就意味着侵权人的行为违法性极高。因此,构成犯罪的行为同时构成侵权行为。[80]在上述两种典型情形之外,比特币等作为其他财产权同样是一般过错侵权保护的客体。当然,由于比特币存于区块链,因此过失侵害他人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情况较为少见。根据新闻报道,出现过比特币的持有人将私钥记录在纸上,但该纸被清洁工过失毁损,进而无法进入比特币账户的情况。[81]由于私钥是控制比特币的唯一方式,因此,此种情况下有构成侵权的可能。此时需要考虑两点,其一,清洁工是否构成过失;其二,用户将私钥记录在纸张上,未加妥善保管,致使清洁工过失侵权,此时有与有过失适用的空间。
尽管从性质来看,只有法定数字货币是货币,非法定数字货币均不是货币,但正如上文所述,私法中货币规则不仅受到法偿性的影响,也受到了货币本身特性的影响。在交易中,如果当事人以非法定货币结算或者以法定货币购买非法定货币时,两种非法定数字货币不论性质为何,但对于当事人而言,同种类的非法定货币之间是没有区别的,例如,不同的Q币之间的没有差异,均起到计价单位和支付手段等功能。因此,仍然需要考虑货币规则能否类推适用于非法定数字货币。此外,尽管数字人民币属于抽像货币,但是由于其载体特殊,因此在适用货币规则时是否存在例外也需要进一步检讨。
我国学说普遍认可货币的物权法规则可以适用于数字人民币和非法定数字货币,[82]尤其是货币“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同样适用于数字货币。这一规则又可细分为四个方面,其一,通过代码控制和支配数字货币的,即是数字货币的所有权人。其二,数字货币的返还请求权是债权性的价值返还请求权,而非原物返还请求权。其三,数字货币不能设立质权。其四,数字货币不适用执行异议。[83]
以上观点是存在疑问的。货币占有即所有的规则本身就存在争议。我国新近学说已经明确了货币占有即所有是对货币混合规则的简略说法,这一规则起源于德国,但被日本法误解,成为了我国目前的通说。[84]事实上,与我国通说认为的不同,作为该规则来源的德国法,在货币被他人取得以后的返还问题上,并非绝对采混合后的债权性返还。第一,不论是现金货币还是存款货币,适用占有即所有的前提是发生混合,无法识别个体性。在一张100元的纸币和两张50元的纸币放在一起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识别个体性,因此不发生混合。[85]此种情况下,100元纸币的所有权人可以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但是基于交易观念和诚实信用原则,返还义务人可以通过代物清偿,返还2张50元的纸币给100元的所有权人。在没有特殊返还利益的情况下,100元的所有权人不得拒绝受领。[86]第二,在混合以后,学界的通行观点认为,应当由主物的所有权人取得单独所有权,例如,在100块现金与收款机中的其他现金混合时,由收款机的所有权人取得单独所有权。[87]但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原则上由双方共有。[88]在共有以后,目前的德国法通说的观点认为,如果混合导致共有所有权的观点不加变动,直接适用于货币,那么会导致与生活利益和生活观念相矛盾的观点。例如甲放了4枚硬币在乙的收银柜里,该收银柜里已经有10枚硬币。如果按照混合的观点,则甲和乙共有14枚硬币,必须进行分割,否则任何一方无法单独处分。混合的观点造成了利益状况失衡,没有必要如此复杂。甲应当享有“分割权(Sonderungsrecht)”,无须乙的同意就可以取得4枚硬币。因为在现金这种可替代物的情况下,现金的价值和单个现金的本身的同一性无关。[89]由此可见,即使是在现金的情况下,占有即所有的观点也不成立。货币是否混合,须考虑是否丧失个体性,混合以后,也应当赋予占有货币的一方,单方的分割权。
在明确了“占有即所有”规则的本质是混合规则以后,判断其能否(类推)适用于数字货币,关键在于判断数字货币是否会因混合而丧失所有权,是否丧失个体性。在不同类型的数字货币中,判断标准不同。数字人民币作为无体物,其交易通过数据交换进行。因此,在交易中,具备可追踪性。[90]这就意味着,与现金相比,数字人民币不会丧失个体性,不存在混合的可能。假设甲与乙订立买卖合同,并以数字人民币支付。随后该合同无效,那么在物权变动采有因性的前提下,甲作为数字人民币的所有权人,可以主张原物返还。但与现金返还的情况相同,数字货币的所有权人如果对于数字货币的返还没有特殊利益,那么返还义务人可以给付其他货币。例如在上述返还的情况下,乙可以向甲原物返还数字人民币,也可以通过给付现金,或者转账支付记账货币的方式,进行代物清偿。此外,由于数字人民币的具备可追踪的性质,因此在其上也可以设定质权,数字人民币的所有权人也可以提出执行异议。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数字人民币不会因混合而消灭所有权,因此,在交易中,需要适用善意取得。[91]
上述观点在Q币等传统非法定数字货币中同样类推适用,其利益状况类似于存款货币的混合,是债权与债权的混合。[92]有争议的是,比特币等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法定数字货币是否必然会因混合而丧失绝对权。比特币本质上是“受他人认可的可交易的单位数”,有观点基于其技术特征,认为比特币必然适用占有即所有,因为一旦比特币转账进入他人账户以后,区块链的其他用户达成了受让人取得该单位数新的合意,此种合意不能撤销。[93]技术上的不能,并不意味着法律评价上的不能。即使是存款货币的转账交易中,如果发生原物返还,也很少通过撤销原交易进行。关键在于,是否赋予原权利人可以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性返还请求权。这一点不全然是技术问题。例如在上述案例中,甲与乙订立买卖合同,并以比特币支付,支付以后买卖合同无效,甲对于享有物权性返还请求权,那么在乙的其他债权人扣押其比特币账户时,法院应当认可甲可以提出执行异议,并要求乙提供给相应的比特币私钥。
数字人民币由于其法偿性,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货币之债的规则。相反,非法定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货币的功能,也具备货币的部分特征,因此需要考虑在个案中讨论能否类推适用。首先作为前提的问题是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购买非法定数字货币或者以非法定数字货币阶段的合同效力。
1. 购买非法定数字货币或以非法定数字货币结算的合同效力
与法定数字货币不同,《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第1条第2款否定了非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与货币相同的地位。已经失效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第1项则明确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除购买发行人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以外,不得用于支付、购买实物或者兑换其它单位的产品和服务。因此,在判断货币规范能否适用于非法定数字货币时,必须先考虑当事人购买非法定虚拟货币或者以非法定虚拟货币购买其他产品的合同效力。
我国司法实践为了扩大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流通,在将其定性为“虚拟商品”的基础上,认为《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禁止的是以非法定数字货币购买其他产品,而不禁止以人民币购买非法定数字货币。[94]此种论证更多是一种形式论证。从《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的前言和第1条第1款明确表明,该公告适用于代币发行融资、投机炒作的情况。投机炒作并非是严格的法技术概念,根据该公告第1条第2款结合第3条、第4条来看,其同样应当适用于以人民币购买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情形。不论是以人民币购买非法定数字货币,还是以非法定数字货币购买其他产品,当事人中的一方均负有提供非法定数字货币的给付义务,并且非法定货币均起到了计价单位的功能。在以非法定数字货币购买其他产品中,这点毋庸置疑,在以人民币购买非法定数字货币时,我国司法实践认为非法定数字货币是买卖的标的物,但相反也可以认为是以非法定数字货币作为计价单位,衡量人民币的价值。
对于合同效力的判断仍然要回到实质的判断理由。从规范性质来看,《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第1条和《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属于公法规范。在公法层面上,上述条文限制非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但如果当事人之间约定了以非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买卖合同(或者互易合同)的对价或者以人民币购买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合同,是否必然无效,则取决于该条是否属于《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第1句意义上的强制性规范。《九民纪要》第30条第2款认为,应当基于保护法益、违法行为的后果和交易安全保护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构成强制性规范。与《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第1条和《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类似,我国《外汇管理条例》第8条同样禁止外汇在我国境内作为货币流通。我国法院在认定以外币结算的合同效力时,呈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外币结算的条款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8条无效,因此当事人应当以人民币结算[9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汇管理条例》第8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法院对于当事人约定以外币结算的条款不予干涉。[96]两种观点均没有否认合同整体的效力,对于债权人而言,如果外币结算条款无效,其也能在获得相应比例的法定货币以后,自行兑换成外币。因此,对其利益状况影响不大。本文以为,从规范目的来看,上述规范均不应认定为效力性强制规范,其目的应当通过行政处罚或者刑罚方式实现,不应影响私法合同的效力。[97]
2. 货币之债规则的(类推)适用
(1)法定数字货币与非法定数字货币的共通问题
法定数字货币和非法定数字货币由于其特殊形式,因此在构成典型合同给付标的和履行迟延规则上有一定的共性。
一方面,货币之债是买卖合同的给付义务。数字人民币具备法偿性,是货币之债的给付客体。因此,以数字人民币购买其他产品同样构成买卖合同。相反,由于非法定货币在定性上,不属于货币,因此通说认为,如果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以非法定数字货币作为给付,构成互易,而非买卖。[98]应当适用《民法典》第595条、第647条,构成易货交易,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规定。少数说则认为,当事人可以约定法定货币的以外的外国货币作为买卖合同的价款,例如在欧洲,当事人也可以约定以美元作为买卖合同的价款,这不影响该合同被归为买卖合同。那么,如果当事人约定比特币作为买卖合同的价款同样不应影响合同定性。[99]当然,由于互易合同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规定,因此,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实质上的区别是存在疑问的。[100]二者可能的区别在于,如果认为是互易,那么交付非法定货币之债可能发生瑕疵,适用瑕疵担保的规定。但由于我国瑕疵担保是违约责任的一种形态,因此,没有必要细分是买卖合同还是互易合同。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数字人民币还是非法定数字货币,在构成合同标的时,均需考虑当事人是否选择了数字货币作为给付客体。在非法定数字货币构成给付客体时,需要当事人明确约定。相反,数字人民币虽然具备法偿性,但是由于数字货币的技术特点,数字人民币的交易需要借助智能手机,在便利性方面不如现金,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基于交易观念和交易习惯,可以通过补充解释的方式认定当事人以默示方式排除了数字人民币作为给付客体。[101]
另一方面,货币之债是赴偿之债,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作为货币的数字人民币,但交付非法定货币之债是否同样为赴偿之债。货币之债之所以是赴偿之债(或者至少是债务人负担在途灭失风险的寄送之债),是因为目前寄送金钱比去陌生的地方收取金钱容易,因此,法律在推定了当事人约定的是赴偿之债,由债务人承担在途风险。[102]此种价值判断在非法定货币的移转中同样成立,相较债权人,债务人更能控制其移转,因此,交付非法定货币的债同样是赴偿之债。
在明确了这一点以后,不论是何种数字货币的交易均依赖交易平台,因此在履行迟延方面具备共性。如果以现金为给付客体,那么在债权人终局性取得对金钱的支配(完成交付并移转所有权),才构成履行并移转风险。但是,就目前数字人民币所采的技术路径来看,尽管离线状况下,同样可以进行数字人民币交易,但是受领数字人民币的一方取得的数字人民币必须经过商业银行系统的确认,才能真正使用。[103]这就意味着,债权人取得数字货币后,如果一直处于离线状态,则无法使用,此种情况下,如果严格适用现金货币之债的规则,那么,货币之债并未履行完毕,债务人可能陷入履行迟延,这就导致债务人的负担过重。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更应当参考交付支票等进行支付时风险的移转。在货币之债中,债务人负有及时和按规定提供给付的义务。此种及时性与合规性不在于债务人必须将收款银行迟延记账的全部风险计算在内,而是仅在于根据通常状况,考虑到银行记账的时间,以及所选择的转账方式符合约定或所处的情势。[104]数字人民币的履行迟延问题同样应当适用这一点。在履行期届满之前,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数字货币即完成了给付,债权人是否及时联网向银行确认归属的风险不应当由债务人承担。这一点与支票方式清偿相同,债务人在履行届满前交付支票即履行完毕,是否及时承兑的风险由债权人负担。[105]此种考量同样适用于非法定数字货币,尤其是比特币,债务人承担非法定数字货币移转中灭失的风险,并且在给付时间上,考虑到到账的时间。因为只有非法定数字货币完全到达债权人的账户以后,才完成给付。
(2)非法定数字货币的特殊问题
在上述由于数字化带来的共通问题以外,由于非法定数字货币不是货币,因此也存在特殊性。
第一,如果当事人迟延交付非法定数字货币是否同样产生利息。我国目前的实践,基于非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性质不是货币,认为比特币之债即使迟延,也不产生利息。[106]迟延利息的规则也无法类推适用于非法定数字货币,这一点与外币之债不同,外币之债中,外币在其母国有利息规则,因此尚有类推的余地。但非法定数字货币并无利息规则。这一问题本质是迟延损害计算的问题,货币之债的迟延利息本质上是迟延支付造成的最低损害。[107]因此,即使否定了利息规则在非法定数字货币之债中的类推适用,债权人仍可以主张履行迟延造成的损害,最为典型的是因债务人迟延,非法定数字货币价格下跌的损害。
第二,最为关键的货币之债无履行不能的问题。货币之债无履行不能的前提是货币之债的本质在于“价值创造之债”,货币之债的债务人提供的不是特定的货币。具体而言,债务人须提供相应数额的货币,此种情况与给付物的情况是不同,在给付物的债中,物的种类与品质对于债权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但货币之债中,品质和种类对于当事人而言并无意义。那么,无法想象市面上所有流通的货币均灭失,这就不会出现客观不能的情况。而主观不能同样原则上不适用货币之债,因为债务人目前无资力不构成主观不能,只有债务人将来也无获得可能性时才构成主观不能。[108]此外,其他的债务在不能的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而货币之债无转化的必要,因为给付的标的物均为货币。
饶有趣味的是,针对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数字货币,我国学说认为,由于区块链技术问题,比特币之债无法返还,换言之,比特币之债必返还不能,因此,须转化为法定货币的返还之债。[109]据此,则比特币之债不适用货币之债无履行不能的规则。就技术而言,返还比特币之债确实难以返还。但比特币作为一种虚拟资产,其品质或种类对于当事人而言,无特殊意义。因此,以比特币为标的物的债务中,固然无法返还原来的比特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给付比特币的债务履行不能。重要的是比特币的数额,因此,债务人仍负有支付相同数额比特币的义务。此种比特币之债可等同外币之债,只要当事人约定的意义是为了取得比特币的价值。[110]因此,比特币之债与货币之债是类似的,原则上(类推)适用货币之债无履行不能的规则。一方面,比特币之债无客观不能,即使债务人所持有的比特币灭失,债务人仍能通过“挖矿”或者用法定货币购买的方式取得比特币。或有观点认为,比特币总量限定,因此存在全部灭失的可能性。[111]当然,此种情况下,通过解释也可以认为债务人得提供他种给付,因此比特币之债没有履行不能。另一方面,货币之债无主观不能的论证也可以适用于比特币之债。
值得思考的是,债务人是否得因履行费用过高,拒绝履行比特币之债,转而通过法定货币进行损害赔偿。在本国法定货币之债中不存在这一问题,相反,在外币之债或比特币之债中会存在当事人约定币种突然升值的问题。但是,履行费用过高抗辩的前提是,债务人的履行费用与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严重失衡,[112]在比特币升值中,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同样因比特币升值而提高,因此不存在失衡。[113]
相反,在非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法定货币之债中,由于其性质为对发行人的债权,因此更有可能发生履行不能。例如,发行人破产以后,所有的债权因清算而消灭,那么此种非法定数字货币客观不能。而持币人的账户也可能被发行人永久封禁,而陷入主观不能,也即其再也无法取得此种货币。
新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对现有法律体系和法律理论带来冲击,但是通过体系解释、类推适用等法教义学方法,可以将新技术带来的问题纳入到既有的法学体系之中,以维持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数字货币的私法适用同样如此。在充分认识和明确数字货币的技术特征与法律定性以后,法学家的工作是考虑关于货币的既有规则能否适用的问题。
第一,法定数字货币属于法定货币,性质上类似现金货币。但其特殊性在于数字人民币的载体是无体的数据,持币人对于数据文件享有所有权。因此,货币规范在适用时,需要考虑其载体的特殊性。“占有即所有”的规则在适用于数字人民币,需要考虑到数字人民币具备可追踪性,因此,所有权人不会因混合而丧失所有权。在货币之债规则适用时,同样应当考虑到数字化技术的影响,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对当事人合意的解释,排除以数字人民币作为货币之债的客体。并且在履行迟延等方面,考虑到技术迟延的影响。
第二,对于非法定数字货币而言,根据是否采区块链技术的不同,应当区分两类不同的非法定数字货币,非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法定数字货币是对发行人的债权,而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非法定数字货币是持币人享有的受他人认可的绝对性财产权。两种非法定数字货币在交易中均起到货币的部分功能,而且本身也具备货币的部分特征,因此需要考虑货币规范的类推适用。一方面,货币的物权法规则“占有即所有”规则适用的前提是货币之间混合,这同样可能发生于非法定货币;另一方面,货币之债在类推适用时,非法定货币之债同样具备价值创造之债的特点,例如货币之债无履行不能的规则可以类推适用于给付比特币之债。
注释:
[1]我国案件参见“北京海淀法院发布8个涉互联网商事典型案例之八:冯某诉A公司合同纠纷案”,法宝引证码CLI.C.74261012;外国案件如日本MTGOX株式会社破产案,東京地方裁判所平成26年(ワ)第33320号平成27年8月5日民事第28部判決。
[2]参见“陈某诉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北大法宝引证码CLI.C.84175716(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两周年十大影响力案件之三)。
[3]Vgl. Beck/König, Bitcoins als Gegenstand von sekundären Leistungspflichten,AcP 215 (2015), 655, 658.
[4]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85页;杨晓晨、张明:《比特币:运行原理、典型特征与前景展望》,《金融评论》2014年第1期,第43页。
[5]Vgl. Beck/König, Bitcoins als Gegenstand von sekundären Leistungspflichten,AcP 215 (2015), 655, 658.
[6]Vgl. Beck/König, Bitcoins als Gegenstand von sekundären Leistungspflichten,AcP 215 (2015), 655, 658.
[7]参见杨晓晨、张明:《比特币:运行原理、典型特征与前景展望》,《金融评论》2014年第1期,第40页。
[8]参见杨晓晨、张明:《比特币:运行原理、典型特征与前景展望》,《金融评论》2014年第1期,第41页、第42页。
[9]高航、俞学劢、王毛路:《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电子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245页、第246页。
[10]道垣内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担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内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会の発展と民法学上巻』(成文堂、2019年)493頁参照。(该文的一部分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参见道垣内弘人:《比特币的法律性质与交易所破产取回权的成立与否》,刘慧明译,渠涛主编:《中日民商法研究(第16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页-第159页。)
[11]Vgl. 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 AcP 218(2018), 385, 403.
[12]该部门规章已于2019年6月28日废止。
[13]李炳:《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共识与展望》,《金融理论与实践》2018 年第12期,第104页。
[14]参见柯达:《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4期,第58页。
[15] 2019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于数字人民币“会坚持中心化管理,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术路线,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选优,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参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70zn/fbh2/zbsl.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8月30日。
[16]杨晓晨、张明:《Libra:概念原理、潜在影响及其与中国版数字货币的比较》,《金融评论》2019年第4期,第65页。
[17]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92页以下;赵天书:《比特币法律属性探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84页。
[18]参见赵磊:《论比特币的法律属性》,《法学》2018年第4期,第160页。
[19]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96页-第98页;
[20]参见赵磊:《论比特币的法律属性》,《法学》2018年第4期,第160页。
[21]参见赵天书:《比特币法律属性探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88页。
[22]参见“金晨与北京火币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3民终3461号。类似观点也参见“张琳琳与李彦钰民间借贷纠纷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陕01民终9832号。“济南凯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孙呈昊买卖合同纠纷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10232号。
[23]参见“陈某诉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北大法宝引证码CLI.C.84175716(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两周年十大影响力案件之三)。
[24]参见“冯某诉A公司合同纠纷案”,北大法宝引证码CLI.C.74261012(北京海淀法院发布8个涉互联网商事典型案例之八)。
[25]参见“李建锋与北京葡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7176号。
[26]参见“北京乐酷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绥化市华辰商贸有限公司,彭泉泉侵权责任纠纷一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黑民终274号。
[27]该案涉及以悖俗侵权方式获取比特币,根据中国法院网对案情的介绍,被告甲乙丙丁通过殴打等暴力方式,从原告处取得了比特币。参见“闫向东等与李圣艳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3689号。
[28]Vgl. MüKoBGB/Grundmann, 8. Aufl. 2019, BGB § 245Rn. 10.
[29]参见朱晓喆:《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7页。
[30]Vgl. Sebastian Omlor, Geldprivatrecht, Mohr Siebeck, 2014, S. 117.
[31]参见朱晓喆:《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7页;孙鹏:《金钱“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权利流转规则之重塑》,《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26-28页。
[32]Vgl. Staudinger/Omlor (2016) Vorbemerkungen zu §§ 244–248, A66-A68.
[33] Vgl. Staudinger/Omlor (2016)Vorbemerkungen zu §§ 244–248, A62-A87.
[34]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6版,第208页、第209页;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版,第481页、第482页。
[35]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6版,第208页。
[36]参见朱晓喆:《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8-119页。
[37]参见孙鹏:《金钱“占有即所有”原理批判及权利流转规则之重塑》,《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33页。
[38]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39]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4版,第353页。
[40]Vgl. Heermann, Geld und Geldgeschäfte, Mohr Siebeck, 2003, S. 44.
[41]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42]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版,第579页。
[43]参见王洪亮:《债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页。
[44]Vgl. Heermann, Geld und Geldgeschäfte, Mohr Siebeck, 2003, S. 24.
[45] Vgl. D. Medicus, „Geld muss man haben“,AcP 188 (1988), 489, 490. 梅迪库斯借助破产法的规定论证了债务人无资力(主观不能)不影响货币之债的效力。根据原《德国破产法》第164条第1款(目前《德国支付不能法》第201条)规定,在常规清偿程序终结以后,如果债权未获满足,那么债权人仍可向债务人主张。由此可见,债务人主观不能,不构成履行不能。Vgl. D. Medicus, „Geld muss man haben“,AcP 188 (1988), 489, 491 f.
[46]Vgl. Tonner/Krügger, Bankrecht, Nomos, 2020, S. 160 f.
[47] A. Spiegel, Blockchain-basiertes virtuellesGeld, Mohr Siebeck, 2020, S. 46.
[48]基于非法定数字货币欠缺法偿性,其流通性也尚未被交易现实广泛接受,实质问题应当货币之债的(类推)适用等理由,否定非法定数字货币(尤其是比特币)的货币定性的,参见[德]塞巴斯蒂安·欧姆勒:《德国法与欧盟法下的金钱、货币数字化》,张佳丽译,《私法研究》2018年第1期,第237页。
[49]例如,在“周丽君与中金国际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翁家乐合同纠纷案”中,原告购买的数字货币是由被告交易平台发行的、由其他用户持有的数字货币。参见“周丽君与中金国际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翁家乐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9)浙0212民初12175号。
[50]参见梅夏英:《信息和数据概念区分的法律意义》,《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157页。
[51]在上述“周丽君与中金国际投资控股(深圳)有限公司、翁家乐合同纠纷案”中,原告指出由于监管部门关闭交易平台,原告所有的CNYH平台币失去了价值。由此可见,数字货币的价值源自于发行人的允诺。
[52]针对有发行人的电子货币(E-Geld),德国法通说认为其为债权。Vgl. MüKoBGB/Casper, 8. Aufl. 2020, BGB §675c Rn. 30. 此种观点同样适用于有发行人的非法定数字货币。
[53]Vgl. Wieling, Sachenrecht. 5. Aufl., Springer, 2007, S. 24.
[54]Vgl. Beck/König, Bitcoin: Der Versuch einer vertragstypologischenEinordnung von kryptographischem Geld, JZ 2015, 130, 131.
[55]对于此种观点的评述也参见加毛明「仮想通貨の私法上の法的性質―ビットコインのプログラム・コードとその法的評価」金融法務研究会『仮想通貨に関する私法上・監督法上の諸問題の検討』https://www.zenginkyo.or.jp/fileadmin/res/news/news310339.pdf(2019)17頁。
[56]加毛明「仮想通貨の私法上の法的性質―ビットコインのプログラム・コードとその法的評価」金融法務研究会『仮想通貨に関する私法上・監督法上の諸問題の検討』https://www.zenginkyo.or.jp/fileadmin/res/news/news310339.pdf(2019)17頁。
[57] Vgl. Beck/König, Bitcoin: Der Versucheiner vertragstypologischen Einordnung von kryptographischem Geld, JZ 2015,130, 130 f.
[58]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6版,第8页。
[59]Vgl. Spindler/Bille, Rechtsprobleme von Bitcoins als virtuelle Währung, WM2014, 1357, 1359.
[60]此种观点的介绍参见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 AcP218(2018), 385, 406.
[61]Vgl. BeckOGK/Köndgen, 15.6.2020, BGB § 675c Rn. 132 ff.
[62]Vgl. Neu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2. Aufl., C. H.Beck, 2020, S. 238 f.
[63]Vgl. Spindler/Bille, Rechtsprobleme von Bitcoins als virtuelle Währung, WM2014, 1357, 1360.
[64]同样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91页。
[65]道垣内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担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内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会の発展と民法学上巻』(成文堂、2019年)494頁。
[66]道垣内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担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内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会の発展と民法学上巻』(成文堂、2019年)495頁。
[67]道垣内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担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内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会の発展と民法学上巻』(成文堂、2019年)494頁;Spindler/Bille,Rechtsprobleme von Bitcoins als virtuelle Währung, WM 2014, 1357, 1360; Langenbucher,Digitales Finanzwesen, AcP 218(2018), 385, 407.
[68]東京地方裁判所平成26年(ワ)第33320号平成27年8月5日民事第28部判決参照。对于该案的介绍,参见罗勇:《论数字货币的私法性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54页-第155页;赵磊:《数字货币的私法意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15页-第117页。
[69]例如,加毛明采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权利说,加毛明「仮想通貨の私法上の法的性質―ビットコインのプログラム・コードとその法的評価」金融法務研究会『仮想通貨に関する私法上・監督法上の諸問題の検討』https://www.zenginkyo.or.jp/fileadmin/res/news/news310339.pdf(2019)24頁参照。道垣内弘人同样采合意为基础的财产权说,道垣内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担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内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会の発展と民法学上巻』(成文堂、2019年)494、495頁参照。
[70]参见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位与保护》,《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83页-第90页。
[71]参见纪海龙:《数据的私法定位与保护》,《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84页。
[72]参见叶金强:《<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的展开路径》,《法学》2020年第9期,第33页。
[73]相同观点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3版,第179页。
[74]例如,在“齐心月与苏雨彤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中,被告盗刷了原告QQ内的Q币。参见“齐心月与苏雨彤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山东省济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鲁0891民初1407号。
[75]参见“李攀登、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终11815号。
[76]相反,梅夏英则认为通过合同不足以保护虚拟财产,其理由有二,其一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关系如果免费合同关系,则很难成为民法上的合同关系,拘束力程度不明;其二,通过合同关系只能解决合同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无法解决第三人侵害的情况。参见梅夏英:《虚拟财产的范畴界定和民法保护模式》,《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45页。
[77]参见“冯某诉A公司合同纠纷案”,北大法宝引证码CLI.C.74261012(北京海淀法院发布8个涉互联网商事典型案例之八)。
[78]道垣内弘人「仮想通貨の法的性質――担保物としての適格性」道垣内弘人ほか編『近江幸治先生古稀記念社会の発展と民法学上巻』(成文堂、2019年)496頁参照。
[79]例如参见“许武浩、朴敏哲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3刑终1204号;“孟陈林、刘铸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3刑终1117号。
[80]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这可能会使得民法的保护依赖于刑法的价值,而二者不一定总是并行不悖的。Vgl. 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AcP 218(2018), 385, 408.
[81]“对不起,弄丢了私钥,只能怪你没有拥有比特币的这个命”,https://www.sohu.com/a/297594216_99978892 2021年1月5日最后访问。
[82]参见柯达:《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4期,第60页;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01页。
[83]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01-102页。
[84]参见朱晓喆:《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8-119页。
[85]Vgl. MüKoInsO/Ganter, 4. Aufl. 2019, InsO § 47 Rn. 19, 19a.
[86]Vgl. Sebastian Omlor, Geldprivatrecht, Mohr Siebeck, 2014, S. 149.
[87]Nur vgl. Medicus, Ansprüch auf Geld, Jus 1983, 897, 899.
[88]Vgl. MüKoBGB/Füller, 8. Aufl. 2020, BGB § 948 Rn. 7;
[89]此种观点源自黑克(Heck),Vgl. Heck, Grundriß des Sachenrechts, 3Aufl.,1930, Scientia Verlag Aaalen, 1994, S. 260 f. 随后成为了德国的绝对通说,vgl. Palandt/Herrler, 79. Aufl. 2020, BGB § 948,Rn. 3. 对于黑克观点的质疑,vgl. Brehm/Berger, Sachenrecht, 3. Aufl.,Mohr Siebeck, 2014 S. 459. 其认为黑克举的例子不具普遍性。因此仍然应当坚持所有的共有人达成合意后分割的观点。
[90]参见何德旭、姚博:《人民币数字货币法定化的实践、影响及对策建议》,《金融评论》2019年第5期,第46页。
[91]《德国民法典》第935条第2款规定善意取得同样适用于货币遗失物与盗赃物的情况,进一步强化了善意取得在货币中的运用,以保护交易安全。Vgl. MüKoBGB/Oechsler, 8. Aufl. 2020, BGB § 935 Rn. 14.
[92]关于存款货币的返还应当如何评价,参见朱晓喆:《存款货币的权利归属与返还请求权》,《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134-135页。
[93]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01-102页。
[94]参见“陈某诉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北大法宝引证码CLI.C.84175716(杭州互联网法院成立两周年十大影响力案件之三)。
[95]例如参见“霸州市新思钢木家具有限公司诉东莞朗顺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定作合同纠纷案”,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2008)霸民初字第215号。
[96]例如参见“北京蓝狮金桥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17307号。
[97]此种观点也受到我国仲裁实践的支持,深圳国际仲裁院2018年公布的比特币仲裁案中,当事人之间订立以比特币理财协议,但随后理财受托人不愿返还比特币,并主张比特币理财合同无效。仲裁庭针对这一点认为,“并无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当事人持有比特币或者私人间进行比特币交易,而是提醒社会公众注意有关投资风险。”深圳国际仲裁院归纳的裁判要点同样提及,“私人间订立的比特币归还契约并未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应认定为无效。中国法律法规并未禁止私人持有及合法流转比特币。”参见“深国仲案例精选比特币仲裁案”,https://mp.weixin.qq.com/s/U_qDgQN9hceLBbpQ13eEdQ2021年1月2日最后访问。当然,这一仲裁案件最终被我国法院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而撤销。
[98]Vgl. Spindler/Bille, Rechtsprobleme von Bitcoins als virtuelle Währung, WM2014, 1357, 1362; Erman/Grunewald, 15. Aufl. 2017, § 480 BGB Rn. 1.
[99]Vgl. Beck/König, Bitcoin: Der Versuch einer vertragstypologischenEinordnung von kryptographischem Geld, JZ 2015, 130, 137; 相同意见参见G. Wagner对Langenbucher提出的质疑,vgl. Hamann, Diskussionsbericht zum Referat vonKatja Langenbucher, AcP 218 (2018), 430, 432.
[100]同样指出这一点如Langenbucher, Digitales Finanzwesen, AcP218(2018), 385, 413.
[101]法定货币的法偿性是其公法属性,这并不影响在私法中,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支付法定货币。Vgl. Staudinger/Omlor (2016)Vorbemerkungen zu §§ 244–248, B81. 同样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如柯达:《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4期,第62-63页,但其混淆了货币的公法与私法属性。
[102] Vgl. P. Heck, Grundriß des Schuldrechts,Mohr, 1929, § 6,6, S. 24.
[103]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科学技术研究所:《使用数字货币芯片卡进行数字货币支付的方法和系统》,专利号:CN107230052A。
[104]Vgl. MüKoBGB/Krüger, 8. Aufl. 2019, BGB § 270 Rn. 18.
[105] MüKoBGB/Krüger, 8. Aufl. 2019, BGB § 270Rn. 20.
[106]参见“深国仲案例精选比特币仲裁案”,https://mp.weixin.qq.com/s/U_qDgQN9hceLBbpQ13eEdQ2021年1月2日最后访问
[107]Vgl. Jauernig/Stadler, 18. Aufl. 2021, BGB § 288 Rn. 2.
[108]Vgl. Lorenz Kähler, Zur Entmythisierung der Geldschuld, AcP 206(2006), 805,821f.
[109]当然,该说同样认为,应当允许债权人选择比特币之债抑或法定货币之债。参见杨延超:《论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02页。
[110]Vgl. Beck/König, Bitcoins als Gegenstand von sekundären Leistungspflichten,AcP 215 (2015), 655, 663 f.
[111]例如,Spiegel举的例子是所有的比特币均被挖出,且持币人均不愿出售。Vgl. A. Spiegel, Blockchain-basiertes virtuellesGeld, Mohr Siebeck, 2020, S. 80.
[112] Vgl. Looschelders, SchuldrechtAllgemeiner Teil, 16 Aufl., Vahlen, 2018, S. 167 f.
[113]Vgl. Beck/König, Bitcoins als Gegenstand von sekundären Leistungspflichten,AcP 215 (2015), 655, 673.
“民商辛说”栏目由辛正郁律师主笔/主持,我们希望借此搭建民商法律理论与实务完美衔接和自洽的平台。如您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点击文末留言。

向“民商辛说”栏目投稿,欢迎发送邮件至:
xinzhengyu@tiantong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