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凝,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后
目 次
一、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之裁判考量因素与学理依据
二、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真意并非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的正当理由
(一)当事人真意视角下的展开
(二)解除权约定的类型化:概括约定与具体约定
(三)实质违约理论的不足
三、体系评价一致性下的司法干预不能构成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的正当理由
(一)司法干预与体系评价一致性
(二)反驳意见:以违约金为例
四、诚实信用原则不足以一般性地限制轻微违约下的约定解除权
(一)诚实信用原则限制论
(二)对诚实信用原则限制论的反思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替代机制
五、结论
摘 要:《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47条确立了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的规则。司法实践在适用该规则时主要考量“是否补正履行”“义务违反程度”“因合同关系产生的既有投入”等因素。尽管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全面认可,比较法上亦不乏采纳类似立场者,但其正当性值得怀疑。以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真意不能证成该规则的合理性,至多只能作为概括约定与具体约定的区分依据;由于所涉利益状况的不同,违约金酌减等司法干预规则不足以从体系评价一致性上说明该规则具有合理性;诚实信用原则虽然构成对解除权行使的限制,但不能证成轻微违约下应当一般性地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当事人利益可能失衡的问题可以交由解除制度内外的一系列规则处理。该规则可能排斥当事人关于解除事项的特别安排并损害当事人对于法律关系确定性的信赖,因而会架空约定解除权的主要功能,《民法典》第562条未承认类似规则的做法应予肯定。
关键词:轻微违约;约定解除权;合同解释;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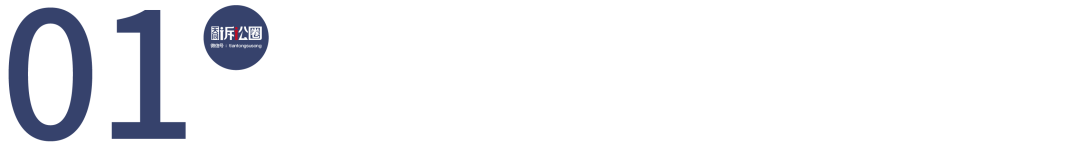
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之裁判考量因素与学理依据
《民法典》第56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依该款文义,约定解除权产生与否取决于约定事由是否发生,除此之外不再受限制。这一结论乍看之下颇为合理。毕竟约定解除权的基础在于当事人合意,出于对合同内容自由的尊重,法律自然不应再作限制。不过,当前述观点以合同自由为立论基础时,这也为对其进行限制埋下了伏笔。因为即使是最为强调意思自治的合同法,也并不承认完全不受限制的合同自由。
司法层面对约定解除权发生的限制首先体现为《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47条。根据该条,如果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的实现,即使约定的解除权发生条件成就,守约方也不能解除合同。与之类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第55条第1款也认为轻微违约下应限制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此外,部分裁判早在《九民纪要》之前便表达过类似观点。例如,在一起商标权纠纷案中,当事人约定一方逾期付款达一个月或累计达三个月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债务人于约定的一个月宽限期的两日后才支付费用。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债务人违约情节轻微,对债权人实现合同目的未产生实质性影响。“在约定解除的情形下,虽然解除事由可以由当事人自行约定,但在行使单方解除权时,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解除权。”[1]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否认案涉合同已被解除。
不过,在前《九民纪要》时代,也曾有裁判明确反对以违约程度轻微为由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例如,在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表示,上诉人基于自身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主张对方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的观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
为了更为全面地获知司法实践对于约定解除权应否受违约程度限制的见解,本文以《九民纪要》第47条中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以及四组替换表述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经筛选后共得到相关案例222件。[3]就所得案例而言,支持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可谓主流见解,严格而言,仅有3件明确反对这一立场。[4]在全部案件中,有200件直接援引《九民纪要》第47条进行说理或表达了类似观点(部分裁判于《九民纪要》公布前作出),在这些案件中仅有22件最终认为违约程度不符合《九民纪要》第47条的规定,[5]进而确认约定解除权发生。
而且,基于这些裁判可以发现,在《九民纪要》第47条“是否显著轻微”“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等抽象表述之下,司法实践对如何适用该条其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该共识在《九民纪要》公布之前的部分裁判中便有迹可循。具体而言,司法实践经常基于以下三项因素认定构成轻微违约,进而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1)是否补正履行。在所收集的案例中,有89件在裁判说理中明确提及这一点。根据这些案例,即使约定解除权的发生条件已经满足,只要债务人事后补正履行或有补正履行意愿便可排除约定解除权。(2)义务违反程度。在所收集的案例中,有54件(不包括可能考虑该因素但仅采用“违约程度轻微”等模糊表述的案例)明确指出这一点。就义务违反程度的判断而言,法院主要从尚未履行义务的比例、履行义务的迟延程度和不可修复的瑕疵程度三方面入手。此外,如果债务人并非故意违约,法院将更倾向于认定仅构成轻微违约,即便此种“事出有因”未必满足不具有可归责性的要求。[6](3)因合同关系产生的既有投入。在所收集的案例中,有32件明确以此为由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其中,提及此点的案件大多涉及长期合同,典型者如租赁合同(18件)。以租赁合同纠纷为例,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在于违约方在履约准备或先前的履行过程中已经就租赁物及其附属设施支出了相当数额的修缮和改建费用,而且合同往往还包括罚没约定,例如合同解除后违约方就租赁物已经投入的支出全部归守约方所有。[7]
以前述司法实践为基础,如果将视野进一步拓展至域外法不难发现,违约程度是否影响约定解除权发生是合同解除领域的重要问题。而且,虽然最终采纳的教义学路径和实质理由有所不同,但支持轻微违约下应当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无疑是域外合同法裁判和学理上的主流见解。[8]总结而言,域外合同法裁判和学理主要给出了以下三点理由。(1)轻微违约下允许解除合同违背当事人实质意义上的真实意思,在个案中应当结合案件事实的具体情况限制解除权人行使约定解除权。(2)基于体系评价的一致性,当解除权约定的内容过于严苛、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利时,法院应当准用或类推适用违约金酌减等规则,以司法干预的方式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3)轻微违约下允许解除合同将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还可能使合同当事人已经投入的成本落空,造成经济上的浪费,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但本文认为这三项理由均难以证成轻微违约下应当一般性地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下文将针对这三项理由逐一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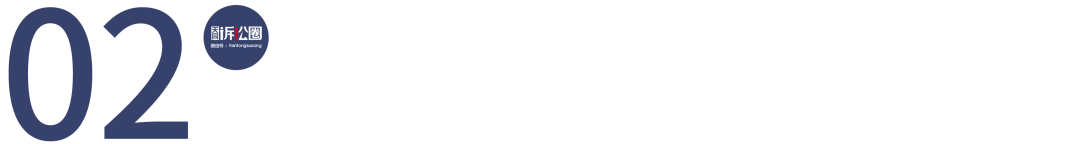
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真意并非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的正当理由
认为轻微违约下允许解除合同违背实质意义上当事人真意的观点主张,在涉及轻微违约的案件中,如果只依据解除权约定的文义确实应认为解除权发生,但从可能的当事人真意和交易实践的一般情况出发,此种恪守文义的解释结论不符合商业惯例。[9]尤其是在合同约定债务人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债权人均可解除合同时,考虑到合同关系的内容可能非常复杂,义务类型也较为丰富,很难想象当事人确实认为就某一义务存在轻微违约时对方即可解除合同。所以,基于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真意,有必要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对解除权约定进行限制性解释以排除轻微违约下的解除权。[10]
至于具体的限制方法,则需兼顾形式层面的解除权约定和实质层面的当事人真意。一方面,既然当事人有意在法定解除规则之外另行确立标准,便不宜认为仅在满足法定解除的标准(如根本违约)时方可产生约定解除权。另一方面,当事人的真意又要求排除轻微违约下的解除权,因此,在法定解除的标准之下仍然需要根据当事人的真意区分不同的违约程度。进而,一种可能的方案是解除权约定适用于中间程度的违约行为,亦即当违约程度介于轻微违约和根本违约之间时约定解除权发生。比较法上持此类见解的典型是英国法,在涉及约定解除权是否发生的案件中,部分裁判承认了所谓的“实质违约”(material breach)概念,[11]以区别于根本违约和轻微违约。[12]具体而言,实质违约意味着“违约程度高于轻微违约但未达到根本违约”。[13]与之类似,在我国也有裁判主张,约定解除权的行使应以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为条件。[14]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此种观点的立论依据,因为在个案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无疑是当事人真意,如果文义之外存在其他解释资源充分表明当事人有意排除轻微违约下的约定解除权,自然应依照当事人真意。然而,问题恰恰在于缺乏此类解释资源的情况。就此本文认为,既不能一般性地基于轻微违约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也不应引入所谓的实质违约理论。原因有两点:其一,前述观点所关注的问题应当通过对解除权约定进行类型化并相应地设置任意性规则予以解决,由此方能揭示当事人真意而非违约程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其二,以实质违约理论为代表的方案将架空约定解除权的主要功能,对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基于类型化的思考方式可以将解除权约定区分为概括约定与具体约定。概括约定包括两种:第一种是既未指明何种义务的违反亦未说明何种程度的违反可以解除;第二种是虽然指明具体义务的违反但未说明何种程度的违反可以解除。在实践中,前者通常表现为“一方违约即可解除”或“违反合同约定便可解除”等泛泛约定;后者例如“迟延付款即可解除”。与之相对,具体约定则指明对何种义务何种程度的违反足以引发解除权。典型者如有关金钱给付的约定,比如“迟延付款10日卖方可以解除合同”。对于概括约定,应当谨慎承认其效力,除非有证据表明当事人确实意欲如此,否则应认为该约定因为内容过于不确定而不具有拘束力。[15]相反,如果解除权约定具体、明确,原则上应当按照约定内容判断解除权是否发生。[16]
在实然层面上,此种区分所体现的思路不仅有比较法例予以印证,也为我国许多司法裁判所采纳。首先,对于轻微违约下的约定解除权限制,尽管英国法长期以来采肯定立场,但相关的重要先例所涉及的几乎均是概括约定。例如,在“The Antaios 案”中,当事人约定对租船合同的任何违反都将使出租人有权收回船只。[17]又如,在“Rice 案”中,当事人约定一方一旦违反合同项下的义务,另一方便享有解除权。[18]在这两起案件中,法院在解释解除权约定时均认为不能将违约理解为任何程度的违约,而应指根本违约。[19]在后续案件中有法官更是直言,将合同约定解释为任何程度的违约均引发解除权无异于公然违背商业常识。[20]
类似立场还可见于法国法。法国相关学理和实践认为,诸如“合同不履行就解除合同”等概括约定不过是法定解除权规则的简单重复,解除权人仍负有法定解除之下的催告等义务。[21]在法国债法改革的进程中,三部主要草案均要求合同中的解除条款指明不履行的债务范围。[22]虽然修改后的《法国民法典》第1225条在文义上虽略有区别,但法国学者认为,考虑到既往判例的立场,可以认为该条包含了前述意思。[23]
其次,就中国的司法实践而言,早在《九民纪要》之前便有法院在分析约定解除权时有意区分概括约定与具体约定。例如,针对“一方不履行合同,另一方可提出解除合同”的约定,有法院认为,当事人虽然约定了解除权但不够具体、明确,“所谓‘一方不履行合同’系指当事人‘不完全履行合同’,还系‘完全不履行合同’,约定不明”。最终,该法院认为应当将“一方不履行合同”解释为“完全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致另一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24]在《九民纪要》之后亦有判决持类似观点。例如,在一起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约定双方均可由于对方未履行合同义务而终止合同,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此种表述“没有明确写明‘未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违约情形”,该解除条款系约定不明,最终否认合同已被解除。[25]
而在应然层面上,此种区分的正当性恰恰在于规范意义上的当事人真意。相较于约定具体、明确的情况,约定的内容越模糊,越能说明当事人对相关解除事项缺乏特别安排的意思。此时也就无需担心约定解除权的制度功能被架空,因为这对当事人而言本就无足轻重。所以,在概括约定之下,债权人仅在债务人的违约程度满足法定解除权的发生条件时才可解除合同。[26]换言之,当事人之间实质上相当于没有解除权约定。[27]
在明确了解除权约定的类型化才是问题的关键之后,还有必要从约定解除权的制度功能出发,回应实质违约理论提出的挑战。通常认为,约定解除相较于法定解除具有两项特别功能。一是法定解除事由的范围有限,未必契合具体交易当事人的意愿,约定解除允许当事人自行确立解除权的发生事由和法律效果,从而对法定解除进行修正、缓和与补充。[28]二是明确解除权是否发生,避免如法定解除一般受到“根本违约”“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等不确定概念的影响,从而降低守约方证明自身享有解除权的难度,提升法律关系和交易的确定性。[29]循此,实质违约理论的最大问题便在于架空约定解除权的这两项特别功能。
首先,就变更法定解除规则而言,如果承认实质违约理论,在个案中虽然当事人特别看重但在一般交易观念中无足轻重的事项或者违反后结果轻微的事项将不再具有规范意义。在微观视角下,此种限制无疑挫败了个别交易中的当事人意愿;而在相对宏观的视角下,将导致当事人不得不采取替代措施迂回实现约定解除本可实现的功能,增加整体的市场交易成本(挫折成本[30]上升)。就此,实质违约理论始终需要从根源上回应当事人关于轻微违约的特别安排为何无法在法律上得到承认,而是需要以所谓实质违约作为扣减基准的问题。
其次,就明确解除权是否发生和追求法律关系确定性这一目的而言,考虑到法定解除中的根本违约本就是含义极不确定的概念,以其为参考系创设的实质违约在不确定性上恐怕只增不减。而且,根本违约严格来说是一个“半开放区间”,在具体判断时只需要考虑“根本性”这一标准,在标准以上即构成根本违约,反之则不构成。相比之下,实质违约则是“两端封闭区间”,在具体判断时需要同时考虑根本违约和轻微违约的判断标准,司法实践就此无疑更难形成统一认识。在财货流通迅速、交易机会转瞬即逝的现代商业社会,当事人就自身能否脱离原合同拘束、同潜在的其他交易对象进行磋商等事项,无疑期待获得清晰、明确的预期。采纳实质违约理论将使当事人不得不设计更为复杂的解除权约定条款以规避司法介入,甚至可能导致其一般性地丧失约定解除的动力。[31]
实质违约的判断困难从英国司法实践对此概念的界定也可见一斑。在有关该问题的两则重要先例上,克拉克法官(Clarke J)表示,在判断任何违约行为的实质程度时都应当同时考虑违约行为的构成和产生背景。[32]杰克逊法官(Jackson LJ)则界定道,想要构成实质违约,违约程度必须足够严重,而不能是无关紧要的。[33]问题在于这些因素同样是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参考因素。鉴于两者在判断思路上相似且各自的判断标准均较为模糊,区分实质违约和根本违约恐怕颇为困难。所以,相较于认可形式上不同于根本违约但实质上难以区分的实质违约,倒不如直接根据前述类型化方案分别适用不同规则。由此,法院可以在处理概括约定时参考既有关于根本违约的研究,也能够“倒逼”真正想要另立解除权发生标准的当事人明确解除权的发生条件,从而降低司法成本。[34]
综上,以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真意并不能证成轻微违约下应当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其至多只能说明概括的解除权约定为何应受限制。当然,在运用前述“概括约定—具体约定”的二分法限缩约定效力时需要特别谨慎。如果当事人关于合同解除存在明确约定,原则上应该严格按照约定文义理解。例如,在当事人约定“逾期超过6个月未能支付”解除权即发生时,认为该表述指的是连续6个月未支付任何款项无疑不妥。[35]否则按照此种理解,债务人每隔6个月支付部分收益款(无论支付比例如何)即可规避解除权约定,这显然违反了相关表述的通常含义以及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正常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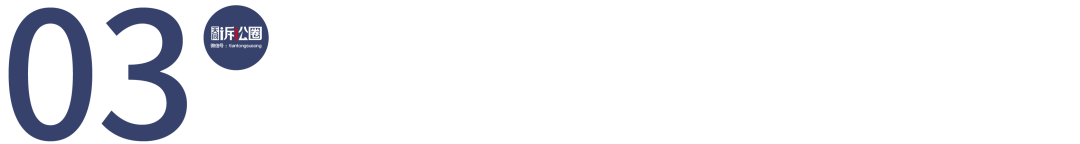
体系评价一致性下的司法干预不能构成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的正当理由
与前一种观点强调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真意不同,第二种限制理由虽然也围绕当事人意思展开,但立论基础在于通过司法干预当事人意思。换言之,该观点承认当事人通过解除权约定表达了轻微违约下亦可解除的意思,但同时认为鉴于违约金酌减等既有规则表达的价值立场,基于体系评价一致性,应当通过司法控制限制轻微违约下的约定解除权发生。
详言之,正如解除权约定反映了当事人关于合同解除这一法定救济方式的特别安排,违约金也是当事人在法定损害赔偿规则之外达成的特别约定。在违约金过分高于损失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减少。那么,在约定的解除权发生事由过于轻微、明显偏离法定解除权的标准时,法院为何不能依请求对解除权约定进行限制?例如,在当事人约定迟延付款一日卖方可以解除合同时,如果该约定有违行业交易惯例,法院能否类推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在约定的基础上再行宽限几日?
在比较法上亦可寻得此类观点。法国学界针对这一问题的主导性意见便是参照违约金规则承认法官对解除权约定也享有调节权力,但在实证法层面,法国法就此问题仅规定了一些特别法以限制解除权。相比之下,与学界观点更为接近的则是司法,后者长期以来均以解除权约定的解释为名实质上行使裁量权,以审查当事人是否善意运用解除权约定。[36]
本文对上述观点的回应是,解除权约定与以违约金为代表的约定所涉及的利益格局存在差异。既然“实质有别”,自然无需“评价一致”。以违约金为例,首先,尽管违约金和合同解除同属广义的合同救济手段,但两者的功能差异明显。前者旨在填补守约方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损害,后者则意在赋予当事人脱离合同关系的机会。相应地,违约金酌减关注的是守约方在因违约行为受损后最终可以获得何种程度的金钱给付以填补损失。法院是否酌减只可能影响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具体数额,而不会影响债权债务关系的性质以及是否发生。与之相异,解除权发生与否则直接决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未来是否可能发生性质上的变化。而且在中国法上,解除的法律效果原则上包括返还已经履行的部分和免除尚未履行的义务,其不仅影响当事人之间已经履行部分的最终归属,还左右着行使解除权一方未来的经济计划。
对于意图解除合同的一方而言,倘若其对于是否享有解除权这一事项理解有误,进而错误地行使了解除权,此时无论是解除合同的表示,还是后续因认为合同已经解除而拒绝履行自身义务,都可能构成对方主张违约责任甚至解除合同的基础。[37]所以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的解除权约定(尤其是涉及期限的约定)常常采取相当刚性的表述。相比之下,违约金酌减则不会对守约方产生此种潜在的不利影响,守约方即使对法院的酌减权力理解有误亦不影响其法律地位。相较于违约金酌减,当事人对于解除权是否发生有着更高的确定性需求,而满足此种需求的最佳路径是原则上尊重当事人关于解除权的具体约定。
其次,在正当性上,违约金酌减及类似规则共同反映了合同法上限制合同自由的一种重要机制,即基于实质正义限制合同自由。[38]既有研究也强调,违约金酌减规则是在意思自治、形式自由的基础上协调实质正义、个案公平的一种法技术。[39]但是,解除合同本身不会给债务人带来额外给付,债务人仅需返还已经受领的给付,在结果上难言不公。[40]至于因为合同解除而附带产生的不利益,例如合同存在罚没约定的情况,则如后文所述,可以通过解除制度内外的一系列规则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会造成实质结果层面的显著不公。所以,就基于利益平衡限制意思自治的必要性这一点而言,违约金酌减与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亦难以相提并论。
最后,体系评价一致性还可能成为反对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的有力理由。如果认可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此种价值判断还应贯彻至其他规则上。例如,《民法典》第481条第1款规定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假设承诺期限为某日中午12时之前,而承诺到达时间为该日中午12时5分,合同是否成立?承诺的迟延到达未必均可归责于承诺人,而可能系传递人传递迟延所致。此时,尽管《民法典》第487条给予承诺人区别于迟延承诺的特别保护,但合同最终能否订立仍然取决于要约人,一如约定解除之下是否维持合同关系取决于守约方。如果认为应严格按照承诺期限作出判断,则难以解释此时为何不鼓励交易,毕竟承诺人仅仅轻微逾期。甚至在传递迟延时,承诺人基于并未迟延发出的预设还可能已经开始了合同履行的准备工作。问题在于如果这些直接涉及当事人之间是否产生法律关系的明确约定均需要基于所谓的实质公平扩张出“缓冲范围”,有关交易的各种特别安排和由此产生的交易信赖将在很大程度上落空。更进一步而言,各种旨在确定法律关系的法定规则,如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等,应否作类似处理?
类推的基础在于“肯定的平等原则”,即“同样事物,同样处理”。[41]但上述分析表明违约金酌减与轻微违约下应否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实则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无论是以《民法典》第585条第2款进行个别类推还是以该款的规范目的进行整体类推均缺乏基础。所以,体系评价一致性下的司法干预不能构成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的正当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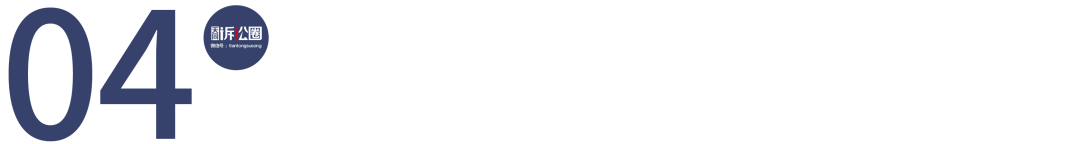
诚实信用原则不足以一般性地限制轻微违约下的约定解除权
(一)诚实信用原则限制论
支持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的第三项理由认为,违约方轻微违约即允许守约方行使约定解除权,容易导致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违约方因为轻微违约便丧失合同履行对应的全部利益甚至由此负担较重的赔偿义务,因履行而支出的成本也将落空,在整体层面上将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也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理念,有违诚实信用原则。[42]《九民纪要》第47条也强调须“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
在比较法上,以诚实信用原则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是相当主流的做法。在示范法层面,欧洲《共同参考框架草案》(DCFR)第 III-1:103条第1款便规定解除合同须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交易的要求。在内国法层面,德国法、法国法、日本法以及以《美国统一商法典》为代表的美国法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可以诚实信用原则限制解除权约定的效力。[43]
例如,对于轻微的义务违反尤其是轻微迟延,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债权人通常不得行使约定解除权。[44]主流观点表示,这一做法背后的理由在于“不成比例性”(Unverhältnismäßigkeit)的考量(尤其是对比《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第2句和第324条就法定解除设定的标准)。[45]相较于债务人轻微违约引发的微不足道的影响,债权人直接选择解除合同的做法有过度反应之嫌,违反了比例原则的要求。德国法上对比例性的考量适用于法律制度整体。以民法为例,该原则的作用途径即通过《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等一般条款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与德国法类似,《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9条的官方评注也指出,针对履行能力可能存在问题的情况,合同可以约定当事人享有广泛的解除或变更合同的权利,但在解释此类约定时必须意识到诚实信用是合同义务的固有内容,不得由约定排除。该条官方评注甚至认为,如果当事人约定的合同解除标准过于不公平,该约定直接无效。[46]
此外,值得参考的是,在《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一书中,编者交由各国学者进行国别报告的案例7“租金迟延”便是典型的轻微违约,[47]其实质争议与前文提及的商标权纠纷基本相同。[48]针对该案,参与报告的各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迟延支付租金仅两日的承租人应当获得保护,出租人不得解除合同,而以诚实信用原则限制解除权正是其中的代表性思路之一。[49]
针对上述观点,本文认为,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诚实信用原则无疑为权利行使设置了一般性的限制,行使约定解除权如果违反该原则,确实不应该产生解除的效果。就此而言,比较法上的主流观点并无错误。但是,如果着眼于轻微违约这一具体问题,以诚实信用原则既难以证成应当一般性地限制约定解除权,更无法为类似《九民纪要》第47条的规则提供正当性基础。
首先,轻微违约下解除合同未必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通常认为,权利人行使权利的仅在滥用权利时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问题在于权利滥用的构成要件包括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即客观上要求权利的行使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主观上要求以此种损害结果为主要目的。[50]在债务人轻微违约时,债权人行使约定解除权固然会损害债务人本可基于合同履行获得的利益,但此种损害往往并非权利人的主要目的。在实践中,债权人的此种做法背后可能存在许多类型的正当理由。例如,基于先前的履行情况,债权人已经不再信任债务人;再如,债权人是为了保证后续交易的完成或避免对第三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在缺乏特别约定时,债权人的主观偏好自然会受到法定解除规则的限制,但前已述及,约定解除的核心功能之一正在于保护当事人的此类主观偏好。[51]
而且,在当事人交易地位不存在结构性不对等时,前述主观偏好大多并非“恣意”,将其体现在合同中往往需要经过反复磋商,提出严苛解除条件的一方还可能为此接受对方提出的其他条件。[52]如果动辄以诚实信用原则进行限制,不仅使约定解除追求的意思自治沦为“口惠而实不至”,而且会破坏当事人缔约结果中隐含的利益交换关系。从整体经济的视角出发,当事人在交易中所表达的诸多主观偏好还构成市场经济中差异化竞争的基础,对此法律无疑应予保护。
此外,即使是貌似不甚合理的动机,也未必达到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程度。例如,债权人选择解除合同可能是因市场变化有了更好的交易选择,而解除权约定恰好给了债权人脱离原合同拘束的机会。此种反悔机会并非约定解除专属,而是解除制度提供的一般性保护。[53]甚至债权人在解除合同主要意在“攫夺”债务人已经付出的投入时也未必构成权利滥用,因为其行为目的并非单纯损害他人利益,而是为自身谋得利益。此时,即便认为债权人不值得保护,基于比例原则对必要性的要求,也不应当直接以诚实信用原则限制其行使解除权,而是应当首先考虑既有规则能否限制或阻止债权人的此种行为。
其次,诚实信用原则限制论的价值基础在于避免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但轻微违约下解除合同未必会造成此种结果,既有制度对此已有防范。所以,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限制基础可能违反基本原则的适用要求。[54]在以诚实信用原则直接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前,应当先分析既有具体规则能否避免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如果能够得出肯定的回答,便不应限制解除权发生。而后文将指出解除制度内外的一系列规则提供了诸多利益平衡机制。例如,当合同存在罚没约定时,可以准用违约金酌减规则;当解除权约定属于格式条款时,约定效力将受格式条款规则的限制。总之,本文虽然无意断言个案中一定不存在需要基于诚实信用原则限制解除权的情况,但也认为既有规则基本能够应对支持限制论者和司法实践所关注的案型。
最后,除了就轻微违约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存在错误认识外,《九民纪要》第47条还混淆了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的关系。根据该条第2句,如果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的实现,法院便不应支持守约方解除合同。问题在于如果合同目的的实现受到影响,守约方本就享有法定解除权,无需借助解除权约定。而且,当合同是否解除取决于对违约程度和合同目的而非解除权约定的解释时,这本质上是将约定解除问题置于法定解除的框架下分析。此时,本文一直强调的约定解除的两项特别功能均将受到严重影响。
相较于《九民纪要》第47条,《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第55条第1款删去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的要求,同时新增了“解除合同对违约方显失公平”的要件。但本文认为即使不考虑“显失公平”这一概括表述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的风险,此种修改方案也难言进步。
一方面,以诚实信用原则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本身并无错误,《九民纪要》第47条的不足在于该条第2句机械地认为只要违约程度轻微且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便不应允许解除合同。如果中国法必须规定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的规则,理想的方案是删去《九民纪要》第47条第2句,并在第1句中突出诚实信用原则的核心地位,违约程度和合同目的则可以作为裁判者应当重点考虑的因素予以保留。
另一方面,增加“显失公平”要件的目的似乎是防止法院动辄以《九民纪要》第47条限制约定解除权。而且,该要件看似还能灵活应对既有规则无法妥善处理的一些极端情况。问题在于以显失公平制度作为“控制阀”的正当性何在,以及其与诚实信用原则又是何种关系。在个案中,权利人行使约定解除权被认为对违约方构成显失公平的,此时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如果采肯定的回答,限制约定解除权的真正原因恐怕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如果采否定的回答,则既需要在价值判断上回应权利的行使为何须受制于“显失公平”要件的审查,又需要在教义学层面澄清显失公平制度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关系。尤其是通常认为显失公平制度主要关注的是法律行为的内容是否有效,权利行使的问题则属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控制领域。[55]《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第55条第1款似有误解两者关系之嫌。
1. 解除制度内部
解除权约定关注的是解除权何时发生,通常不涉及法律效果的问题,因此,即使认为约定解除权发生,该权利行使的具体效果仍须适用法定规范。[56]而在这些规范中,有诸多规则可以在轻微违约时发挥利益平衡的功能,至少包括以下三项:(1)部分解除;(2)解除权的消灭或限制行使事由;(3)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1)部分解除
最高人民法院在《九民纪要》释义书中表示,在适用第47条时应考虑违约行为的后果,“如果一方已经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比如已经支付了全部1000万元价款中的950万元,仅剩小部分尾款未付,此时,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即便违约也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不能轻易根据合同约定认为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57]
就法定解除权是否发生的判断而言,这一分析当然成立。因为950万元较之于总额1000万元已经构成“履行主要债务”,因而不能适用《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问题在于如果当事人明确约定不论迟延给付的价款为多少,守约方均可解除合同,此时是否必然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果。本文认为未必。在上例中,假设价款的对待给付在客观上可分且在交易观念上允许部分解除,除非当事人还明确以约定排除部分解除,否则,权利人在行使约定解除权时便应受到部分解除的限制。进而,其解除合同的表示只能免除剩余50万元价款对应的自身义务,而不能拒绝履行已付价款对应的义务或请求返还该部分给付。就此问题比较法上不乏类似规则。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第1句,在债务人已经提供部分给付时,债权人仅于该部分给付对其而言无利益时才可以解除整个合同。[58]在中国法上,虽然《民法典》没有在合同编中一般性地规定部分解除,仅在“买卖合同”一章中规定了第631-633条作为该领域的特别规则,但考虑到第646条确立的参照适用规则,第631-633条(尤其是第632条)无疑可以作为其他类型有偿合同适用部分解除的依据。
至于不适用部分解除的情况,考虑到给付整体对于债权人的意义,在债务人仅为部分给付或者整体给付存在瑕疵时,允许债权人解除合同亦难言造成利益失衡。以整体给付存在瑕疵为例,如前所述,在判断是否构成轻微违约时,不可修复的瑕疵程度是法院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问题常发生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例如,在当事人约定面积误差超过3%买受人即享有解除权而实际误差为3.48%时,有法院以“超出比例显著轻微,不足以导致购买房屋之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否认约定解除权。[59]但此种观点难言妥当。一方面,根据商品房买卖的法定解除规则,超过3%的面积误差已经足以引发解除权,[60]可见,3.48%的误差本身即可构成根本违约。即使没有解除权约定,当事人也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另一方面,开发商交付面积不符合约定的还可能构成履行欺诈,如果认为轻微违约下约定解除权不发生,则正好导向履行欺诈意图规避的后果——“被发现并无法律后果,不被发现则有净收益”。[61]而且,这一后果无法通过事后要求开发商就瑕疵给付承担违约责任而予避免。
(2)解除权的消灭或限制行使事由
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在本质上都是法律提供给当事人的选择性救济手段,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维持合同关系还是解除合同。不过,鉴于解除权的行使将直接引发当事人之间既存债之关系的变化,而且此种变化同时包括未履行部分义务的消灭和已履行部分的返还,所以,在解除权是否行使悬而未决时,相对人将处于极为不确定的状态。基于对相对人合理信赖的考虑,法律上设置了解除权的消灭规则,典型者如《民法典》第564条规定的解除权除斥期间规则。[62]在司法实践中,解除权的消灭事由中尤值注意的是权利人放弃解除权。[63]
详言之,在解除权发生后,如果守约方表示放弃解除权,无论是合意放弃还是单方弃权,其嗣后均不得再次主张解除合同。[64]在具体方式上,放弃解除权不以明示为必要,默示的意思表示亦足以发生相应效果。而判断是否存在默示的意思表示,主要依赖对当事人行为的推断。循此,在司法实践中占据首要地位的考量因素即是否补正履行便可得到妥当回应。
债务人事后补正履行的,债权人如果接受履行或者继续依约履行自身义务,则可从其相关行为推断出放弃解除权的意思。[65]例如,承租人连续四个月迟延支付租金虽然已经触发解除权约定,但出租人事后受领了补交的租金,且在此后近一年继续受领租金,[66]从其行为可以推断出放弃解除权的意思。
即使债权人未接受补正履行,其解除权也可能因为债务人的救治权(the right to cure)而受到限制。通常认为,与解除权相比,债务人的救治权具有优先性,[67]债权人原则上需要接受债务人的补正履行。[68]但也有观点主张,解除权发生意味着丧失补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债务人此时不应享有救治权。[69]本文认为,尽管中国法上并未明确规定违约救济手段的选择顺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债权人可以自由选择,实际履行排除事由、减损规则等均可能限制债权人的选择权。考虑到约定解除权的发生并不必然意味着丧失补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更为合适且兼顾当事人利益平衡的方案是,债务人在合同解除之前已经达到适当履行状态并提出补正履行的,债权人的解除权须受限于债务人的救治权,[70]但债权人可以通过证明存在正当事由排除救治权,例如已经同第三人开始缔约谈判,若退出则须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此外,解除权还可能因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权利人暂不行使而受到限制。对约定解除权而言,除非存在特别约定,否则权利人无需催告便可直接解除合同。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权利人暂不行使解除权的情况则不同,例如,债务人长期轻微违约但债权人未提出异议的,尽管不宜认为双方默示变更了合同义务,但至少可以认为债权人负有预先催告对方按约履行或者表示如不按约履行则解除合同的附随义务。[71]如果解除权人在对方违约后先催告履行,由于催告表明其仍欲获得履行,违约方亦有理由相信权利人暂不行使解除权。在此合理信赖期间内,违约方补正履行的仍属迟延履行,但应认为对方不得解除合同。至于该期间的确定,在解除权人指定的情况下依其所定,未指定则可参考《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中的“合理期限”。
(3)解除权的行使方式
正如当事人之间关于解除权是否发生的约定应被严格遵守,在当事人约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时,基于平等对待的考虑,即使解除权人只是轻微违反了行使方式之约定,也不应产生解除的效果。已有司法裁判注意到这一问题。例如,在当事人约定“延期交付土地超过60日的,经受让人催交后仍不能交付土地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时,正如该案裁判所言,“催交”应当理解为迟延交付60日后仍需催告方可解除合同。[72]所以,即使债权人曾在债务人迟延交付后的第55天催告履行,其后来解除合同的表示仍然因为不符合约定的行使方式而不应发生效力。相应地,约定行使解除权需预先通知但未通知而直接解除,[73]或者约定了解除通知发送地址但未发送到指定地址的,[74]均因不符合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约定而不产生解除的效果。
2. 解除制度之外
(1)格式条款与解除权约定
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等一般性效力瑕疵事由之外,解除权约定的效力需要特别关注格式条款规则,[75]比较法上亦不乏直接以具体规定进行内容控制的做法。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308条第3款,如果格式条款允许提供一方保留基于非实质正当且未载明于合同的理由免除自身给付义务之内容,则属于应受否定评价的格式条款,不拘束当事人。与之类似,在英国法上,如果解除权约定隶属于格式合同,则需通过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案》(Unfair Contract Terms Act 1977)第3条的合理性测试(reasonableness test);至于隶属于消费合同的约定,如果不属于2015年《消费者权利法案》(Consumer Rights Act 2015)明确规定无效的情况(如附件二第一部分第7条,类似于《德国民法典》第308条第3款),则需通过该法案第62条的公平性测试(fairness test)方可有效。[76]
循此,在解释约定解除权是否发生时,首先要考虑我国《民法典》第496-498条规定的格式条款规则能否适用,这对于解决实践中争议频发的金融借款纠纷尤为重要。[77]司法实践对此已经有所重视。例如,当事人约定借款人未按时偿还借款本金即构成违约,贷款人可以选择上浮借款利率或解除合同。在解释“未按时偿还借款本金”时,法院认为该条款系格式条款,在双方提出的解释方案均能与条款表述相洽时,应作出不利于条款提供一方的解释。最终,法院认为贷款人能否行使约定解除权取决于违约程度,而非一旦违约即可解除。此外,法院还指出如果按照条款提供一方的理解,即任何程度的违约均可解除合同,则属于不合理地加重对方责任或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无效条款。[78]
(2)损害赔偿限制规则
除了通过约定效力“前置”地限制解除权发生,还可以考虑控制解除后的违约损害赔偿使得守约方在对方轻微违约时缺乏行使解除权的动力。关于解除后的损害赔偿,中国法上素来存在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之争。尽管主流观点倾向于履行利益说,但亦有学者提出在合同尚可履行时,守约方主动消灭合同效力则不应再对合同的履行享有期待利益,解除后只能请求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79]
基于类似理由,比较法上有观点更是认为守约方行使约定解除权的,除非违约方的违约本身构成根本违约,否则守约方便只能请求赔偿解除时其已经遭受的损失,无权就因解除而消灭的未到期义务主张相应的履行利益赔偿。[80]例如,买受人迟延付款导致出卖人解除合同、另行交易的,如果买受人未构成根本违约,出卖人在解除合同后仅可向买受人主张迟延付款的损害赔偿,如果在此期间标的物价值下降,出卖人不得就该部分损失请求损害赔偿。[81]尽管此规则一般性地适用于约定解除权,但其在法律政策上的基础主要在于避免轻微违约下因解除权约定造成的不合理结果。[82]
然而,上述限制甚至排除损害赔偿的规则在正当性和必要性上均值得怀疑。[83]该规则与限制解除权发生的做法在正当性上存在类似问题。从外部第三人的视角观察,轻微违约的确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但守约方完全可能因为自身的主观看法不再信任违约方并意图摆脱合同关系的拘束,而法律在制度层面对约定解除的承认恰恰表明了其接受当事人以合意方式表达个别偏好。
更重要的是,在必要性上,限制或排除损害赔偿意在避免债务人因轻微违约承担过重的违约责任,但减损义务、损益相抵等规则已经提供了必要保护。在解除权人能够与第三方进行替代交易时,其最终可以主张的损害赔偿主要包括另行缔约的成本、标的物价值波动和替代交易完成前本应因履行获得的利益。以租赁合同为例,出租人因为承租人轻微违约而解除合同的,法院在计算损害赔偿时不能以剩余租期的租金为准,而应基于出租人的适当转租义务进行扣减。[84]如果标的物的市场流通性较强,守约方能够主张的损害赔偿更是微乎其微。考虑到这一点,守约方在对方轻微违约时便解除合同的动力其实相当有限。由此也不难理解在司法实践中解除权人为何很少在解除权发生后毫不迟延地直接解除。而在极端情况下,以减损规则为代表的限制规则甚至可能使得解除权人负有与相对人重新缔约的不真正义务。典型者如市场上缺乏合理的替代交易机会,与原本的债务人缔约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损失的情况。[85]
(3)解除后返还与违约金酌减
相较于解除权人请求损害赔偿的范围,中国的司法实践更关注的还是当事人基于合同关系的既有投入如何处理,比如承租人就租赁物已经支出的费用以及各种承包关系下承包人投入的固定成本。在此类案件中,如果合同还包含罚没约定,即使对方轻微违约,解除权人也有较强动力解除合同。
就此,首先需要考虑关于解除法律效果的一般规则。根据《民法典》第566条第1款,已经履行的部分需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返还。所以,违约方就合同解除前的各种支出可以主张原物返还或者价值偿还。其次,还需考虑关于解除法律效果的特别规范。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号发布,法释[2020]17号修改)第9条第2项和第11条,如果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或扩建,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承租人负担。相反,在经过出租人同意时,尽管承租人不得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的残值损失,但出租人同意利用的应在利用价值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最后,如果当事人约定守约方可以保留违约方提供的给付而无需价值返还,则可能构成实质意义上的违约金约定,[86]法院应准用违约金酌减规则,综合个案中违约方的违约程度、守约方所受损失等因素予以确定。在排除返还的利益过分高于守约方遭受的损失时,违约方可以请求守约方返还明显超出部分的价值。
综上,即使允许权利人在轻微违约下行使约定解除权,也不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明显失衡。司法实践关注的考量因素可以通过既有具体规则的适用得以明确。因此,权利人依约解除的行为便难言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鉴于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可能产生的弊端,本文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不足以一般性地限制轻微违约下的约定解除权,以违约程度和是否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为标准创设一项独立的限制规则更是难言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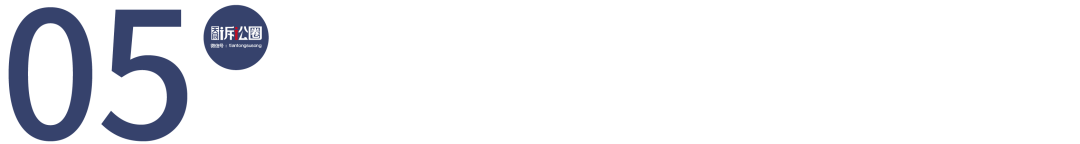
结论
综上,主张轻微违约下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的三项理由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首先,强调实质意义上当事人真意的观点虽然意识到合同解释的优先性,但错误地选择了以实质违约理论为代表的解决方案。出于维护约定解除制度功能的考虑,更为合理的方案是对解除权约定进行类型化,并在区分概括约定与具体约定的基础上相应地配置任意性规则。概括的解除权约定原则上不发生相应效力,具体的解除权约定原则上应予尊重。
其次,基于体系评价一致性而主张类推适用违约金酌减等规则的观点亦不成立。从形式上看,违约金酌减和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都是基于平衡当事人利益而限制合意效力,但两者对权利人法律地位的影响存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异。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不仅可能使权利人错误地作出解除合同的表示,导致其自身构成违约,还会破坏权利人对合同将被解除的合理信赖,导致其后续安排目的落空。
最后,以诚实信用原则难以证成轻微违约下应当一般性地限制约定解除权。权利人可能出于各种正当理由而选择在对方轻微违约时解除合同,即便其主要动机是为了从对方处获得利益,也不应直接认定为权利滥用。至于当事人利益可能失衡的问题,应当通过解除制度内外的一系列规则予以解决。以司法实践关注的三项考量因素为例,“是否补正履行”应在解除权消灭和限制行使的框架下予以分析;“义务违反程度”本身不能说明限制解除的合理性,部分解除、减损义务等足以避免可能的利益失衡;“因合同关系产生的既有投入”主要涉及解除后的返还关系,存在罚没约定时可以类推适用违约金酌减规则。在个案中,法院应当首先适用前述具体规则,仅在具体规则无法解决问题时方可诉诸诚实信用原则。在适用该原则时需要遵循就该原则的适用已经形成的共识,比照既有案型并充分说理,不能仅因违约程度轻微、合同目的不受影响便限制权利人行使约定解除权。
整体而言,既有制度足以应对轻微违约下允许行使约定解除权可能引发的利益失衡问题。以《九民纪要》第47条和《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第55条第1款为代表的规则可能对约定解除的制度功能产生负面影响,在规范正当性上值得怀疑。相比之下,《民法典》第562条未采纳类似规则的做法应予赞同。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233号民事裁定书。
[2]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浙杭民终字第394号民事判决书。
[3]四组替换表述分别为“违约程度+第五百六十二条”“违约程度+第九十三条”“轻微违约+第五百六十二条”以及“轻微违约+第九十三条”。检索条件均为“裁判理由及依据+常规+民事”,并从结果中剔除审级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案例。本文援引的案例均来自“威科先行数据库”,最终检索时间为2023年1月31日(未限定起始时间)。
[4]除前述租赁合同纠纷外,还可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3民终3160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3民终3186号民事判决书。
[5]或许有人会质疑正因为法官想要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所以才会援引该条,以该条作为检索条件注定会得出司法实践倾向于限制轻微违约解除的结论。倘若如此,则该条已经成为法院动辄限制约定解除权发生的兜底性规定,而这亦是本文所担忧之处。
[6]参见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7民终4939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再193号民事判决书。
[8]See Guenter Treitel,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p.360-361.
[9]See Hugh Beale (ed.), Chitty on Contracts, Sweet & Maxwell, 2021, para. 25-055.
[10]See Kason Kek-Gardner Ltd v. Process Components Ltd [2017] EWCA Civ 2132.
[11]See Kim Lewis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Sweet & Maxwell, 2020, para. 17.115.
[12]英国法上将设定义务的合同条款分为条件(condition)、保证(warranty)和无名条款(innominate term)。在债务人违反条件性义务时,无论违约程度如何,均可产生法定解除权(不妨对比德国法上定期债务中的履行迟延);在债务人违反保证性义务时,无论违约程度如何,均不产生解除权;在债务人违反无名条款性义务时,则需要考虑违约程度,仅当债务人构成根本违约时债权人方可获得解除权。在英国法上,解除权约定的主要意义在于针对无名条款性的义务,即使债务人未构成根本违约债权人仍可解除合同。
[13]See Mid Essex Hospital Services NHS Trust v. Compass Group UK and Ireland Ltd (Trading as Medirest) [2013] EWCA Civ 200.
[14]参见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2021)豫0505民初1325号民事判决书。
[15]See Jack Beatson, Andrew Burrows & John Cartwright, Anson’s Law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 p.63.
[16]See Re Sigma Finance Corporation [2008] EWCA Civ 1303.
[17]See Antaios Compania Naviera SA v. Salen Rederierna AB (The Antaios) [1985] AC 191.
[18]See Rice (T/A the Garden Guardian) v. Great Yarmouth Borough Council [2003] T. C. L. R. 1.
[19]中国法上持类似观点的判决,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6民初141号民事判决书。
[20]See Dominion Corporate Trustees Ltd v. Debenhams Properties Ltd [2010] EWHC 1193 (Ch).
[21]参见[法]弗朗索瓦·泰雷等:《法国债法:契约篇》(下),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9页。
[22]参见李世刚:《法国合同法改革——三部草案的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32页。
[23]François Terré etc., Droit civil Les obligations, Dalloz, 12 e éd., Paris, 2019, p. 857.
[24]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987号民事判决书。
[2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494号民事判决书。
[26]See Bates v. Post Office (No. 3) [2019] EWHC 606 (QB).
[27]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2、3项规定的解除事由均以不履行“主要债务”为前提,在当事人指明何种义务但未说明何种程度的违反足以引发解除权时,当事人约定所指向的义务可能并非主要债务。此时,应当认为该义务因当事人的特别约定而“升格”为主要债务,进而可以适用前述两项。这也是第二种概括约定较之于第一种概括约定仅有的特别意义。
[28]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50页;Simon Whittaker, Termination Clauses, in Andrew Burrows & Edwin Peel (eds.), Contract Ter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58-259.
[29]See John Randall, Express Termination Clauses in Contracts, Cambridge Law Journal, Vol. 73, Issue 1, 2014, p. 115.
[30]See Thomas Merrill & Henry Smith, 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110 Yale Law Journal 1, 35-38 (2000).
[31]See Richard Hooley, Express Termination Clauses, in Graham Virgo & Sarah Worthington (eds.), Commercial Remedies: Resolving Controvers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43.
[32]See Dalkia Utilities Services plc v. Celtech International Ltd [2006] 1 Lloyd’s Rep 599.
[33]See Mid Essex Hospital Services NHS Trust v. Compass Group UK and Ireland Ltd (Trading as Medirest) [2013] EWCA Civ 200.
[34]此种规则属于惩罚性的任意性规则(penalty default rule)。See Ian Ayres & Robert Gertner, Filling Gaps in Incomplete Contracts, 99 Yale Law Journal 87, 92-94 (1989).
[35]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再193号民事判决书。
[36]参见[法]弗朗索瓦·泰雷等:《法国债法:契约篇》(下),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7-1278页。
[37]参见葛云松:《期前违约规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页。
[38]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增订新版),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463页。
[39]Vgl. Bötticher, Wesen und Arten der Vertragsstrafe sowie deren Kontrolle, ZfA 1 (1970), 3, 24 ff. 转引自姚明斌:《〈合同法〉第114条(约定违约金)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5期,第166-167页。
[40]参见李建星:《加速到期条款之内容规制》,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9期,第130页。
[41]参见[奥]恩斯特·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页。
[4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637页。
[43]See Guenter Treitel, 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60-361; [日]我妻荣:《债权各论》(上卷),徐慧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44]Vgl. Gai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9. Aufl., 2022, § 354 BGB Rn. 2.
[45]Vgl. Looschelders/Olzen, i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Neubearbeitung, 2019, § 242 BGB Rn. 679.
[46]Se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Official Text and Comments, Thomson Reuters, 2014, p. 141-142.
[47]See Reinhard Zimmermann & Simon Whittaker (eds.), Good Faith in European Contract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05.
[48]类似案件还可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2022年重排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75页。
[49]See Reinhard Zimmermann & Simon Whittaker (eds.), Good Faith in European Contract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20.
[50]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5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页。
[51]同旨参见陆青:《合同解除论》,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12页。
[52]同旨参见姚明斌:《违约金酌减事先排除特约的效力》,载彭诚信主编:《民法案例百选》(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358页。
[53]See Edwin Pe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2020, para. 18-002.
[54]方法论上的说明,参见王泽鉴:《诚实信用与权利滥用》,载《北方法学》2013年第6期,第8页。
[55]参见贺剑:《〈合同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显失公平制度)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1期,第166页。
[56]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57页。
[57]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315页。
[58]Vgl. Ernst,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8. Aufl., 2019, § 323 BGB Rn. 204.
[59]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6民终4393号民事判决书。
[60]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14条第2项被废止后,《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20条第2款第2项仍可作为此种法定解除权的依据。
[61]洪国盛:《论消费者保护法上的履行欺诈》,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3期,第36-37页。
[62]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1民终10031号民事判决书。
[63]本可以此否认解除的,参见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皖01民终8435号民事判决书。
[64]See Edwin Pe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2020, para. 18-094.
[6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3335号民事裁定书。
[66]参见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琼96民终1049号民事判决书。
[67]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93页。
[68]关于补正履行的分歧,参见朱心怡:《不完全履行下债权人救济途径选择权之限制》,载《法学》2022年第4期,第136-140页。
[69]参见武腾:《救济进路下不完全履行的定位和效果》,载《法律科学》2021年第3期,第163页。
[70]See Reinhard Zimmermann & Simon Whittaker (eds.), Good Faith in European Contract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14.
[71]Vgl. Kaiser, i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GB, Neubearbeitung, 2012, § 346 BGB Rn. 49;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终32247号民事判决书。
[72]参见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13民初75号民事判决书。
[73]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民终15379号民事判决书。
[74]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2549号民事判决书。
[75]面对具体案件时首先应该判断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参见王轶:《新冠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载《法学》2020年第3期,第39-40页。
[76]See Hugh Beale (ed.), Chitty on Contracts, Sweet & Maxwell, 2021, para. 25-063. 关于两项法案的适用区分及具体内容的介绍,参见Mindy Chen-Wishart, Contrac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452-454.
[77]参见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21)湘0102民初2935号民事判决书。
[78]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终217号民事判决书。
[79]参见王利明:《合同编解除制度的完善》,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3期,第25页。
[80]See Financings Ltd v. Baldock [1963] 2 Q. B. 104. 英国法上,合同解除仅使当事人免于履行尚未到期的债务,在不涉及能够主张返还请求的若干特殊情况时,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已经获得的履行以及虽未履行但已经到期的债务仍然有效(类似于大陆法系中的合同终止,但英国法以债务是否到期而非当事人是否履行为区分标准)。以迟延履行导致合同解除为例,债权人既可以主张因为解除而消灭的债务对应的履行利益损害赔偿,也可以主张迟延履行未因合同解除而消灭的那部分债务对应的迟延损害赔偿。See Mindy Chen-Wishart, Contrac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504-505.
[81]See Andrew Burrows (ed.), English Privat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75.
[82]See Edwin Peel, Treitel on the Law of Contract, Sweet & Maxwell, 2020, para. 18-068.
[83]英联邦范围内的反对意见,参见Keneric Tractor Sales Ltd v. Langille (1987) 43 D. L. R. (4th) 171.
[84]参见朱虎:《解除权的行使和行使效果》,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5期,第106页。
[85]See Sotiros Shipping Inc v. Sameiet [1983] 1 Lloyd’s Rep 605.
[86]在形式上是否界定为违约金不影响在结论上认为法院应当介入。参见陆青:《合同解除效果的意思自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1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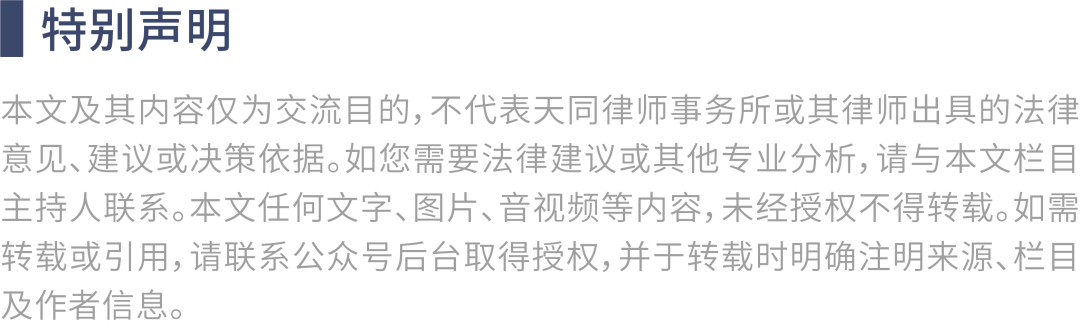
“合同实务”栏目由廖鸿程律师、吴陶钧律师主持,战斗在合同实务栏目一线的天同律师们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合同实务的相关思考。如您对“合同实务”栏目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查看往期文章,请点击以下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