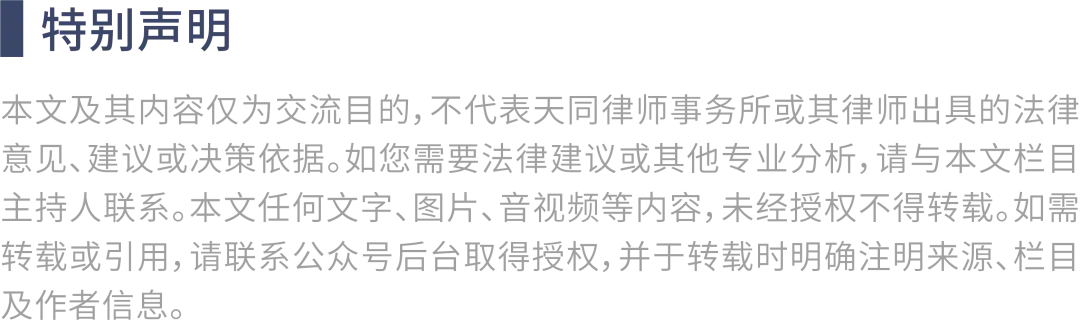注:本文原载《法学家》2022年第5期第177-190页。
《民法典》第188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目录
一、规范意旨
(一)规范意义及正当化理由
(二)规范性质
(三)适用范围
1、第188条第2款第1句的适用范围
2、第188条第2款第2句的适用范围
二、时效起算的一般条件(第2款第1句)
(一)条件一:权利受到损害
1、权利
2、“受到侵害”抑或“受到损害”
3、“受到损害”的样态
4、损害的确定性
(二)条件二: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1、权利人
2、知道
3、应当知道
4、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程度(可发现性标准)
(三)条件三: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
1、义务人
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程度
三、时效起算的常见案型
(一)履行期限明确的合同
(二)持续性侵权
(三)违约金
四、时效起算的效力
(一)起算时点
(二)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三)从权利
1、利息债权
2、担保权
五、举证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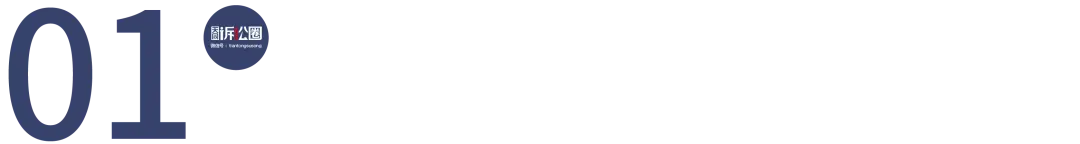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规范意旨
(一)规范意义及正当化理由
【1】《民法典》第188条(以下简称“第188条”)第2款第1句、第2句是诉讼时效起算(以下简称“时效起算”)的基础规范。第1句规定时效起算一般条件,其修改了《民法通则》第137条第1句对时效起算一般条件的规定。第2句规定一般条件与特殊规定的关系,《民法通则》无该内容,属新设规定。该两句与《民法总则》第188条第2款第1句、第2句完全相同。
【2】时效起算的直观意义是使计算时效期间的始点得以确定,因其影响时效期间计算和实际长短,故与时效期间规则相互协调、互为牵制,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安全性和伦理性价值。[1]时效起算标准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贯彻程度以及立法者对权利人的“容忍”程度,因为时效起算条件具备前不构成“怠于行使权利”。时效起算对适用其他规则具有“前置意义”:时效未起算,无论经过多长时间,时效抗辩权都不可能产生;时效未起算,中止、中断、延长规则就不能适用,即使发生了相应事由。
【3】比较法上,时效起算标准存在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客观主义,以某种客观事实发生时点为时效起算点。[2]二是主观主义,以权利人知晓某种事实的时点为时效起算点。[3]合同请求权的到期日和义务人相对明确,故多采客观主义;侵权请求权常出现侵害行为、损害与义务人确定时间不一致的情形,故多采主观主义。但在始于21世纪初的德国、日本[4]等国修法活动中,似有将合同与侵权时效起算标准予以统一的趋势:普通时效期间采主观标准,辅以最长时效期间采客观标准。该做法的主要原因是区域性条约的影响,[5]以及为解决因起算标准不一致在实务中造成的困扰等。[6]
【4】《民法通则》第137条采主观主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且未区分合同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而采统一起算标准。《民法典》第188条第2款第1句继承了该做法,但将起算的具体条件修改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我国现行法模式与德、日等国新近立法态度较为接近。依据立法机关释义书的解释,其立法理由在于:其一,在立法技术上,该起算标准配合(较短的)3年普通时效期间,有利于诉讼时效制度各价值目标的平衡。其二,基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活差异较大”的现实,该起算标准较为公平。[7]有学者以“有利于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诉讼时效制度目的、[8]“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9]“由此显示法律对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状况的平衡”[10]“与诉讼时效适用对象是救济性请求权相一致”[11]等视角,论证该起算标准的合理性。亦有学者认为,第188条第2款第1句应解释为“主客观相结合的认定标准”[12]或者“自权利可以行使时起算”。[13]
【5】现行法框架下的一般起算标准,总体上应解释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可以行使权利之日起算”,即行使权利的法律障碍消除且当事人对此知情的最早时点为起算点。理由如下:其一,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而言,“怠于行使权利”以“可以行使”为当然前提,故权利行使条件具备前起算时效没有意义。其二,各立法被冠以主观主义或客观主义标签,仅是对其法条表述的直观描述,而对“可以行使权利时起算”实则存在很大程度共识。各立法的真正区别仅是对“可以行使”的认定标准侧重点有所不同。[14]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典》之起算标准亦为“可以行使”标准的具体化,二者差异则反映了立法者对“可以行使”认定标准的变化。其三,比较法上,“可以行使”通常解释为“行使权利的法律障碍消除”,即行使权利的期待可能性程度应当满足各类法律关系的要求。[15]时效起算是否要求权利人对此知情,存在肯定说[16]和否定说[17]两种做法。考虑到第188条第2款第1句明确要求“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及比较法经验,我国采肯定说较为妥当。其四,与“法律障碍”相对的“事实障碍”(如权利人因身体欠佳、工作繁忙无暇行使权利)原则上不影响时效起算,仅某些严重的“事实障碍”(如不可抗力)被法律规定为中止事由。
【6】《民法典》施行前,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针对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合同撤销后果、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时效起算所作规定,系以《民法通则》《合同法》中“未定履行期限合同的宽限期规则”等规定为依据。[18]《民法典》第511条等继承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相关规定,2020年修正后的《诉讼时效规定》也保留了司法解释规定。因此,《诉讼时效规定》第47条对上述情形下时效起算的解释于《民法典》施行后仍应适用,既有文献和司法意见也仍具说明意义。
(二)规范性质
【7】依据“职权禁用规则”(《民法典》第193条)的精神,是否依据第188条第2款主张时效起算,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时效起算规则。有权主张时效起算的主体是讼争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包括权利人、义务人及其代理人、财产代管人等。义务人对权利人请求主张时效抗辩的,可将时效起算作为时效抗辩权成立的依据,权利人亦可将时效起算、中断等作为反抗辩的手段。
【8】时效起算规则属强制性规范,当事人对其另行作出的约定无效(《民法典》第197条)。但在合同关系中,当事人通过约定履行期限实质性地导致时效起算点被提前或推迟的,并不被禁止。时效起算后(原履行期限届满),当事人达成延期履行协议的,导致时效中断(《诉讼时效规定》第14条),而非时效再次起算。
【9】法院受理诉讼案件时不应审查时效起算事项,受理后义务人(被告)主张时效抗辩的,法院依据时效起算等规则予以实体审理并据此作出判决(《民诉法解释》第219条)。法院受理申请执行案件时也不应审查时效起算事项,受理后义务人(被执行人)以时效抗辩为由提出异议的,法院依据时效起算等规则判断异议是否成立。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不予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1条第1款)。这是“抗辩权发生主义”“职权禁用规则”在程序法上的体现。[19]
(三)适用范围
1、第188条第2款第1句的适用范围
【10】本句规定的时效起算一般条件,适用于普通时效期间和法律未对起算另作规定的特殊时效期间。20年最长时效期间不适用本句规定,而适用同款第3句之起算条件(客观主义标准)。
2、第188条第2款第2句的适用范围
【11】本句之“但书”具有引致条款的作用,表明某些特殊领域的时效起算规定与同款第1句构成特别规范与一般规范的关系。[20]本句之“法律”仅指狭义法律和司法解释,[21]分为以下几种情形讨论。
【12】其一,《民法典》其他条文的规定。例如分期履行债务时效起算(第189条);对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时效起算(第190条);受性侵未成年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时效起算(第191条);保证债务时效起算(第694条)等。这些条文系基于特殊规范目的所作规定,属于本句“另有规定”情形。
【13】其二,民商事单行法对《民法通则》第137条第1句的重复规定。例如《环境保护法》第66条、《产品质量法》第45条第1款、《拍卖法》第61条等。这些条文是对《民法通则》第137条第1句的简单重复或变相重复,因其不具有特殊规范意旨而不构成“真正意义的”特别规范,故不属于本句“另有规定”情形。由于第188条第2款第1句对时效起算的一般条件作出修改,故《民法典》施行后上述规定不再适用,而应适用第188条第2款第1句。
【14】其三,民商事单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特殊规定。例如保险金请求权时效起算(《保险法》第26条、《保险法解释二》第16条);票据权利时效起算(《票据法》第17条);海商法上请求权时效起算(《海商法》第257-265条)等。这些条文系基于商法等领域特殊规范目的所作规定,属于本句“另有规定”情形。
【15】其四,仲裁领域的法律规定。《民法典》第198条规定,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构成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关系,故仲裁时效起算规则应遵循该要求。包括:第一,商事仲裁领域中,现行法对仲裁时效起算未作规定,故应适用第188条第2款第1句。第二,劳动争议仲裁领域中,《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系对《民法通则》第137条第1句的重复,故《民法典》施行后不再适用,而应适用第188条第2款第1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4款之拖欠劳动报酬争议的时效起算规定具有特殊规范意义,故属于本句“另有规定”情形。第三,土地承包争议仲裁领域中,《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8条系对《民法通则》第137条第1句的重复,故《民法典》施行后不再适用,而应适用第188条第2款第1句。[22]
【16】其五,执行领域的法律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46条第2款规定,申请执行时效起算点是“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者“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该规定系基于执行领域“及早稳定经济关系、提高执行效率”等特殊规范目的,[23]属于本句“另有规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法释〔2008〕9号)第8条规定,内地判决到香港特别行政区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时效起算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46条第2款;香港特别行政区判决到内地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时效起算点是“判决可强制执行之日”或者“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
时效起算的一般条件(第2款第1句)
(一)条件一:权利受到损害
1、权利
【17】该“权利”是指原权利,包括绝对权(物权、人格权、知识产权等)和相对权(合同债权、不当得利债权、无因管理债权等)。该“权利”本身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其被侵害产生的救济性请求权(如侵权请求权、违约请求权)为诉讼时效的直接限制对象。因此,诉讼时效意义上的“怠于行使权利”是指怠于行使救济性请求权,从而导致时效起算。
【18】该“权利”亦包括某些民事利益(如死者人身利益),因为此类民事利益受到损害而产生的侵权请求权,也应适用诉讼时效。[24]
2、“受到侵害”抑或“受到损害”
【19】《民法通则》将该条件表述为“受到侵害”,《民法典》改为“受到损害”。对于该变化的解读,存在分歧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侵害”改为“损害”不构成实质性变更,“受到损害”仍应解释为权利受到侵害或请求权产生之时。[25]第二种观点认为,《民法通则》所采“侵害”有欠准确,《民法典》改为“损害”更为精确,该“损害”大于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26]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其一,该条件的核心意义是请求权内容客观上被确定,从而满足行使权利的前提。是否构成“受到损害”,应结合请求权的具体要件予以判断。其二,对于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在侵害行为与(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发生时间不一致的情形下,因“侵害”发生时请求权内容尚不明确,故起算时效尚存法律障碍。因此对于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作为时效起算条件的“受到损害”是指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发生。其三,并非仅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他适用诉讼时效的请求权(如违约金请求权、双倍返还定金请求权等)成立不以(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为要件。对这些请求权而言,作为时效起算条件的“受到损害”,意指请求权成立要件之“行为要件”(如违约行为)具备。对这些请求权而言,“受到侵害”与“受到损害”具有相同意义。其四,虽然侵害行为发生是法律救济的前提,但直接针对侵害行为的救济性请求权(停止侵害)不适用诉讼时效,故一律以“侵害”直接作为时效起算条件并不妥当。
【20】该条件之“受到损害”的意义在于:其一,权利受到损害始有救济的必要,对救济性请求权进行时间限制的诉讼时效才有起算的可能。其二,“受到损害”是请求权内容得以确定的前提,并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及进一步行使权利提供了可能。
3、“受到损害”的样态
【21】基于上文分析,“受到损害”的核心判断标准是权利被侵害后请求权的内容是否被确定,故不应机械地以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发生为认定标准。对于不同类型请求权而言,作为时效起算条件的“受到损害”的样态亦不相同。分述如下:
【22】其一,对于损害赔偿请求权,“受到损害”是指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发生,而非侵害行为(侵权行为、违约行为)发生。例如某豆种买卖合同纠纷中,卖方售出并交付不合格豆种的时间是2004年底至2005年3月23日(违约行为发生时),豆种种植后产出不合格大豆最迟是在2006年8月21日(损害发生时)。买方的诉讼请求是赔偿损失,应以2006年8月21日(损害发生时)为时效起算点。[27]
【23】在侵权法领域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曾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28]该规定系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中将《民法通则》之“受到侵害”扩张解释为“受到损害”,其精神与【19】之观点一致。第188条第2款第1句系将该扩张解释上升为一般标准。
【24】其二,对于继续履行、违约金等不以(损害赔偿意义上的)损害为要件的请求权,“受到损害”是指(作为请求权成立要件的)侵害行为发生。例如:第一,合作开发纠纷中,当事人一方向对方明确表示拒绝履行义务;[29]第二,合同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函,否认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30]第三,施工合同纠纷中,发包人擅自将涉案工程分包给第三人,系以行为表明拒绝履行义务[31]等。
4、损害的确定性
【25】损害的确定性程度,依是否消除法律障碍判断,即损害的确定性只需满足权利人起诉条件即可,而无须百分之百确定。分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26】其一,一般情形下,损害“类别确定”就具备时效起算条件,而无须“数额确定”。最终损害数额通过实体审理认定,起诉时并不要求权利人对损害数额已形成精确结论。例如:第一,债务人向债权人发出“企业询证函”,将其财务记载为“预付款项”的款项确认为工程款(类别确定且数额确定),债权人才确定未归还本案借款,其债权受到侵害;[32]第二,受害人到医院检查,诊断意见为“轻—中度异常脑电图”“大脑发育不良”等,此时伤害结果已非常明显并经医院检查确诊(类别确定但数额尚不确定),具备时效起算条件;[33]第三,转让款数额确定,仅因增值税冲减影响数额计算的(类别确定但数额尚不确定),不影响时效起算[34]等。
【27】其二,如果损害数额、比例等须经法律程序才能确定,而确定前对权利人起诉构成法律障碍,则损害数额、比例等确定才具备时效起算条件。例如:第一,合同约定标的物最终价格按国家计委等部门批准价格执行,订约一年多后国家计委文件调价通知下发,标的物价格即已确定,卖方的价差补偿请求权此时才具备时效起算条件;[35]第二,船舶碰撞事故发生后,海事局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事故调查结论,认定A轮负次要责任、B轮负主要责任,此时责任比例划分得以确定,具备时效起算条件;[36]第三,用人单位通过《会议纪要》等程序确定“买断工龄款”具体数额前,不具备时效起算条件[37]等。
(二)条件二: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
1、权利人
【28】该“权利人”是指有资格行使请求权的人,包括权利人本人、代理人、财产代管人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6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应以其法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判断标准,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为权利人本人欠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意思能力。委托代理情形下,权利人本人或者代理人中任何一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即满足该条件,因为二者均具有行使权利的资格。公益诉讼情形下,“权利人”是指依法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民事诉讼法》第58条)。[38]
【29】权利由法人享有的情形下,并非仅法定代表人构成“权利人”,董事和员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亦满足该条件。[39]因为基于后者职务上的报告义务,可以此推定前者应当知道。权利由非法人组织享有的,应作相同解释。
【30】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形下(《民法典》第16条),其权利(如遗产应继份)受到损害的,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相同处理,即以其监护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判断标准。该监护人不仅限于母亲,[40]也包括父亲以及父母均无监护能力时为被监护人设置的其他监护人(《民法典》第27条)。
2、知道
【31】“知道”本意是指权利人对某事实已知情的实然状态。虽然该心理状态属于主观范畴,但可凭借权利人言行、具体情境等因素作出认定。可认定“知道”的情形包括两种:一是其言行表明其知情;二是其言行虽然否认知情,但依常识、交易习惯等因素判断,有高度盖然性知情。[41]在后一情形下,“知道”实为极大概率的、不容否认的“应当知道”,即结合相关因素其几乎不可能不知情(如收到通知、鉴定书[42])
【32】实务中,认定为构成“知道”及其时点的情形包括:第一,损害由另一诉讼认定的,“知道”时点为判决书送达时,而非依据该判决申请强制执行时;[43]第二,侵害著作权纠纷中,原告(作者)实际购得侵权书籍之日,为“知道”被告(出版社)侵害行为之时;[44]第三,甲受雇于被告工作期间失踪,后被法院宣告死亡,权利人(甲的近亲属)“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是宣告死亡之日[45]等。
3、应当知道
【33】“应当知道”是指虽然权利人对某事实不知情,但其对不知情具有可归责性,故与“知道”作相同处理。对于“应当知道”的标准,存在两种意见。客观说认为,应采“一般人标准”[46]“理性人标准”[47]等客观标准判断,无须考虑权利人的实际智识能力。折中说认为,应以客观标准为原则、主观标准为补充。单纯的客观标准不考虑权利人特殊的专业背景、预见能力,失于机械和准确,而单纯的主观标准过于强调个案特殊性。[48]权利人判断能力明显高于理性人标准时,应以权利人本人的判断能力为准。[49]相较而言,折中说更为合理。实务中,法院判断是否构成“应当知道”时通常会适当考虑相关主观因素,例如“权利人作为香港企业,不便知晓内地公司的经营状况”[50]“权利人距离标的物交付地点较远”[51]等。
【34】进一步的问题是,折中说中的客观标准具体内容如何界定?学界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应采一般过失标准,前述“一般人标准”“理性人标准”等意见即为其例。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借鉴德国法,采重大过失标准。[52]笔者赞同观点二,即“应当知道”应解释为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理由如下:其一,现行法将“知道”与“应当知道”并列规定,二者认定标准不宜过于悬殊。由于他人无法真正了解义务人的内心,而“应当知道”在大多数场合下是义务人对权利人以不知情辩解的反驳,只有当注意标准极低时(重大过失)该反驳才是有力的,因为此时权利人的心理状态与推定的“知道”已很难区分。其二,观点一有偏离时效起算主观主义之嫌,因为作为中性标准的一般过失很难与客观主义之“可以行使权利时起算”严格区分。其三,侵权法领域采一般过失标准,通常系针对某一时点的行为作出评价。时效领域中要求权利人在持续期间内遵守较高注意义务似过于苛刻,仅当注意义务要求极低权利人却仍未注意时,其心理状态与明知才具有类似强度的道德可责性,而使其具有可归责性。[53]其四,一般过失标准与重大过失标准的本质差异是,前者采理性人标准,后者采普通人标准。[54]德国债法改革后改采主观主义,并在起算标准中增设“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当知道”之规定(《德国民法典》第199条)。依此标准,并不要求权利人对使请求权成立的事实和义务人本人进行广泛的调查,但如果该调查既不费力也不需要大量费用,则权利人负有调查义务。一般而言,在没有各种情况的具体线索或者特征时,权利人不负有调查义务。[55]德国法的这种变化,体现了向普通人标准的回归。考虑到我国时效期间偏短(3年)以及社会信用状况不佳的现实,采普通人标准有利于强化权利人时效利益保护,故更为合理。
【35】实务中,对“应当知道”的认定多体现了重大过失标准的精神,虽然判决书未必就此展开论证。认定构成“应当知道”的情形包括:第一,施工合同约定了获得省优工程奖励2万元的条款,权利人在2009年6月21日案涉工程被评为省优工程奖时就“应当知道”可以向对方主张该权利;[56]第二,当地电视台曝光被告(房地产开发商)违约交房的事情,推定原告(普通购房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损[57]等。
【36】认定不构成“应当知道”的情形包括:第一,被告发给原告的“克虏伯公司报价表”,与克虏伯公司真实的报价表样式、TAGAL标识完全相同,使原告误信该报价表即为真实报价表,故此时原告并不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58]第二,原告(某企业)据以起诉的两份信用证,是法院在审理另一案件时依职权向工商银行调查取得,在此之前原告客观上无法取得该证据,无法得知其权利是否被侵害;[59]第三,货款托收纠纷中,法院认为在仅告知汇票被承兑的情况下,被上诉人无法据此判断单据是否已经放走、款项是否已经收回,故也无法知晓其权利是否受到侵犯[60]等。这些裁判意见亦体现了重大过失标准的精神。
4、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程度(可发现性标准)
【37】基于一般起算标准中“法律障碍消除”的要求,只要行使权利的法律要件具备且权利人对此知情,即满足时效起算条件。换言之,可发现性标准仅要求权利人对“行使权利具有法律上的期待可能性”知情,而非要求权利人掌握的信息达到行使权利必然成功或大概率胜诉的程度。
【38】一般而言,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下事项即满足可发现性标准要求:一是使救济性请求权产生的基础事实(侵权行为、违约行为);二是对该请求权的法律评价。[61]事项一的判断相对简单。事项二应采普通人标准判断:如果普通人基于事项一可推知行使权利的法律要件基本具备,则符合起算条件;如果普通人须借助专业人员才能作出法律评价(如资本投资欺诈),在得知专业评价前起算条件尚不具备。[62]例如:委托服务合同中,委托人怀疑受托人工作可能存在瑕疵,另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被收购公司进行审计评估,审计报告作出时委托人方为“知道”。[63]
【39】权利人无需对影响行使权利的所有因素有所认知,因为“可以行使权利”不等于行使权利不存在任何阻碍或者必然成功。下列事项不构成行使权利的法律障碍,不属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事项:义务人是否能够提出抗辩;义务人是否存在免责事由;是否具备适用过失相抵的条件[64]等。
(三)条件三: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
1、义务人
【40】该义务人是指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对象。如果权利人不知义务人为何人,因不能确定行使权利的对象而构成法律障碍。该条件在侵权、不当得利等案件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合同案件中意义并不明显。《民法典》施行前,学说上多将《民法通则》规定的起算标准扩张解释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65]第188条第2款第1句新增该条件系对该扩张解释的确认。
【41】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义务人(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不知其监护人是谁,不影响时效起算。因为:一方面,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作为民事诉讼被告,行使权利不存在法律障碍;另一方面,如果时效起算后因尚未确定监护人而影响权利行使,可适用时效中止规则得到救济。
【42】义务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合并、分立,权利人不知新义务人的,分两种情形处理:其一,义务人合并、分立前时效已起算的,由新义务人继受时效计算的效力,故权利人不知新义务人不影响时效计算,也不发生时效再次起算,但可能有时效中断的问题(《诉讼时效规定》第17条)。其二,义务人合并、分立前,侵害行为已发生但因损害未确定、不知义务人等原因时效尚未起算的,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新义务人时满足本要件。因为权利人可通过工商查询等便捷方式获知义务人的最新有效信息,权利人负有此类查询义务并未不合理地增加其负担。如果新旧义务人就合并、分立后义务归属存在分歧,应自对义务归属作出认定的裁决生效之日满足本要件。[66]
2、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程度
【43】该程度是否满足时效起算要件,应以权利人凭借知道的信息能否提起诉讼为标准予以判断。一般而言,权利人须知道义务人的姓名和住所。[67]如果权利人仅知道义务人的零星信息而不足以起诉,须依据前述重大过失标准判断其是否负有调查义务,从而认定是否构成“应当知道”。例如权利人知道义务人的车牌号,由于可以据此很容易查到义务人的姓名、住址等信息,知道车牌号信息即已满足本要件。[68]又例如原告请求返还期货保证金,虽然无法准确判断承担欠款责任的最终主体,但其知道期货公司营业执照吊销之日起,即满足本要件。[69]如果权利人仅知道义务人曾用名,由于须进行难度很大的特别调查才能获知义务人完整信息,而(依据重大过失标准)权利人不负有此类较重的调查义务,因此仅知道曾用名不满足本要件。
【44】义务人是依法登记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名称即满足本要件,[70]因为权利人可据此很容易地查到其他信息。是否知道义务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具体经办人,不影响时效起算。
【45】实务中,认定不具备本要件的情形包括:第一,借款纠纷中涉及诈骗犯罪,法院及公安机关作出法律文书认定真正债务人之前,不具备时效起算条件;[71]第二,另案判决生效,确定A公司的实际托管人是B公司,此时权利人方能明确具体侵权人,此前不具备时效起算条件;[72]第三,原告虽然2008年发现煤款数额不对,但并不能确定侵害人是被告,2012年3月12日从第三人查询还款记录时才发现双方煤款结算有误,此前不具备时效起算条件[73]等。
时效起算的常见案型
(一)履行期限明确的合同
【46】该情形下,履行期限届满时义务人未履行义务的,迟延履行所生违约请求权时效起算条件此时即具备。[74]由于权利人对义务人享有期限利益的范围具有明确认知,履行期限届满时无需对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另行判断。
【47】一般场合下,如果债务履行期限明确,即使履行期限届满时债务未经清算或结算而数额尚不确定,也不影响“履行期限届满”构成时效起算点。如果合同既约定债务履行期限,又明确约定清算或结算期限,该清算或结算期限届满时义务人未履行清算或结算义务的,才具备时效起算条件。[75]因为前一场合下不存在行使权利的法律障碍,而后一场合下则相反。
【48】履行期限届满前义务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预期违约)、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瑕疵给付等)的,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违约行为时,该违约行为所生请求权时效起算条件即已具备,而无需待履行期限届满。
(二)持续性侵权
【49】此类侵权行为常发生于下列场合:持续生产或售卖侵害知识产权的产品;持续非法使用他人姓名、肖像等;持续不法占有、使用他人动产或不动产等。对于此类侵权行为所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时效起算,存在较大争议。第一种观点(统一起算说)认为,时效起算点应为“侵权行为终止之日”,因为在此之前损害尚不能确定。[76]第二种观点(区分处理说)认为,不应设置单一起算标准,而应当根据持续性侵权行为终了的不同阶段,分别确定时效起算点。因为持续性侵权行为既具有表面上的整体性,又具有实质上的阶段性和可分割性。[77]第三种观点(逐次计算说)认为,时效起算点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发生时”,时效起算超过3年后权利人起诉的,以起诉之日为起点向前推算3年,超过3年的部分损失不予赔偿。该观点是将此类侵权行为视为连续发生的多个单独侵权行为,每一个侵权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逐次计算。[7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1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18条采取该观点。
【50】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但应将“侵权行为终止”解释为时效起算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理由如下:其一,另两说将持续性侵权行为按日分割成多个独立侵权行为,既不符合普通人认知,也导致法律关系烦琐不堪。其二,持续性侵权行为随时间推移导致损害“量”的增加,而非持续产生多个不同“质”的新损害,因为每天的“新损害”与“旧损害”在类别、性质、填补对象上没有差异。其三,按照另两说的理解,每天的侵权行为产生独立的损害,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成立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因为今天的损害很可能是此前持续侵权积累的结果。其四,在非持续性侵权已完成但损害尚未确定的场合下,不起算时效系为保护权利人利益。持续性侵权行为终止前损害总额虽未确定,但应允许权利人此时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法律有特殊限制除外),否则将导致“侵权行为不终止,权利人就不能寻求救济”的悖论。赔偿数额可通过实体审理依据实际产生的损害确定,但不能据此认为此前时效已经起算。其五,比较法上,旧时多采逐次计算说,但因其在理论及实务上存在诸多弊端,逐渐被统一起算说取代。[79]据此,在一般场合下应采统一起算说为妥,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1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18条可作为知识产权领域的特殊规则予以适用。
【51】该情形不同于“侵权行为一次性完成,但损害持续发生”之情形,例如侵权人于报纸上发表侵权作品,其后数年间损害持续扩大[80]。在此场合下,受害人(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初步损害及侵权人之日时效起算。由于损害几近永不可能结束,初步损害确定即满足时效起算条件。
(三)违约金
【52】约定固定数额违约金的,时效起算点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违约金请求权成立之日”。例如迟延违约金时效起算点是合同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瑕疵给付违约金时效起算点是“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瑕疵给付的事实”等。有少数判决认为,当事人未约定违约金履行期限的,也应适用宽限期规则(《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时效起算点是“支付违约金的宽限期届满之日”。[81]该观点并不合理,因为违约金请求权作为违约责任形式,直接受诉讼时效限制,而并无适用自身履行期限的问题。[82]
【53】按日累计迟延违约金时效起算点如何认定,学理及实务上争议较大。第一种观点(单个不定期请求权说)认为,此类违约金仍为一个请求权,应统一计算时效,时效起算点是“义务人拒绝支付违约金之日”。[83]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采此观点。[84]第二种观点(多个定期请求权说)认为,持续的迟延履行构成多次违约。[85]每日所生违约金为独立请求权,应分别计算时效,义务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违约金保护范围为起诉之日前两年(当时)。[86]有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采此观点。[87]第三种观点(迟延终了说)认为,时效起算点是“履行迟延终了之日”,迟延终了包括:债务履行、拒绝履行、给付不能等情形。[88]
【5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不合理,此类违约金时效起算点应为“迟延履行的首日”。理由如下:其一,迟延违约金成立于迟延履行的首日,此时行使违约金请求权已不存在法律障碍,故应起算时效。其二,此类违约金按日累计,仅是对迟延损害的计算方法,而非意味着每日存在独立的违约行为及产生独立的违约金请求权。在义务人就迟延履行请求损害赔偿的场合下(未约定违约金),迟延履行的持续同样造成每日新增损害,权利人仍以迟延损害整体请求赔偿,损害数额结合迟延时间、范围、影响等因素认定。违约金按日累计不过是事先约定了损害计算方法,而与迟延损害赔偿性质、功能并无差异,故时效起算标准亦应相同。同理,迟延违约金为惩罚性的,按日累计构成惩罚数额的计算方法,而非惩罚多次。其三,持续的迟延履行与持续侵权行为不同:前者终止意味着债务因清偿消灭而不再有时效问题;后者终止使损害确定化,但仍有时效计算问题。因此,按日累计迟延违约金时效起算不能适用【50】处理。其四,以“迟延履行的首日”为时效起算点的可能弊端是弱化权利人保护,但由于现行法框架下较易中断时效,权利人通过中断时效获得保护更为有力。实践中此类违约金多用于商品房买卖的迟延办证场合,业主(权利人)多年后才起诉多因开发商(义务人)此前以不当、虚假承诺拖延所致,沟通过程中的行为多可认定为“诉讼外请求”“义务承认”之中断事由。如此可使权利人获得违约金全部数额,相较于权利人主张权利时仅保护三年数额,更符合“防止怠于行使权利”之制度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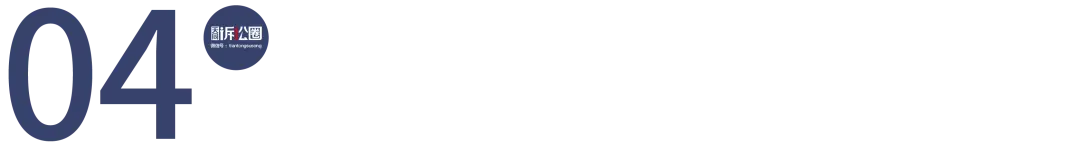
时效起算的效力
(一)起算时点
【55】对于时效起算点,第188条第2款第1句表述为“××之日”,故该时点应以日计算(《民法典》第200条)。时效起算条件具备最早之日当天不计入时效期间,次日开始计算时效期间(《民法典》第201条第1款)。
【56】上述【55】之起算时点规定的缺陷在于,很多场合下难以精确认定上述“最早之日”。为解决该困扰,有域外法规定起算时点是“发生时效起算事实的当年结束之日”[89]该做法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减轻当事人举证负担,其仅须证明时效起算条件于当年内发生即可;二是有利于保护权利人,且一定程度上弥补时效期间偏短的负面效果。我国实务上,在难以查清起算时点具体是哪一日的情形下,有法院笼统认定起算时点是“×年初”[90]“×年×月”[91]“×年×月×日之后”[92]。该做法可资赞同,因为在难以确定具体起算点(日)的情形下尽量将其延迟,并未损害义务人的时效利益,而在此情形下认为时效不起算则是不合理的。
【57】另一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权利人才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的,该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而非知道之日)为起算时点。[93]因为知道之日实体审理还未结束,有关事实及法律关系尚处于待决状态,故行使权利尚存在法律障碍。同理,权利人依据刑事侦查中获得的证据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的,刑事判决生效之日(而非知道之日)为起算时点。[94]
(二)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58】时效起算点届至的,开始计算一个完整的诉讼时效期间,期间类别依据该请求权所适用的时效期间确定。由于诉讼时效是可变期间,起算后具备中断、中止条件的,依其规则产生相应效力。换言之,“开始计算一个完整的诉讼时效期间”并不意味着该诉讼时效期间必定被“完整地计算完毕”。
(三)从权利
1、利息债权
【59】利息债权包括两种:一是“作为基本权的利息债权”,其与本金债权相互依存,从属性较强。二是“作为支分权的利息债权”,其以各期所生利息的支付为目的,具有一定独立性。[95]这两种利息均可单独约定履行期限,唯未约定履行期限时时效起算有所不同。基于“作为基本权的利息债权”之从属性,对其履行期限未作约定的,随本金债权时效起算而起算。[96]基于“作为支分权的利息债权”之独立性,其时效起算与本金债权时效起算分别认定,[97]故应适用宽限期规则(《诉讼时效规定》第4条)单独确定其时效起算点。
2、担保权
【60】保证债权虽与受担保债权构成从主关系,但因《民法典》第694条对其时效起算标准有特殊规定,故于时效起算上并不遵循从随主规则。
【61】《民法典》第419条规定,行使抵押权应于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为之。有实务意见将其解释为,抵押权行使期间是一种独立期间(司法保护期),“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仅是其计算标准,两种期间分别计算。[98]该观点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44条第1款所否定。依该款规定,《民法典》第419条的规范含义是主债权时效届满后抵押人可援引主债权时效抗辩权对抗行使抵押权的行为,而并不存在“独立的”抵押权保护期间,[99]因此也无该期间单独计算(起算)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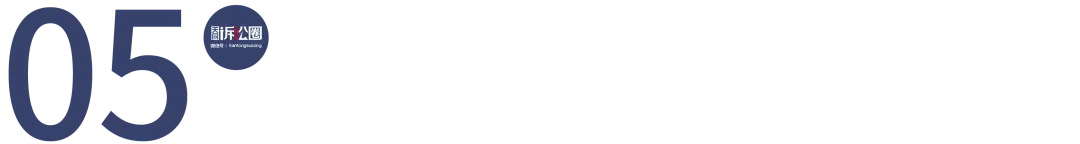
举证责任
【62】原告(权利人)起诉时仅须证明权利有效存在,而无须主动证明时效未届满及时效起算点。在当事人未提及时效事项的情形下,法官不得主动依职权对时效起算作出认定。具体而言:其一,被告提出时效抗辩之前,原告对时效起算不负举证责任。其二,被告援引时效抗辩权的,应就时效起算各要件事实予以举证证明。其三,原告对时效起算提出异议并由此否认被告时效抗辩的,须针对有异议的起算要件举证以证明时效未届满。
【63】权利人采取公证方式保全证据的,如果义务人不能证明此前权利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的,法院通常认定时效起算点是“公证保全之日”。例如:第一,权利人委托代理人公证购买被诉侵权产品的时间被认定为时效起算点;[100]第二,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中,著作权人公证取证之日被认定为时效起算点[101]等。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办理公证前权利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的,可推翻该认定。[102]
注释:
[1] 参见冯恺:《诉讼时效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2] 此类客观时点包括“权利可行使之时”(《意大利民法典》第2935条)、“损害被确定之时”(《法国民法典》第2226条)、“请求权发生之时”(《阿根廷民法典》第3956条)等。
[3] 此类主观时点包括“知道损害和义务人之时”(《葡萄牙民法典》第498条)、“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时”(《俄罗斯民法典》第200条)等。
[4]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9条;《日本民法典》第166条。
[5]Vgl.Helmut Grothe,Kommentar zum § 195,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8.Aufl.,München:C.H.Beck,2018,Rn.3.
[6] 参见[日]潮见佳男《民法(债权关系)改正法の概要》,金融财政事情研究会2017年版,第46、47页。
[7]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03页。
[8]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3页。
[9]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1页。
[10] 参见朱晓喆:《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基础与规范表达》,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3期,第708页。
[11] 参见房绍坤:《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4期,第8页。
[12] 参见张雪楳:《诉讼时效审判实务与疑难问题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
[13] 参见朱虎:《诉讼时效制度的现代更新——政治决断与规范技术》,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第93页。
[14] 参见[奥]海尔姆特·库齐奥主编:《侵权责任法的基本问题》(第二卷),张家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734-736页。
[15] 参见[日]鈴木銀治郎、滝口博一、椿原直:《时效の法律相談》,青林书院2018年版,第97页。
[16] 2017年修正前的《日本民法典》第166条第1款采否定说,但修正后该款改采肯定说。该变化是将侵权时效起算的主观标准上升为一般标准,以强化权利人保护。
[17] 我国台湾地区主流意见采否定说,但为克服该说所生诸多弊端,实务上多设例外处理。参见陈聪富:《论时效起算时点与时效障碍事由》,载《月旦法学杂志》2019年第2期,第10-11页。
[1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122页。
[19] 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5页。
[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949页。
[21] 不同观点,参见张雪楳:《诉讼时效审判实务与疑难问题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80页。
[22] 参见杨巍:《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衔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38页。
[23] 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61页。
[24] 参见房绍坤:《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4期,第8页。
[25]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4页。
[26] 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91页。
[27]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吉民再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
[28]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0号民事判决书。
[2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0)民终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
[30]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再1126号民事判决书。
[31] 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民终545号民事判决书。
[3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504号民事判决书。
[33]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再426号民事判决书。
[34]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二终字第77号民事判决书。
[3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二终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书。
[36]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终618号民事判决书。
[37]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再142号民事判决书。
[38]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3页。
[39] 参见注16,第72页
[40] 相反的意见,参见房绍坤:《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载《法学论坛》2017年第4期,第8页。
[41] 参见石一峰:《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136页。
[42] 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终543号民事判决书。
[43]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终160号民事判决书。
[44] 参见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陕民三终字第00025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参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云高民三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
[45] 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辽民三终字第99号民事判决书。
[4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948页。
[47] 参见崔建远等:《民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1页。
[48] 参见张雪楳:《诉讼时效审判实务与疑难问题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页。
[49]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53页。
[5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51]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545号民事判决书。
[52] 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5页;麻昌华、陈明芳:《<民法典>中“应当知道”的规范本质与认定标准》,载《政法论丛》2021年第4期,第128页。
[53] 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83页。
[54] 参见石一峰:《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144页。
[55]Vgl.Helmut Grothe,Kommentar zum § 195,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8.Aufl.,München:C.H.Beck,2018,Rn.31.
[56] 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民终743号民事判决书。
[57] 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民再435号民事判决书。
[58]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民终1786号民事判决书。
[59]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闽民终字第706号民事判决书。
[60]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沪高经终字第335号民事判决书。
[61] 参见注16,第73页。
[62]Vgl.Helmut Grothe,Kommentar zum § 195,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8.Aufl.,München:C.H.Beck,2018,Rn.29.
[63] 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监三再终字第00021号民事判决书。
[64]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释评·总则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86页。
[65]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6页;参见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5页。
[66] 参见张雪楳:《诉讼时效审判实务与疑难问题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177-178页。
[67] 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释评·总则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86页。实例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知民终字第0177号民事判决书。
[68] Vgl.Helmut Grothe,Kommentar zum § 195,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8.Aufl.,München:C.H.Beck,2018,Rn.35.
[6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书。
[70] 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91页。
[71] 参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终143号民事判决书。
[72] 参见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津民终608号民事判决书。
[73] 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50号民事判决书。
[74] 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1页。
[75] 参见吴宝庆:《准确起算诉讼时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11期,第7页。
[76] 参见张雪楳:《诉讼时效审判实务与疑难问题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76页;参见崔建远等:《民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84页。
[77] 参见李群星:《论持续性侵权之债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1期,第78-79页。
[78] 参见廖志刚:《专利侵权诉讼时效研究》,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第179-180页。
[79] 参见[日]酒井廣幸:《損害賠偿請求における不法行为の时效》,新日本法规出版株式会社2013年版,第142-145页。
[80]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终1134号民事判决书。
[81]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民终字第00336号民事判决书。
[82] 参见姚明斌:《<合同法>第114条(约定违约金)评注》,载《法学家》2017年第5期,第165-166页。
[83] 参见韩世远:《商品房买卖中的迟延损害、违约金与时效》,载《法律适用》2010年第11期,第22-23页。
[8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8年第2期。
[85] 参见姚明斌:《违约金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页。
[86] 参见陈嘉贤:《按日累计的违约金请求权诉讼时效何时起算》,载《人民司法》2011年第22期,第82-84页。
[8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030号民事裁定书。
[88] 参见郗伟明:《论迟延履行违约金诉讼时效的起算》,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第84页。
[89]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99条第1款第1项。
[90] 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再183号民事判决书。
[9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
[92] 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皖民终560号民事判决书。
[93] 参见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民终590号民事判决书。
[9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662号民事判决书。
[95] 参见刘勇:《<民法典>第680条评注(借款利息规制)》,载《法学家》2021年第1期,第171页。
[96]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书。
[97] 参见林诚二:《民法债编总论———体系化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
[98] 参见曹士兵:《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版,第303页。实例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9567号民事判决书。
[9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397页。
[10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终216号民事判决书。
[101]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1147号民事判决书。
[102] 参见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终1326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