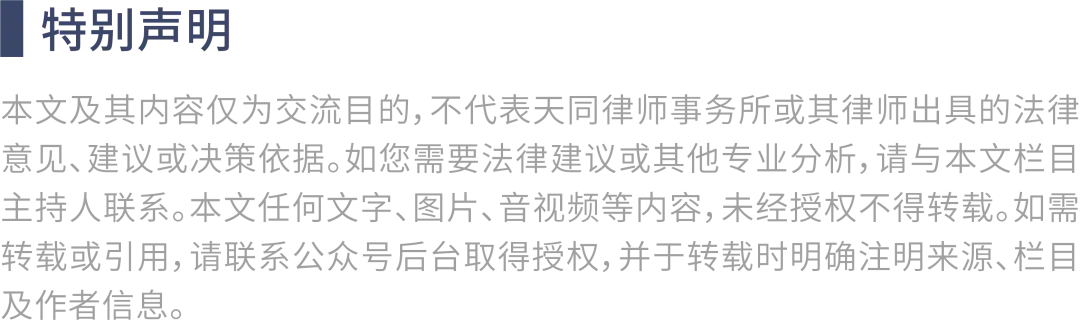本文共计22,976字
作者按语:物上之债指向那些“跟着物跑”的债,常见形态是物上债务,比如,A的房屋为B的房屋设立地役权,约定A在墙壁上加装隔音板,该约定随地役权一并登记,之后A把房屋转让给C,C又转让给D,C、D均有该义务,这种义务就是物上债务。物上之债既有债的属性,仅针对或B或C或D这样特定人,又有物权属性,突出表现为根植于特定客体,需由法律规定并要公示。
物上之债是德语“Realobligation”的汉译,但它并非德国民法术语,而是瑞士民法术语。物上之债在法国法系广泛存在,在德国法系是另类,似乎只有瑞士民法学理将其体系化,它在瑞士物权法教科书中是与物权地位相同的基础概念。在汉语法学界,苏永钦老师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引入物上之债,并持续运用于加工、相邻关系、地役权、物权法定与自由、物权与债的关系、民法典结构等研究当中。但因关注重点不同,苏老师并未专门对物上之债加以展开,以至于我在读后仍有朦胧之感。2007年恰好有到瑞士访学的机会,趁机向Fribourg大学的Peter Gauch教授请教。记得那个寒夜在教授家晚餐后,教授讲了制度的概貌,其夫人Bettina还拿出瑞士民法典指出相应的地方。
后来,教授和其同事Hubert Stoeckli教授陆续向我提供了有关学术资源。在此基础上,几年之后,我完成这篇小文的写作,既解开了自己的心头之惑,也算是对Peter夫妇和Hubert的致谢。小文在阐述瑞士物上之债的基础上,主要通过与德国债的物权化的功能对比,表明物上之债的价值,并主张我国应引入这个概念。当然,概念大多是现实的理论反映,虽然物上之债在我国尚不是教科书的基本概念,但无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受让人要承受原权利人在出让合同中的义务(如配建幼儿园、菜市场)的现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2条),还是可登记的合同约定(如《民法典》第406条限制抵押财产转让的特约等),都可归为物上之债的范畴。就此而言,深入了解物上之债,进而深入思考合同对第三人效力的机理,是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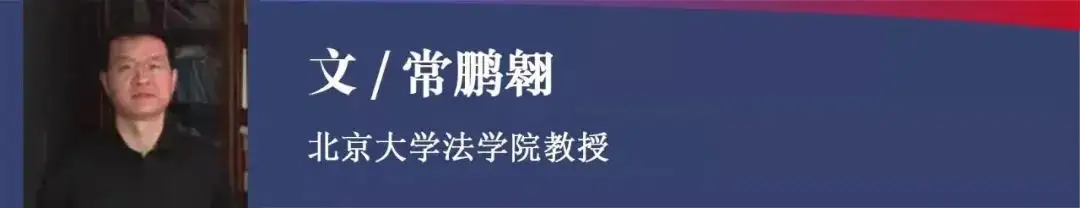
注:本文发表于《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内容提要:物上之债是瑞士民法学理概念,它指向那些既有相对性,又能约束物权受让人的债。从产生依据上看,物上之债有法定和意定之分,无论是哪一类,物上之债通常与物权并存,并遵循法定原则、公示原则等物权法基本规范。物上之债与债权物权化的功能十分相似,但两相对比,物上之债的学理共识度更高,更易于学习和传授,更有解释力,规制机制更简单,比债权物权化更具有学理优势。基于该优势,并考虑我国民法学理对债权物权化尚未形成高度共识,再加上我国有不少与瑞士物上之债相似的法律规范,物上之债对我国有切实可行的借鉴作用。在借鉴时,重点参照意定物上之债,改进我国的预告登记制度,将其适用范围扩及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与物权相关的债。
关键词:债权与物权的区分 物上之债 债权物权化 法律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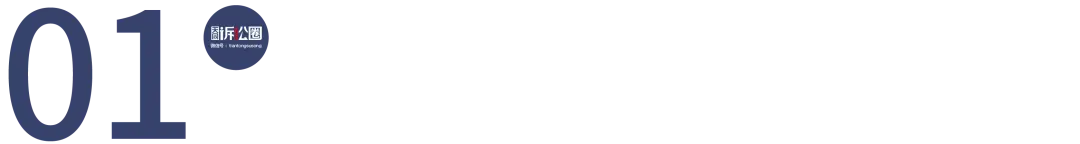
引言
受德国民法的影响,包括我国在内的不少法域,均把债权和物权的二分作为民事财产权规范的基石,债法和物权法因此有了不可跨越的鸿沟。单就权利界分的单一维度而言,债权与物权看上去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权利,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无论在体系化的民法规范脉络里,还是在现实交易实践中,债权与物权有着面相不同的多重动态关联,其中之一是融合和并存,即有这样的一类债,其主体与物权人为同一人,如 A 因通行 B 的土地而对 B 负有支付费用的债务,在 B 的土地所有权移转给 C 后,C 成为 A 的债权人,从 C 处受让土地的 D 同样是 A 的债权人,这种债往往与物权并存,如 A 的债务与其通行的土地所有权并存,它就是瑞士民法学理中的物上之债( Realobligation) 。[1]
从知识继受的角度来看,我国民法学深受德国影响,而物上之债与德国民法学无缘,也因此是我国学界相对陌生的概念。不过,我国学者对物上之债及其所指的现象早有留意。在我国台湾地区,苏永钦教授 1991 年于大作《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中就借力瑞士学理简要阐述了物上之债,[2]后在《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可登记财产利益的交易自由》等作品中又反复提及。[3]
在我国大陆地区,王利明教授借助法国学理提出物权债务( real obligations) ,仅从其阐述的该债务伴随物权存在、与物不可分离等内容来看,[4]物权债务与物上之债并没有实质差别。物上之债在不同侧面分别体现出债和物权的部分特性,无法把它单纯地归为债或物权,这种特殊的法律现象显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民法学知识,无论是出于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理论好奇,还是出于衡量其对我国有无参考和借鉴价值的实用考虑,均有必要借助瑞士文献资料对它进行较全面的论述。目前我国没有以物上之债为主题的专门论述,上述的引注文献也只是局部涉及物上之债的若干方面,它无疑是个知识缺口。[5]
为了填补这个缺口,本文第二、三、四部分将根据新近的瑞士民法学理,对物上之债的概貌、类型和特质进行描述,以期展示相对完整的物上之债信息。物上之债的上述独特性,会让人自觉不自觉地想到同样游离于债权和物权之间的债权物权化,感觉其二者何其相似。源自德国民法学的债权物权化早已深植于我国民法学, 为法科人士所熟知,在路径依赖的心理惯性下,它能否替代或容纳物上之债,是相当自然的疑问。这个问题事关探讨物上之债的价值和意义,因为一旦答案肯定,即便能详尽清晰地勾勒物上之债的面目,也无非是在画一朵不能长在本土的异域之花,它在我国的实际意义近乎于无,若答案否定,则物上之债要么是债权物权化不及之处的补充品,要么能盖过债权物权化的风头而唱独角戏,其意义将不同寻常。故而,在明了物上之债构造的基础上,本文第五、六部分还将把它与债权物权化进行对比分析,以进行功能性的优劣评价,并探讨物上之债对我国学理和制度的可借鉴意义。
物上之债的理论概述
遍览《瑞士民法典》的物权编,它除了涉及物权类型、内容、公示、变动等物权规范,还有不少与债有关的规范。比如,第 647 条第 2 款第 1 项规定,为了保护物的价值及其使用性能,每一共有人都有请求为必要管理措施的权利,[6]这种请求权是债权。又如,根据第730条第 2 款第 1 句,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只能以次要地位而附加于地役权,这种义务属于债务。这些债具有以下共性:第一,与物权并存,如上述共有人的债权与共有并存,供役地所有权人的债务与地役权并存; 第二,债的主体与物权主体重合,如共有人是债权人、供役地所有权人是债务人;第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时,物权转让同时导致债的移转,如第730 条第 2 款第 2 句特别规定,作为义务记入土地登记簿的,需役地或供役地所有权的取得人受其约束。
简言之,上述债的特性在于,谁是物权主体,谁就是债的主体,二者高度一致。比如,A 用自己房屋为 B 设立地役权,约定 A 有义务在地板上铺设隔音地毯,该义务就属于第 730 条第 2 款第 1 句规定的作为义务,在它登记后,A 把房屋转让给C,C 也有这种义务,从 C 处受让房屋的 D 同样如此。显然,此类债不同于债法调整的买卖合同等普通之债,后者存于有特定人格和身份的主体之间,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即便第三人从当事人处受让标的物所有权,也不能成为合同当事人。对比而言,物权编中的上述债虽然也因相对性而指向特定主体,但其不注重主体的人格和身份,而是以标的物为媒介,把该物的任一物权人作为债的主体,如对债权人 B 而言,只要供役房屋这个客体存在,其所有权人无论是 A、C 或 D,均为债务人,故称其为物上之债,以区别于债法规定的普通之债。
在瑞士,债(Obligation)是一种法律关系,内含了债权(Forderung)与债务(Schuld)。[7]与此对应,物上之债也有物上债权(Realforderung)和物上债务(Realschuld)之分,且这种区分有其独特意义。与普通之债相比,物上之债最独特之处虽然是其主体与物权主体保持高度重合,但也有例外。比如,根据第837条第1款第3项,工匠为建筑工程提供劳力和原材料,或单纯提供劳力,由此产生的债权受到以建筑工程所在的土地为标的的法定抵押权的担保,工匠有请求登记该抵押权的权利,这种请求权是物上之债,在此,作为债权人的工匠并非该土地的物权人。也就是说,尽管物上债权和物上债务相对应,但它们的主体未必对应的均是物权人。基于这种差异,就不宜把Realobligation译为物上债权或物上债务,只宜译为物上之债,从而既能与其字义保持一致,又能把债权人并非物权人的情形涵括进来。[8]
在形态上,物上之债包括债权和债务;此外,根据通说和实务,特定情形下的形成权也被纳入其中,这主要表现在第 959 条第 1 款,该款规定: “法律规定的可预告登记的对人权,如先买权、买回权、购买权、用益租赁和使用租赁,可在土地登记簿中为预告登记。”对人权对应着德语 personenliche Rechte,它在瑞士民法学中与仅对特定人发生效力的相对权同义,是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等绝对权的对立概念,既包括先买权、买回权、购买权等形成权,也包括租赁等债权。[9]
在预告登记时,作为形成权的先买权、买回权、购买权也被归为物上之债。[10]在主体上,物上之债的主体可能是所有权人,如供役地所有权人是作为义务人;还可能是限制物权人,如第778条第1款规定,居住权人独自使用居所的,要支付居所的通常维修费用,居住权人就是支付费用的义务人;还可能是占有人,如第720-721条规定拾得人有保管和通知义务,占有遗失物的拾得人就是义务人。由于非物权人的占有人成为物上之债主体的情形较为少见,而债权人有时也不是物权人,故在界定物上之债时,瑞士学理和实务的用词相当谨慎,通常会说,物上之债与某物的物权并存,在特殊情形下会与占有并存,并像物权或占有一样依附于该物,以至于债务人——以及通常情形下的债权人——与物权人或占有人完全重合。[11]
在产生上,物上之债有法定和意定之分。《瑞士民法典》物权编的许多规范直接规定了物上之债,它们的产生无需借助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创意,这类物上之债属于法定的物上之债。此外,物权编还允许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来设立物上之债,它们属于意定的物上之债。这两类物上之债构成物上之债的主干,它们是下文第三部分的讨论对象。在效力上,物上之债能约束标的物上的任一物权人或占有人,这使它与普通之债得以区别的标志,前述的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就是典型,在此不赘。在功能上,物上之债旨在填补债权与物权二分的不周延之处,即这种二分及与其相伴的物权法定有力所不及的地方,导致法律生活的诸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物上之债通过把债务人的积极给付与物权或占有结合的方式,把债权要素和物权要素整合起来,从而能填充债权与物权二分的空隙,[12]这也正是它在瑞士民法学理中得以生成的根本原因。
物上之债在瑞士不是实证法术语,而是由学者发展出来的法学概念。至于其缘起,瑞 士学理认为是通过回溯共同法有关特定事实之诉[13]的学说,并参酌法国、意大利一些学者的学说发展而来的,彼得·利沃尔( Peter Liver) 是其主要推手,后来得到学理和实务的普遍认可;[14]此外,于 20世纪 50 年代论述该概念的阿瑟·约斯特( Arthur Jost) 也是先驱人物。[15]
在瑞士民法学理中,早于物上之债使用的概念是subjektiv-dingliche Rechte和subjektiv-ingliche Pflicht,[16]前者可意译为主体物化的权利,后者可意译为主体物化的义务。为了说明它们的特点,下面以地役权为例展开阐述。地役权是典型的主体物化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实现需役地的客观利益,这种利益不为地役权人的个人利益和主观认识所左右,在这种客观限制下,无论谁是需役地所有权人,只要他以通常方式实现需役地的效用, 成为地役权人就是其最佳选择,即需役地上任一所有权人均为地役权人。比如,为了灌溉 A 的耕地,需在接近水源的 B 的地上开挖水渠,双方由此设立取水地役权,A 以及从其处受让需役地的任一所有权人均为地役权人。由此可知,诸如需役地这样的特定标的物于此不仅是客体,还遮蔽了物权主体的具体人格和身份,成为物权主体的标志,就此可以说物权主体的具体人格和身份被抽离,有了物化的因素,具备这种特性的权利就是主体物化的权利。与此相应,主体物化的义务就是义务主体与特定物的物权主体一致的义务。
由上可知,主体物化的情形不仅涉及债,还涉及地役权这样的物权,这就不容易把纯粹的物权与融合债权、物权特性的法律地位区分开来。再看物上之债,其德语Realobligtion是由Real 和 Obligation 这两个词组合而成,其表达既简洁又意蕴丰富,因为作为词根的 Obligation 指向债,这一定位使得物上之债被归为对人权的范畴,而作为限定词的 Real 包含了物权要素,这使物上之债作为特殊的债而有别于其他债,从而简要而醒目地显示出物上之债与物权的关联。[17]从表达上看,主体物化的义务不如物上之债明晰,后者因此成为瑞士民法学的通行用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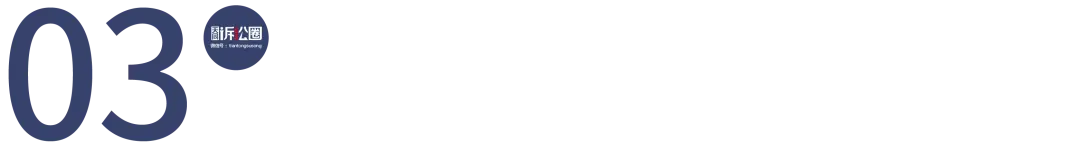
物上之债的基本类型
1. 规范布局
从《瑞士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布局上看,法定的物上之债在第一分编所有权中居多,主要涉及以下领域: ( 1) 共有关系,如第 647 条第 2 款第 1项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物有进行必要管理的义务等; ( 2) 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如第 669 条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有划定相邻界限的协力义务等; ( 3) 土地所有权内容的限制,如第 694 条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有为邻地所有权人设定通行权的义务等; ( 4)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如第 712a 条第 3 款规定所有权人有维修专有部分的义务等; ( 5) 动产所有权,如第 720 - 721 条规定拾得人有保管和通知义务等。
第二分编限制物权也规定了法定的物上之债,主要涉及以下领域:(1)地役权,如第741条规定地役权人有维修行使地役权所需设施的义务;(2)用益权,如第755条第2款规定用益权人有管理用益权标的物的义务;(3)居住权,如第778条第1款规定独用居所的居住权人有负担通常维修费用的义务;(4)建筑权,如第779d条第1款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因建筑权消灭而取得建筑物所有权的,有向原建筑权人支付合理补偿金的义务;(5) 不动产抵押权,如第 837 条第 1 款第 3 项规定的请求土地所有权人设立法定抵押权的权利。第三分编的占有中也有法定的物上之债,如在权利人请求占有人返还占有物时,第939条第 1 款规定,善意占有人有请求权利人支付必要费用或有益费用的权利; 第 940 条第 2 款规定,恶意占有人有请求权利人支付必要费用的权利。[18]
上述的规范布局表明,物上之债是瑞士民法在设置物权规范时的重要关联要素,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债务人的积极给付行为能有效地纠正因物权配置而引发的利益失衡,取得建筑物所有权的土地所有权人向建筑物原所有权人支付合理补偿金、土地所有权人为工匠设立法定抵押权等义务,[19]无不如此。
此外,它还能把物权人对物的支配或用益框定在合理限度内,从而给物权的行使设置必要的限制,以恰切地照料利害攸关方的合理利益,为邻地所有权人设定通行权的义务就是典型,即土地所有权人不能用己方所有权来扼杀袋地所有权人的通行利益,由此产生的损失当然要由袋地所有权人合理补偿; 地役权人维修行使地役权所需的设施、独用居所的居住权人负担通常维修费用等义务,也体现了这种功能。
再者,与独有不同,共有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是多数权利人因物而聚所形成的物权形态,其中不仅有人对物的支配利益,还有为保持物的效用最大化所形成的权利人共同体利益,故法律除了设置人支配物的规范,还要配置权利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以预防或化解可能的人际冲突,为共有或区分所有状态的有效持续或合理分解提供必要通道。比如,通过设置权利人对共有物进行必要管理的协力义务,任一权利人均有请求其他共有人管理的权利,且该权利既不能放弃,也不能被剥夺,[20]这就能确保权利人在共有物管理方面有平等的发言权,使权利人能在共有物管理上实现自治。
2. 构造要点
首先,法定的物上之债源自法律规范,法律是其存续的根本,在判断它是否产生时,要先看有无相应的法律规范。不过,即便有相应规范,也不能得出肯定结论,因为物上之债的法律规范可能是任意规范,一旦当事人约定排除或改变,就没有物上之债可言,故还要看当事人有无这种约定。鉴于物权编有关法定的物上之债规范大多为任意规范,[21]这一步的甄别就显得格外必要。由于物上之债依托于物权或占有,后者是其得以存续的实体基础,故只有后者现实发生,物上之债才能产生。通过上文对法定的物上之债的例举,可知只有个别物上之债涉及 动产物权或占有,其他均与不动产物权有关。在瑞士,依法律行为的不动产物权变动需登 记,该登记时点就是相关的物上之债的产生时点; 非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无需登记,当相应的要件满足时,物上之债也现实发生。[22]其次,法定的物上之债现实发生后,应根据相应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内容,对此要遵循法律解释的方法,既注重法律规范的文义,又尊重学理和实践对其意义的理解和运用。[23]
1. 基本形态
意定的物上之债由法律限定其类型,当事人只能在其中选择,不能超越这些类型范围自由创设。根据是否仅由物权编加以调整,意定的物上之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物上之债完全由物权编调整,它以提供物或劳务为给付内容,而该义务由特定土地的任一所有权人负担。地役权规范中就有这类物上之债的典型例子。比如,地役权的基础规范为第 730 条,该条第 1 款把供役地人不作为当成地役权应秉持的原则,第 2 款则有例外,即允许当事人约定供役地人有作为义务,前述的用以供役的房屋所有权人在地板上铺设隔音地毯的义务就是适例。又如,第 741 条第 1 条款规定地役权人有维修行使地役权所需设施的义务,这是任意规范,当事人可约定改变,如变为地役权人有支付维修费用的义务。[24]
另一个典型是第782-792条规定的土地负担。根据第782条第1款,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负担权利人负有给付义务,且仅以该土地为限承担责任,其中的给付义务通常表现为积极作为,如对牧场或堤坝的维护义务、水源地所有权人的供水义务、林地所有权人提供木材的义务。根据第792条第1款,从承载土地负担的土地所有权人处受让该土地者,自动成为土地负担的债务人,基于债务人通过土地所有权来确定的这一特性,土地负担就是物上之债。[25]
由于土地负担由当事人约定产生,故它也是意定的物上之债。与狭义的物上之债相比,依据第959条通过预告登记而在土地登记簿中记载的对人权属于广义的物上之债,因当中的大多数权利被债法的有名合同规范所调整,如债法第216a 条规定的先买权等权利、第 261b 条和第 290 条规定的租赁、第 247 条规定的赠与人撤销权等,它们通过预告登记显示出物上之债的特性,即能对抗负载预告登记的土地的任一所有权人。就这些物上之债的绝大多数而言,当事人负担的积极给付义务是提出登记申请,对待给付义务通常为支付价金。以先买权预告登记为例,在土地所有权转让条件确定时,即在同一条件下,先买权人有权申请登记为土地的新所有权人,同时对负载预告登记的土地所有权人有对待给付义务。需要注意的是,预告登记的对象不限于债法规定的对人权,还及于物权编规定的意定权利,如在同一土地上承载多个先后顺位抵押权的情形,根据第 814 条第 1 款,先顺位抵押权消灭,后顺位抵押权的顺位保持不变,但第814 条第 3 款允许当事人约定改变,并在土地登记簿中进行预告登记后,使后顺位抵押权在先顺位抵押权消灭时能够升进。[26]
2. 构造要点
首先,意定的物上之债能否现实发生,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故而,只有当事人通过约定在法律规定的类型中加以选择,才能为意定的物上之债提供产生的契机。这意味着,当事人的约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以第 730 条第 2 款规定的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为例,当事人只有在地役权合同中或在地役权产生后约定这种义务,才可能使其 成为物上之债,在买卖合同等其他合同中约定内容完全相同的义务,也只是普通之债。这 种约定还需符合法律行为生效要件,自不待言。不过,上述约定不能直接产生物上之债,在法律把登记作为其产生要件时,只有记入 土地登记簿,上述约定才是物上之债。预告登记固然如此,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也不例外,第 730 条第 2 款第 2 句强调它要在登记后,才能对抗供役地或需役地的受让人; 改变行使地役权所需设施维修义务内容的约定也一样,第 741 条第 2 款强调它们要在土地登记簿的证据资料中显示,才能对抗供役地或需役地的受让人。[27]
其次,在法律规定的框架范围内,当事人可自由形成意定的物上之债的内容,如只要 不背离地役权的主要功能,当事人可约定供役地所有权人的作为义务的具体内容,预告登记的对人权的内容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意定的物上之债的具体内容取决于意思表示,在理解时应遵循意思表示的解释规范。
最后,就预告登记而言,其对象是不同的对人权,它们各有规范基础,当这些权利因其规范基础所设定的条件而消灭时,意定的物上之债也就无从谈起。比如,根据债法第216e 条,先买权人应从知道买卖合同订立及其内容之日起 3 个月内行使先买权,否则,该权利丧失。又如,根据债法第 216a 条,当事人可约定最长不得超过 25 年的先买权,先买权人在此期限内未行使先买权的,根据民法第 976 条第 1 款,无需先买权人的协力,土地所有权人即可申请注销该预告登记,登记机构也可主动依职权注销该预告登记。[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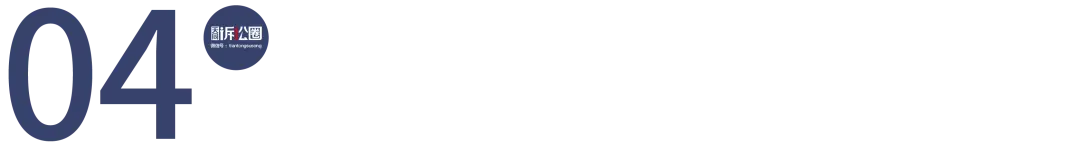
物上之债的主要特质
债权和物权的二分,虽然大致能把民事财产权区隔为非此即彼的两部分,但也存在缝隙地带,物上之债就是用以概括这些地带的法学概念,它能有机地把债的属性和物权属性融为一体,这是其最主要的特质。
1. 债的属性首先,物上之债具有相对性,仅在特定主体之间有约束力,不像物权那样有绝对性。 正如前文所言,物上之债的主体一般是标的物的任一所有权人,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其他人不受制于物上之债。其次,物上之债具有以请求权为中心的关系构造,不像物权那样是支配权,据此,为了实现债权,债务人必须为给付行为,即便它不涉及标的物,也不会影响该给付义务属于物 上之债,这是物上之债在本质上不是物权的表现。[29]根据物权编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大致包括以下形态:
( 1) 提供劳务,如第 669 条规定,在土地界限不清的情形,应邻地所有权人的请求,土地的任一所有权人都有义务协助定界;
( 2) 提供实物,如在土地负担, 土地所有权人有向土地负担权利人提供土地产物的义务;
( 3) 发出意思表示,如土地所有权人申请法定抵押权登记的义务;
( 4) 支付金钱,如独用居所的居住权人支付通常维修费用的义务。[30]
需要说明的是,通说认为物上之债的内容限于上述积极的给付义务,但也有个别见解指出,债务人的容忍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也应包括在内,前者如对上游来水的接受和排导,后者如不能让建筑粉尘危及邻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消极容忍和积极作为的界限往往不甚明晰,难以清楚地确定,而针对债务人的不作为请求权也常常能达到防御性保护的 效果。[31]再次,物上之债遵循债法规定的债的效力规范。比如,因土地所有权转让导致受让人承担债务的,受让人应适当履行债务,否则将承担损害赔偿等责任。举例说明: A、B 相邻,A 有维修隔墙的义务,但他未履行该义务,后他将土地转让给C,C 仍要履行该未竟的义务,B 对 C 也有相应的请求权; 在 C 仍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时,B 可对 C 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32]
又如,以支付金钱为内容的物上之债的履行,受制于诉讼时效,如第 649 条第1 款规定共有人有义务分担管理费,第 2 款规定某一共有人支付的费用超出应担部分的,可向其他共有人请求相应的补偿,该补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10 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33]最后,与普通之债一样,物上之债也能成为登记基础。以抵押权登记为例,在旨在担保借款等主债权的意定抵押权,登记基础是产生普通之债的抵押合同;在法定抵押权,登记基础是请求土地所有权人设立法定抵押权的请求权。[34]
2. 物权属性
首先,物上之债是主体物化的债,特别是在债务人与所有权人完全同一的情况下,它 如同物权一样粘附在特定标的物上,波及该物的任一所有权人,结果就是物上之债随着所有权移转而移转。这样一来,适用普通之债的债务承担和债权让与规范就无适用余地。 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仍以 A 有维修隔墙的义务为例,它依附于 A 的土地,A 把土地所有权移转给C,只是说 A不再负担维修义务,C 则在受让所有权时原始承担该义务,此时无需邻居 B 的同意。至于 A 因迟延履行维修义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不再是物上之债,而是 A 个人的普通债务,仍由其向 B 承担。从债权人的角度来看,在 A未转让土地的前提下,B 把己方土地所有权移转给 D,D 在受让后就原始取得请求 A 维修隔墙的权利,此时B也无需通知 A。[35]其次,物权离不开特定标的物,没有这种客体,就没有物权。物上之债同样如此,没有特定的标的物,就不可能有物权人,当然也就不会有债的主体,故而,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物权客体的灭失在消灭物权的同时,对物上之债的存续也有釜底抽薪的作用。[36]
最后,瑞士的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不能用于物权,[37]而在物上之债,除非它以支付金钱的给付义务为内容,否则就不受制于诉讼时效。[38]对此,或者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如第 790 条第 1 款规定土地负担不适用诉讼时效,或者在法律未明文规定时,有学理和实务的共识,如第 650 条第 1 款规定,共有人有终止共有关系的请求权,它也不受制于诉讼时效。[39]概括而言,物上之债具备债的基本属性,这使它不同于物权;但它依附于物权,特定标的物上的任一物权人就是债的主体,这使其看上去与物权一样根植于特定标的物之上,具有明显的随物定其命运的属性,这又不同于普通之债。正是在此双重否定中,物上之债交融了债和物权的部分属性,具有填补债权与物权二分缝隙的作用。
作为债的一类,物上之债虽然要受债法的调整,但其根基在物权法,没有物权法的规 制,就不可能有物上之债,故而,物上之债要遵循法定原则、公示原则等物权法基本规范。 首先,物上之债的类型只能由物权法规定,这是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这意味着,除了基于物权法规定的要件而直接产生的物上之债,当事人自行创设物上之债的空间很窄,只能在物权法规定的类型中加以选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物上之债把标的物上的任一物权人均作为债务人,这种对抗性和穿透力是普通之债所不能比拟的,为了规避由此给第三人可能带来的风险,就需为物上之债设定合理、确定且明显的范围,对此只有通过物权法才能完成。显然,把物上之债纳入法定原则的适用对象范围,不是来撼动以债法和物权法的区分为基础的财产法秩序,反而是扩展这种秩序。以下例子能说明法定原则对物上之债的限制:(1)只有法律规定可预告登记的对人权才能预告登记,诸如优先通行权、优先交换权、优先承租权、预约合同等法律未允许预告登记的权利就被排除在外;(2)不能通过物上之债来对土地为所有权保留;(3)第644-645条规定了主物和从物及其关系,把它们均限定的物的范畴,这样就不能借助物上之债在物和权利之间,或在权利之间设置主从关系;(4)不能通过物上之债来设定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共有;(5)不能通过物上之债把设定或行使地役权的对待给付义务作为物权内容。[40]此外,根据债法第 261 条第 1 款,出租人在租赁合同成立后转让租赁物的,租赁关系依法由租赁物的新所有权人承受。在此,租赁合同的约束力延及租赁物的受让人,这看上去与物上之债的效力没有差别,[41]但其规范基础不在物权法,故租赁合同不是物上之债。[42]
其次,物上之债有波及和约束新物权人的效力,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当它以土地为标的物时,登记的公示机制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上文所言,多数物上之债的产生均要以登记为要件,在此基础上,先登记的意定的物上之债占据优先地位,能排斥后登记的物上之债或限制物权。[43]再者,登记的物上之债比未登记的普通之债有更强的效力,这一点在租赁合同上有突出表现。前文已说,未预告登记的租赁合同能约束租赁物的新所有权人,但根据债法第 261条第 2 款,新所有权人有权在法定条件下终止租赁关系,如该款第 1 项规定,在租赁物为住房或营业用房时,为了自己、近亲或姻亲的个人急需,新所有权人可基于法定的终止期限,于最近的法定期日终止租赁关系。而通过预告登记,租赁合同的效力得以增强,结果就是在租赁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新所有权人有义务允许承租人按 照约定使用租赁物,而不能根据债法第 261 条第 2 款的规定来终止租赁关系。[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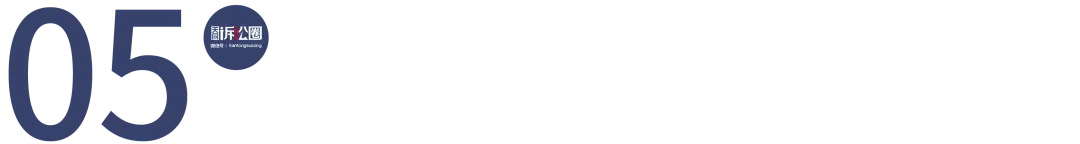
瑞士和德国均把债权和物权的二分作为民事财产法的根基,且它们的立法、学理及司 法对债权和物权内涵的认知没有差别,而这种二分没有全面覆盖性,无法对所有的民事财产权进行非此即彼的区隔,对第三人有约束力的债权就是这种二分不彻底留下的缺口,它点明了无法单为债权或物权完全含括的异形地带。在学理上如何描述和定性该缺口,是两国共同面对的问题。对此,瑞士用物上之债来应对,德国则采用了债权物权化,它们的功能无疑高度重叠。
既然如此,抛开各自的语境限定,把物上之债和债权物权化放在继受或移植的平台上 进行鉴别,究竟何者为优,就是我们这些域外法科人士更关注的问题。换言之,若我们已相当熟悉的债权物权化有足够的解释力和合理性,完全能替代物上之债,我们再花费时间和功夫去了解陌生的物上之债,显然不划算。是否如此,需靠其二者的优劣对比来印证,结论是相比于债权物权化,物上之债更有学理优势。
债权物权化由格哈德·杜尔克凯特( Gerhard Dulckeit) 于 1951 年首次系统提出,他把债权物权化指向有物权特征的债权,并把占有作为债权物权化的基点,具体规范类型包括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或第 1007 条的物权化( 主要是基于占有的物权化)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986 条第 2 款的物权化( 主要针对涉及动产的债权物权化) 、依据《德国民法典》原第 571 条( 现第 566 条) 等条文的物权化( 即租赁)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 883 条的物权化( 即预告登记) 。[45]杜尔克凯特的债权物权化理论在德国没有形成高度共识,无论在其何以如此的机理 探究,还是在其涵括哪些具体形态的制度梳理,争议均不小。对杜尔克凯特提出最有影响力批评的是克劳斯 - 威尔海姆·卡纳里斯( Claus-WilhelmCanaris) ,他认为不能把占有作为债权物权化的基点,并认为只有当债权的效力扩及第三人,也即有物权绝对性时,才构成债权物权化,具体规范类型除了杜尔克凯特提及的预告登记的债权、为占有提供本权的债权和租赁,还包括债权性的留置权、行纪委托人的法律地位和信托人的法律地位。[46]赫尔曼·魏特瑙尔( Hermann Weitnauer) 也提出相当有影响的批评意见,他基于履行的过程和《德国民法典》中债权性权利地位的物权化,否定了杜尔克凯特的债权物权化理论。[47]
上述的学理争鸣表明,债权物权化的机理和形态并不确定,共识度不高。与此不同,正如前文所言,除了在个别细节上有不同声音,瑞士民法学理对物上之债的整体有高度共识。虽然共识程度的高低未必是学理成熟度高低的标志,却是信息聚拢程度高低的方向标,学理共识度愈高,在学习和理解时需把握的信息就愈少,只要掌握所谓的通说即可; 反之,就需了解相对分散且不同的信息,并进行合理地评价和分析,对于我们这些继受法域的法科人士来说,这无疑大幅提升了学习和理解的成本,显非易事。就此而言,共识度更高的物上之债更易于学习和理解。
德国民法学理对债权物权化的展开,除了以物权法为规范基础,还涉及其他法律领 域,如杜尔克凯特把租赁纳入其中,卡纳里斯还扩及留置、行纪、信托等债法和商法领域。 由此可知,债权物权化旨在表明某些债权像物权一样有绝对性,至于这些债权受哪些法律规制,在所不问。这体现了德国学者从具体制度中归纳共性,进而建构具有普适性的一般化理论的学术努力,根据这种思路,债权物权化不一定与物权有关,“物权化”在此更多地起到比喻和象征作用,以表明债权有约束第三人的效用,并在法律地位和保护上与物权相当,从而不能完全为与物权对立的普通债权所包容。
由于债权物权化的规范基础甚广,所包容的具体制度各自构造差异又较大,不熟知它们及与其关联的制度,就难以准确理解债权物权化的基础理论。比如,租赁和预告登记是 最典型的债权物权化现象,根据卡纳里斯的研究,前者除了债法的相关规范,还涉及《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861 - 864 条、第986 条第2 款、第1007 条以及《德国破产法》第21 条、《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第 57 条,后者除了物权法的相关规范,还涉及《德国民法典》第 823 条、第 869 条、第 986条第 2 款、第 1007 条以及《德国破产法》第 24 条、《德国强制拍卖与强制管理法》第 48 条,[48]只有准确理解这些规范并能建立体系化的联结,才能全面把握债权物权化的意蕴。故而,对于如何界定物权化、债权如何物权化、物权化的债权种类有哪些等问题,无法在教科书中充分展现,只能交由专论来探讨和阐述。在德 国,民法总论教科书是民法入门书,它们在阐述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分类时,通常会简短引述杜尔克凯特、卡纳里斯等人的专论,点出债权物权化这种中间状态,仅此而已。[49]债法、物权法等教科书在阐述租赁、预告登记等制度时,主要详细论述其制度构造,债权物权 化只是夹杂或隐藏于其中的局部知识点。[50]在这种格局中,读者往往只知债权物权化的梗概,而不知其详貌和机理,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显然不利于债权物权化作为体系化的知识进行传播。
与债权物权化不同,物上之债的规范基础只限于物权法,这些债因此确定地与物权或占有有关,这使它被限定为物权法的专门知识。这种限定的好处是把焦点聚在与物权紧密关联的债之上,可加深法科人士对物权法规制对象的理解,知道物权人依据物权不仅享有支配利益,还可能享有债权或承受债务,这不仅是实证法布局的真实写照,更与物权人的现实法律地位高度契合。而且,尽管物上之债也涉及租赁等债法制度,但其规范基础仍在物权法,如作为物上之债的租赁以预告登记为支点,债法有关租赁的规定只起辅助理解作用,在理解时只要把握相关的数个债法条文即可。凭借这种简约而单纯的特性,物上之 债很容易从专论进入物权法教科书,成为便于传播和授受的知识板块。
上述范围限定也有缺陷,就是物上之债以物权法为依托,归拢了一批法律制度,同时 又“流放”了债法规定的能约束第三人的债,如未预告登记的租赁因此就无家可归。不过,这些被“流放”的债数量很少,教科书或论文在阐述它们时,只要能将其构造解释清楚,[51]似乎也没有必要非要捏合在一起,形成类似债权物权化的公因式。
债权物权化与公示机制的关系密切。在杜尔克凯特看来,债权物权化总是与标的物的占有联系在一起,而他所谓的占有,在动产就是对物的实际支配,在不动产则是登记,这正是公示原则的体现。[52]卡纳里斯不同意把占有作为债权物权化的基础,但他认为债权物权化多涉及有体物,效果与物权接近,应适用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考虑到债权有约束第三人的效力,就应通过公示来使他人知道这种效力。[53]
显然,公示对债权物权化至关重要。抛开不同的制度要素和说理机制不谈,公示对物上之债也起着根本的支撑作用,如登记对物上之债产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明确的例证。可以说,物上之债与债权物权化都重视公示的作用。必须提及的是,与杜尔克凯特和卡纳里斯不同,魏特瑙尔提出了债的关系的物权化, 他把视角落在约束第三人的债的关系上,所涉及的规范不仅有租赁,以及与其效力类似的保险合同、出版合同、雇佣合同; 还有物权法允许当事人所为的约定,包括共有人约定( 《德国民法典》第 1010 条) 、土地所有权人与用益权人的约定( 《德国民法典》第 1041 条) 、地上权的约定内容( 《德国地上权条例》第 2 条) 等,这些约定是债的属性,它们借助登记而约束第三人,故登记是它们物权化的支撑机制。[54]
若魏特瑙尔的上述见解能放入债权物权化的理论框架,那么,债权物权化与物上之债在部分内容上重合,即德国法允许的上述约定与意定的物上之债极其接近,它们均是相对性的债,均与物权并存,均是物权人应为的积极给付义务,均要通过登记来约束取得标的物的任一物权人。据此可知,德国和瑞士的土地登记除了记载法定的物权内容,还能记载法律允许的约定之债,并因此能约 束第三人。不过,与物上之债不同,德国把可登记的约定之债作为物权的内容来看待,[55]这在理论解说上存有悖论,因为物权是支配权,除了因实现支配利益而受到应有的消极限制外,如根据《德国地上权条例》第 7 条第 2 款,地上权人在地上权上设立的抵押权等负担,不得使地上权的目的受到根本性的妨害或危害,物权人不应再承担积极的行为义务,用物权的内容来涵盖上述债,无疑自相矛盾。而且,即便认为这些债被物权化,也只是说它们对权利的特别继受人有效,并无其他的物权效力,这也不改其债的本性。[56]故而,在实际效果等同的前提下,对可登记的约定之债的解释力而言,物上之债更胜一筹,其理论和规范因此值得重视。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83 条、第888 条,预告登记的对象是引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请求权,如买方对卖方移转土地所有权的请求权。在这种制度构造中,买方等请求权人是预告登记权利人,卖方等物权人是义务人,双方之间是债的关系。
不过,预告登记的债权不同于普通债权,具有明显的物权属性。比如,预告登记不禁止义务人处分该不动产物权,但处分导致第三人取得与预告登记的请求权内容相悖的物权的,该处分对预告登记权利人相对无效,义务人仍是物权人。而且,由于第三人已取得物权,仅凭义务人不足以实现预告登记的债权请求权,为此,在预告登记权利人和义务人进行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 时,权利人有权请求第三人同意该登记,从而能实际确保债权实现。[57]又如,在义务人破产或被强制执行时,预告登记的债权请求权视同已实现,从而能被优先保护。再如,法律对预告登记权利人提供的保护措施,如物权请求权、侵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对物权人的保护没有根本差异。[58]
瑞士的预告登记虽然与德国一样,均以德语表示为 Vormerkung,但其二者实质差异颇大。最明显的是对象不同,德国严格限定为引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债权请求权,瑞士则范围宽泛,除了第 959 条的对人权,还有 960 条的处分限制、第 961条的临时登记或假登记,不过,后两种预告登记不是物上之债。而可预告登记的对人权的具体类型,取决于法律规 定,其中既包括引致物权变动的权利,如第 814 条第 3 款的后顺位抵押权的升进权,也包括直接成立买卖合同、间接引致物权变动的权利,如债法第 216a 条的先买权,还包括不可能引致物权变动的权利,如债法第 261b 条的租赁。照此标准来看,共有物管理协议等为德国法允许的约定之债均能纳入其中,把它们当成物上之债,既能让它们回归债的范畴,化解被强拉入物权内容的错位,又能体现它们对抗第三人的物权属性。此外,二者的效力实现方式不同。瑞士的预告登记不禁止土地所有权人处分该土地,并对之后通过市场交易或强制执行取得该土地所有权的第三人有约束力,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可直接针对该第三人来主张实现权利,从而保障了预告登记权利的实现机会。[59]
这与德国预告登记的效力类似,但实现方式差别不小。德国主要以相对无效为支点,牢牢地把债的主体局限于预告登记权利人和义务人,再辅以权利人对第三人的登记同意请求权。 在这种制度架构中,第三人无论如何不是债的主体,而预告登记权利人要实现其权利,需要义务人和第三人的协助。与此不同,瑞士通过主体物化的方式来实现预告登记的权利, 即一旦第三人从义务人处受让土地所有权,就要承接其法律地位,成为预告登记权利人的相对人,这减少了所涉及的主体数量,关系显得更为简单。
物上之债的借鉴价值
从前述可知,债权物权化和物上之债的学理成型时间基本相当,各有独特的知识路径。在之后的学术发展中,尽管德国和瑞士的学者都注意到对方的理论,但均未借鉴吸收。比如,西索尼乌斯和萨特合著的《不动产物权法》在瑞士相当有影响,该书在阐述物上之债时,把前文提及的德国债权物权化的著述作为参考文献,[60]但从其内容看不出这些文献有什么实质影响。又如,有学者撰文探讨德国法有无物上之债的问题,魏特瑙尔对 此认为,这对深化问题的讨论没有多少助益。[61]
这种微妙的态度表明,虽然德国和瑞士在债权、物权二分上完全一致,并都有填补二分缺口的制度,但因为相关的具体规范存在差别,再经过路径不同的学理和实务锤炼,债权物权化和物上之债都相当成型和稳固,异域经验难以有效渗入。也就是说,尽管与债权物权化相比,物上之债在学理上更优,但只要债权物权化的制度足够成熟,能游刃有余地应对现实问题,倒也没必要为了理论完善而转向物上之债。反观我国,债权物权化所涵盖的制度难言成熟,反而极具争议,这一点在《合同法》第229条的买卖不破租赁上表露无疑,该条是民法常识,但学界和实务界对它的反思从未停止,迄今没有共识。[62]
预告登记也不例外,有关其对象、效力的争辩之声此起彼伏,难以达成一致。[63]既然我国不像德国那样有成型而稳固的制度,借鉴物上之债就不会带来不必要的制度成本,反而会给我们的思维打开另一扇窗,让我们有更宽阔的视野来审视和选择。这也说明,我们在继受债权和物权二分后,如何填补二分的缺口,不是仅有债权物权化这一条路可走到底,物上之债也是一条可选择的道路。不仅如此,虽然债权物权化很早就进入我国民法知识体系,积累了相当的话语熟悉度,但它未凝聚高度的学术共识,其内涵和外延相当不确定,[64]它只是法科人士熟知的一个专业语词。
而且,我国民法教科书多有债权物权化的简述,所举例子多为租赁或预告登记,这与德国类似,但我国缺乏债权物权化的深度专论,更缺乏结合我国规范使其本土化的专论。[65]可以说,债权物权化在我国学理研究中还未充分展开,远非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在这种现实中,借鉴学理上更占优势的物上之债,不是叠床架屋的多此一举,不会在学理更替上增添不必要的理解成本,反而能弥补既有知识的不足。此外,债权物权化勾连了相当复杂的知识系统,非民法教科书所能胜任,即便经过学 术努力,它成为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也不便以教科书作为载体进行传播。与此不同,物上之债被限定在物权法当中,所涉及知识点相对较少,是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很容易理解和把握,也易于通过教科书进行传授,更有借鉴价值。还要看到,我国有不少与瑞士物上之债类似的规范,这为物上之债的理论引入提供了现实通道。
这些类似规范至少存于以下领域:(1)相邻关系,《物权法》第 86 - 88 条的不动产权利人为相邻权利人提供必要便利的义务;(2)共有,《物权法》第 96 条的共有人管理共有物的义务、第 97 条的按约定处分或修缮共有物的义务、第 98 条负担管理费用的义务、第 99 - 100 条的按约定分割共有物的义务;(3)动产所有权,《物权法》第 109、111 条的拾得人保管、通知和返还义务;(4)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 42 条,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用地人的给付义务;(5)地役权,《物权法》第 157 条第 2 款允许当事人约定的利用方法;(6)抵押权,《物权法》第 194 条第 1 款允许当事人约定改变抵押权顺位;(7)预告登记。
与债权物权化一样,物上之债并非实证法术语,而是学理通过梳理有关的具体法律规范后,通过提炼共性的方式而总结出的法学概念,体现了学界对法律规范的再认识。这意味着,物上之债是学理对相关规范进行归类的结果,更多的是在肯定这些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的体系化整理,而不是通过批评性分析得到的改良建议,在此意义上,物上之债就像串珠之线,它把零散的法律规范条文串在一起,有助于规范及其知识的体系化。既然物上之债针对相关的法律规范而展开,那对它的理解和认知,就离不开对这些规范的了解和把握。故而,对异域的法科人士而言,要想全面而立体地掌握物上之债,除了把握其基础理论,还必须关注相关规范的制度构造。而且,对于我国这样的后发法域而言,借鉴物上之债这样的法学概念及其基础理论, 对于知识理论体系的圆满固然重要,但更有实际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是对支持这些概念的具体规范的认真学习和剖析,只有把握好它们的具体细微之处,才能准确地与本土的相应制度进行对比,衡量相互间的异同之处,合理设置本土制度的改进机制。
物上之债主要发挥着与物权协调并存的效用,就是在确保物权法定原则带来的权利稳定性的同时,又在法律框定的范围内,交由当事人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治,以在权利行使和实现上达到细致而精准的调整。在上述效用的实现过程中,不动产登记起着重要作用,它使潜在交易者事先了解与物权并存的物上之债的信息,进而自主决定是否进行交易,是否承受既有的权利义务布局。总而言之,在法律规定的大框架内,把物权人所为的约定之债纳入登记对象的范围,使其约束受让物权的第三人,既维持了原有的利益格局,不至于因有第三人的介入而要重新洗牌,能节省交易成本,又为第三人提供完全的信息,能保障其有效地作出自主决策。
德国的不动产登记也能记载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的债,这些债的功能与物上之债相当,也有上述益处。正是着眼于有这些益处,我国台湾地区在修订其民法典物权编时,大幅增加了可登记的约定之债,并明确经登记而对抗第三人,如该法第826-1条规定,不动产共有人就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的约定登记后,对于应有部分的受让人或取得物权之人效力;又如,该法第836-1条规定,预付的地租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再如,该法第826-3条规定,地上权人约定的使用方法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66]由于我国台湾地区的土地登记簿以记载法定的物权内容为主,其簿页空间相当有限,难以准确且充分地显示上述约定之债,为了应对该问题,根据“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 155 - 1条、第 155 - 4 条,要额外增设专簿,即把这些约定集结起来供查询和复制,主要包括共有物使用管理专簿和土地使用收益限制约定专簿。
我国大陆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尽管《物权法》第 96 - 100 条允许当事人约定共有物的管理、处分、分割等债的事项,但并未提供相应的登记机制,这些约定之债因此无法对抗第三人,当然也不像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那样,既能节省交易成本,又有助于第三人在获取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自主决策。两相对比,法律应明确这些约定之债可被登记,并明确在登记后它们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在此基础上扩大我国大陆不动产登记的容量,把这些约定之债纳入登记对象范围,就是当为的改进之道。这些约定之债载入不动产登记簿后,就是存身于物权范畴之外的物上之债,而非物权 的内容。换言之,借助物上之债,物权人应为的给付义务仍是债,并因其主体物化而有特殊的法律地位。这样的好处是保持了物权在绝对权与支配权上的纯粹性,不混杂债的属性,由此也能避免它究竟是物权还是物权化的德国式歧义和争议。
另外,这些约定之债在不动产登记簿中如何记载,还应予以考虑。以《物权法》第 96 条的共有物管理协议为例, 所有权登记簿页的可记载信息有限,无法有效地容纳协议约定的内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像我国台湾地区那样设立专簿,把协议作为登记簿的附件。这样一来,我国大陆的不动产登记簿就无法完全制式化,而是必须把当事人的约定纳入进来,形成各式各样的专簿,这无疑使登记簿的架构显得过于复杂,无论对登记机构还是当事人,均不便利。为了避免这一弱项,可以扩张预告登记的对象范围,把共有物管理协议等物上之债纳入当 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预告登记的对象是房屋买卖合同等约定的债( 《物权法》第 20 条) ,其簿页的空间容量能充分记载债的信息,用它来体现物上之债,就无需通过增设专簿来改变登记簿的建制。这种设想无疑受瑞士法的启发,但又不单如此,国内也有相应实 践经验的支持,如《南京市城镇房屋权属登记条例》第 28 条早就把涉及房屋的约定请求权作为预告登记的对象,其明文规定的对象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先买权、回购房屋、通行权的约定,此外还能把共有房屋管理协议等解释在内。一旦共有不动产的管理协议等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的债成为预告登记的对象,预告登记就不能禁止不动产物权人再行处分物权,在第三人受让物权后,就会出现预告登记权利人、原物权人和第三人三足鼎立的格局,在物上之债的规制下,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地位不变,受让不动产物权的第三人自动成为相对人,原义务人由此出局,权利人向第三人主张债权请求权即可,该权利不受原义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关系的影响。
概括而言,要借鉴物上之债,就离不开不动产登记的配套支持,主要是把法律允许当事人所为的约定之债纳入登记范围,使其能对抗第三人。为了不额外增加制度改革和运行的成本,并与物上之债的特性保持一致,这些债宜归入预告登记的对象,通过预告登记簿页来记载它们即可,从而无需像我国台湾地区那样在登记簿之外增设专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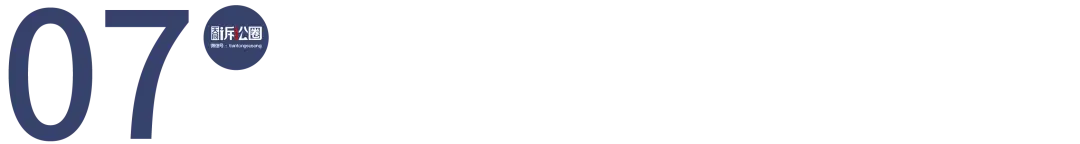
结语
面对债权与物权二分不彻底所留下的法律缝隙,不只有债权物权化这种德国式的解决方案,瑞士的物上之债也具有相同功能。根据瑞士民法学理,物上之债融合了债的属性和物权属性,它既有债的相对性,不像物权那样属于支配权,并受制于债的效力规范,同时又有物权属性,是主体物化的债,依附于物权而存续,并遵循法定原则、公示原则等物权法基本规范。
与债权物权化相比,物上之债更具有学理优势,不仅因其学理共识度高,属于物权法的专门知识而易于学习和传授,且其在债权和物权二分的基础上,为能约束第三人的债提供了恰当位置,不至于像德国那样把这种债作为物权内容,在理论上更自洽,还因其基于主体物化的特性,把预告登记的关系人限定为权利人和义务人双方,有简化法律关系的益处。
我国民法学理虽然早就知悉债权物权化,但学界和实务界对其所指的租赁、预告登记等制度相当有争议,且对债权物权化也未展开充分的研究,再加上债权物权化不宜通过教科书来传播,这就为学理更优的物上之债在我国的继受提供了空间。而我国有不少法律规范与瑞士物上之债规范相似,物上之债对我国的借鉴也就相当现实。在借鉴时,主要是改进我国的预告登记制度,将其适用范围扩及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与物权相关的债,如共有不动产的管理协议等。
在物上之债的法律地位确定后,必须强调,它虽然与并存的物权均有主体物化的属性,但物上之债缺乏物权的支配性和对世性,与物权无法混同,故而,物权法的规制对象不能以物权单一视之,还要把物上之债这种债的要素考虑进来。
当然,物权是物权法进行规范配置的基础和主干,物上之债起到辅助作用,只有在平衡物权人与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时才有必要存在。但无论如何,物权法的内容不只是给主体带来积极利益的物权,在必要之处还有给物权人带来义务的物上之债,在物上之债存在之处,物权人就处在既有权利、又有积极行为义务的法律关系之中,这种法律地位不是仅用物权就能框定和含括的,由此可 知,在物上之债的介入下,物权法实质上就是物上关系法。
注释:
[1]参见常鹏翱: 《债权与物权在规范体系中的关联》,《法学研究》2012 年第 6 期,第 87 - 91 页。
[2]参见苏永钦著: 《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91 页。[3]参见苏永钦著: 《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6 页; 苏永钦著: 《寻找新民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3 - 165 页。[4]参见王利明著: 《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 3 版,第 30 - 31 页。[5]苏永钦教授指出,物上之债在民法释义学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参见苏永钦著: 《寻找新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3 页注 10。[6]为了节省篇幅,《瑞士民法典》物权编的条文在本文中均表示为第…条,《瑞士债法》的条文则表示为债法第… 条,其他法域的法律条文则标明域别称谓,如《德国民法典》。本文引用的瑞士民法条文,由本文作者据其德文版本【Gauch / Stoeckli ( Hrsg. ) ,ZGB,49. Aufl.,Zuerich 2012; Gauch / Stoeckli ( Hrsg. ) ,OR,49. Aufl. ,Zuerich 2012】译出。[7]Vgl. Gauch / Schluep / Schmid,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Allgemeiner Teil,Bd. I,9. Aufl. ,Zuerich 2008,S. 14 ff.[8]参见苏永钦著: 《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6 页; 苏永钦著: 《寻找新民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3 页。[9]Gauch / Schluep / Schmid,a. a. O. ,S. 19 ff.[10]也有个别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尽管这些形成权在行使后会产生债的关系,但其本身不是债权,不应归为物上之债。Vgl. Simonius / Sutter,Schweizerisches Immobiliarsachenrecht,Bd. I,Basel und Frankfurt am Main 1995,S. 98.[11]Vgl. Gauch / Aepli / Stoeckli,Praejudizienbuch zum OR,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gerichts,6. Aufl. ,Zuerich 2006,S.11; Tuor / Schnyder / Schmid / Rumo-Jungo,Das Schweizerische Zivilgesetzbuch,13. Aufl. ,Zuerich 2009,S. 1013.[12]Vgl. Meier-Hayoz,Berner Kommentar,Kommentar zum schweizerischen Privatrecht,Bd. IV,1. Abteilung,1. Teilband,5.Aufl. ,Bern 1981,S. 113 f; Rey,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3. Aufl. ,Bern 2007,S. 68.[13]这是一种特殊的对人之诉,它所针对的责任人是不特定的,在这种诉讼中,原告只列举特定的非法事实,不列举行为人,可要求执法官对所有与此非法事实有关的人判罚。参见【意】彼得罗·彭梵得著: 《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7 页; 黄风编著: 《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2 页。[14]Vgl. Liver,Das Eigentum,in: Schweizerisches Privatreht,Bd. V,1. Hbalbband,Basel und Stuugart 1977,S.21.[15]Meier-Hayoz,a. a.O. ,S.115.[16]Liver,a.a. O. ,S.21.[17]Meier-Hayoz,a. a. O.,S. 115.[18]瑞士民法学理在阐述法定的物上之债时,都会例举相应规范,但因各自的侧重点或篇幅不同,例子和范围均有出入。本文的上述例举,综合了著名学者 Meier-Hayoz 和 Rey 的见解。Meier-Hayoz,a. a. O. ,S. 117 f; Rey,a. a.O.,S. 70.[19]Vgl. Gauch,Werkvertrag,5. Aufl. ,Zuerich 2011,S. 525.[20]Rey,a. a. O. ,S. 186.[21]Meier-Hayoz,a. a. O. ,S. 125.[22]Rey,a. a. O. ,S. 69.[23]Simonius / Sutter,a. a. O. ,S. 88 f.[24]Rey,a. a. O. ,S. 72.[25]Vgl. Schmid / Huerlimann-Kaup,Sachenrecht,4. Aufl. ,Zuerich 2012,S. 391.[26]Rey,a. a.O.,S.72 f.[27]Schmid / Huerlimann-Kaup,a. a. O. ,S. 312.[28]Rey,a. a. O.,S.75 f.[29]Tuor / Schnyder / Schmid / Rumo-Jungo,a. a. O. ,S. 1013.[30]Simonius / Sutter,a. a. O. ,S. 91 f.[31]Simonius / Sutter,a. a. O. ,S. 83,92.[32]Simonius / Sutter,a. a. O. ,S. 85.[33]Schmid / Huerlimann-Kaup,a. a. O. ,S. 184; Simonius / Sutter,a. a. O. ,S. 92 f.[34]Vgl. Riemer,Die beschraenkten dinglichen Rechte,2. Aufl. ,Bern 2000,S. 106 f,147.[35]Meier-Hayoz,a. a. O. ,S. 121.[36]Rey,a. a. O. ,S. 74.[37]Gauch / Schluep / Emmemegger,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Allgemeiner Teil,Bd. II,9. Aufl. ,Zuerich 2008,S. 218.[38]Rey,a. a. O. ,S. 75.[39]Schmid / Huerlimann-Kaup,a. a. O. ,S. 186.[40]Meier-Hayoz,a. a. O. ,S. 123 f.[41]Vgl. Huerlimann-Kaup,Vertragsrecht und Grundpfandrechte,in: Gauchs Welt,Festschrift fuer Peter Gauch zum 65 Ge- burtstag,Zuerich 2006,S. 456.[42]Rey,a. a. O. ,S. 67. 另一种学理见解认为,租赁物的新所有权人因为承受了租赁关系,从而不仅承担义务,还取得权利,这也使物上之债的规范由此没有适用空间。Simonius / Sutter,a. a. O. ,S. 97.[43]Meier-Hayoz,a. a. O. ,S. 124.[44]Vgl·Schmid / Stoeckli,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Besonderer Teil,Zuerich 2010,S. 151.《瑞士债法》于 1990年修订前,采用买卖破租赁的规则,但租赁合同的预告登记有确保买卖不破租赁的效力。Vgl. Isler,Die im Grundbuch vormerkaren Persoenlichen Rechte ( Vrokaufs-,Kaufs-und Rueckkaufsrecht; Mite und Pacht) und ihre Steuerrechtliche Behandlung,Zuerich 1989,S. 103; Ott / Verardo,Kauf bricht ( nicht) Miete,in: ZSR 1 /1996,S. 32.[45] Vgl. Dulckeit,Die Verdinglichung obligationscher Rechte,Tuebingen 1951,S. 3 ff .[46]Vgl. Canaris,Die Verdinglichung obligationscher Rechte,in: Festschrift fuer Werner Flume zum 70. Geburtstag,Bd. I, Koeln 1978,S. 372 ff.[47]参见【德】赫尔曼·魏特瑙尔: 《物权化的债之关系》,张双根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48] Canaris,a. a. O. ,S. 373 ff.[49]如【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 《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9 - 60 页; 【德】卡尔·拉伦茨著: 《德国民法通论》下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02 - 304 页。[50]如【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 《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0 - 193 页; 【德】曼弗雷德·沃尔夫著: 《物权法》,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2 - 243 页。[51]Ott / Verardo,a. a. O. ,S. 29 ff; Schmid / Stoeckli,a. a. O. ,S. 168.[52]Dulckeit,a. a. O. ,S. 11 f.[53]Canaris,a. a. O. ,S. 376 ff.[54]赫尔曼·魏特瑙尔: 《物权化的债之关系》,张双根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153-160 页。[55]Baur / Stuerner,Sachenrecht,18. Aufl. ,Muenchen 2009,S. 387 f.[56]赫尔曼·魏特瑙尔: 《物权化的债之关系》,张双根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160页。[57]由第三人承担债法义务,也是一种选择,但《德国民法典》立法者认为,这类法定的债务承担违背了整个体系,故未采用。Baur / Stuerner,a. a. O. ,S.261.[58]Canaris,a. a. O. ,S. 381 ff; Baur / Stuerner,a. a. O. ,S. 260 ff.[59]Vgl. Zobl,Grundbuchrecht,2. Aufl. ,Zuerich 2004,S. 127.[60]Simonius / Sutter,a. a. O. ,S. 81.[61]赫尔曼·魏特瑙尔: 《物权化的债之关系》,张双根译,载《中德私法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158页注65。[62]参见张双根: 《谈“买卖不破租赁”规则的客体适用范围问题》,载《中德私法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 - 19 页; 黄凤龙: 《“买卖不破租赁”与承租人保护》,《中外法学》2013 年第 3 期,第 618 - 643 页。[63]参见何小勇: 《预售商品房抵押效力问题探讨》,《西部法学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 61 - 64 页; 孟祥沛: 《中国式按揭》,《政治与法律》2013 年第 5 期,第 94 - 95 页; 张双根: 《商品房预售中预告登记制度之质疑》,《清华法学》2014 年第 2 期,第 74 - 86 页。[64]如王泽鉴教授把租赁和预告登记作为典型形态,参见王泽鉴: 《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 - 14 页; 而王利明教授还把基于债权产生的优先购买权、共有中的分管协议、债的保全归入进来,参见王利明著:《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第 3 版,第 27 - 28 页。[65]以“债权物权化”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和 CSSCI 期刊搜索,截至 2015 年 9 月 18 日,在 1998 - 2014 年间,有 29 篇论文与此相关,其中,金可可教授发表于《法学》2007 年第 7 期的《预告登记之性质》和发表于《法学研究》2009 年第 2 期的《基于债务关系之支配权》完全以债权物权化为主题而展开,这两篇论文主要参酌德国文献进行展开。[66]参见王泽鉴著: 《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2 版,第 219、235、243、297 页; 谢在全著: 《民法物权论》中册,作者2010年修订 5 版,第 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