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栏目主持人顾嘉按:在历经7年、35轮艰苦谈判后,中国和欧盟如期实现2020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预期目标。协定的核心内容包括市场准入、透明度、劳工待遇、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然而,中欧双方尚需就协定中采用何种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ISDS),进行磋商。本文将就协定中可采取的ISDS条款类型,提出建议。本文的作者李珏律师,对国际投资法和投资协定仲裁方面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跨境顾释”栏目非常乐意刊登像李珏律师这样的中国年轻涉外争议解决律师,在新型法律问题上的思想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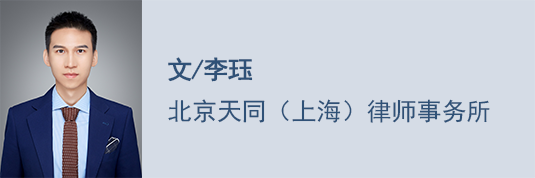
2020年12月30日,中国与欧盟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标志着历时7年的谈判工作终于完成[1]。在中欧领导人就协定已经达成政治结论(political conclusion)后,双方即将开始协定的法律文件起草、翻译以及校对工作。
实际上,在中欧投资协定之前,我国与欧盟多个成员国之间已经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但条款内容相对而言较为简单,部分协定仅涉及投资保护条款,缺乏市场开放的内容。根据目前公开的新闻报道,中欧投资协定则涵盖市场准入、透明度、劳工待遇、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2]。除实体条款以外,中欧投资协定将设计和采用何种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端解决条款(ISDS条款)同样令人期待和关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目前新闻报道,中欧投资协定文本并不包含任何关于ISDS条款的内容,而是采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相类似的路径——缔约国同意将先行公布和签署实体内容,然后在一段时间内就ISDS条款另行协商和确定[3]。如此一来,就最终ISDS条款将采取何种模式,给大家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有鉴于此,笔者基于中国及欧盟近年来对外签订投资或贸易条约的情况,以及目前关于《中欧投资协定》公开的信息,仅就最终商定的ISDS条款可能呈现的方式,尤其是近年来广泛讨论的上诉机制是否会进入ISDS条款进行简要分析和预测。
一、中国与欧盟成员国所签订投资协定中ISDS条款的特点
1982年瑞典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这也是首个与中国缔约的欧盟成员国。在此之后,中国与欧盟各国相继签署及重新谈判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与包括德国、芬兰、瑞典等在内的23个欧盟成员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4]。虽然这些协定在实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大区别,但ISDS条款却呈现出一定共性。
首先,多数ISDS条款强调通过非诉讼或仲裁的方式解决争端,部分协定将非诉方式作为提起仲裁的前置程序,这一点在中国与欧盟成员国较晚签订的投资协定中体现得格外明显[5]。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关于保护投资的协定议定书》第二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约定:“如投资者对其被征收的投资财产的补偿款额有异议,投资者和采取征收措施的缔约一方应为在六个月内达成补偿款额协议进行协商。如在前述规定的期限内,协商的双方未获一致,应投资者的请求,由采取征收措施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国际仲裁庭对补偿款额予以审查。” 又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第十条约定:“在本条第一款所述的书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友好解决时,有关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的补偿额的争议,可按投资者的选择:(二)或直接提交国际仲裁,而不诉诸其他任何手段。”此外,2005年《中国西班牙双边投资协定》、2005年《中国葡萄牙双边投资协定》以及2007年《中国法国双边投资协定》均作出了相同或者类似的规定,而这符合中国政府历来希望通过友好协商、磋商或调解的方式解决国家作为一方主体的争端的传统。
其次,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签订的ISDS条款基本上采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及临时仲裁两种方式并行的制度设计,投资者可择一适用。例如《中国德国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九条约定,争议应依据1965年3月18日《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提交仲裁,除非争议双方同意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UNCITRAL)或其他仲裁规则设立专设仲裁庭。类似的约定还包括《中荷双边投资协定》、《中法双边投资协定》等,在部分协定中也将国内法院作为一种可选择的争端解决的主管机构[6]。
二、欧盟对外签订投资协定中ISDS条款的特点
为提高ISDS机制的合法性、透明化及中立性,欧盟自2015年开始在对外签署的投资协定中引入并实施了一系列争端解决条款的改革措施[7],其中比较典型的特点包括:
1.强调国家规制权,缩小ISDS受理范围
强调对外来投资的规制权(the State’s right to regulate)是欧盟就ISDS机制改革的重点事项,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是缩小ISDS条款的受理范围。以《欧盟与加拿大的综合经济贸易协定》为例,Section F关于ISDS条款即规定,如东道国在投资准入阶段违反Section C项下的非歧视待遇义务(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的,由此产生的争议不适用于ISDS条款解决[8]。例如,东道国对于外国投资者与本国投资者在东道国设立公司环节施加不同的标准和义务的,则可能违反国民待遇原则,但是投资者并不能根据条约中的ISDS条款来解决由该等违反义务行为导致的争端。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近年来出现大量投资者对于东道国法律制度(包括投资准入阶段)的合理性提出挑战,但东道国对投资准入制定法律本身属于一国内政,如果允许投资者对此不断提出投资仲裁,则可能对国家主权造成损害,因而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
2.创设投资仲裁上诉程序
投资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出现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一直以来广受诟病,这也是2015年欧盟改革ISDS条款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欧盟与加拿大的贸易协定》中,在保留ICSID和UNCITRAL仲裁规则项下的投资仲裁的同时,建立了由15位裁判人员组成的相对固定建制的常设仲裁机构,对欧盟与加拿大之间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进行初审仲裁和上诉仲裁[9]。这一创新性的上诉机制体现了欧盟解决投资仲裁裁决结果不一致的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成为未来ISDS条款改革和发展的趋势。
三、中欧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方式的展望-上诉机制之辩
实际上,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中国与欧盟各自对外签订的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存在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内容,比较典型的如均将协商及磋商等非诉讼或仲裁争端解决方式纳入到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框架之中,并与传统的投资仲裁并行或前后衔接共同构建起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些非诉解决措施也会出现在最终的ISDS条款之中。
相比之下,真正需要讨论的是中欧投资协定ISDS条款是否会引入上诉机制以及如何设计上诉机制。
1.上诉机制出现的原因
作为传统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无论是通过提交ICSID进行仲裁,亦或是适用UNCITRAL规则组建临时仲裁,最终的裁决结果具有“终局性”。虽然ICSID具有裁决撤销制度(Annulment)[10],但其并不审查“事实认定错误”及“法律适用错误”的实体性问题,这一方面导致部分仲裁裁决出现明显的法律和事实认定错误,但当事人缺少必要的救济手段;另一方面也导致相同的案件事实,因仲裁庭组成不同,出现截然不同的裁决结果[11]。基于此,一般国际投资仲裁的“一裁终局”的传统理念已无法满足投资者及东道国对仲裁结果实体公正的渴求,各个国家对改革目前的ISDS机制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其中建立上诉机制便成为可供选择的改革措施之一。
2. 欧盟通过引入上诉机制对ISDS条款的改革
如上文所述,针对传统国际投资仲裁在裁决结果不一致方面的弊端,欧盟贸易委员会于2015年5月制定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提出关于设立上诉机制的建议,具体形式则采用设立常设仲裁庭的方式[12]。2016年,欧盟分别与加拿大及越南达成《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以及《欧越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即引入了前述常设仲裁庭制度并对上诉庭的构成和上诉审查权限均进行了明确的规定[13],但相关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并不尽如人意。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上诉的范围和仲裁员选任方面的设计和规定。例如《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第8.28条第2款规定了上诉庭可以根据三种理由维持、修改或者撤销初审法庭裁决:(1)法律适用或解释上的错误;(2)事实认定上的明显错误;(3)《ICSID公约》第52条第1款第1至5项规定的理由。虽然前述规定在投资仲裁领域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和称赞,但实际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其中的第(2)项事由“事实认定上的明显错误”即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无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认定错误最终能否被认定明显错误,上诉庭实际上均需要对案件事实重新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双方提交的全部证据,这意味着双方当事人重新进行了一次初审程序。考虑到国际投资仲裁程序本身历时漫长,如果上诉机制将初审程序重复进行一次,当事人在原本高昂的法律费用的基础上又将额外产生额外的费用,但上诉最终能否改变初审结果则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显然并不符合当事人的利益。
再比如其中对于上诉机制的仲裁员选任制度,由于不同仲裁员实践经验可能存在巨大差异,最终仲裁员构成对一方缔约国是否公平存在疑问。《欧越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五章规定,上诉法庭的仲裁员由越南-欧盟自贸区贸易委员会指定,其中三分之一应为越南国民,三分之一为欧盟成员国国民,三分之一为第三国国民。这种制度设计的问题是,相比于欧盟成员国的仲裁员而言,越南方面的仲裁员明显缺乏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实践经验[14]。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即便越南籍国民被指定为上诉法庭的仲裁员,在实践中也很难发挥实际作用,容易造成法庭内部力量对比的失衡。
综上而言,欧盟通过建立上诉机制对ISDS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家开阔了思路,具有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但该制度落实到具体细节时,很多设计仍比较粗糙,部分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也值得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3. 中欧投资协定ISDS中值得期待的上诉机制
根据欧盟目前公布的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信息,欧盟明确要求协定条款应当保证来自欧盟的公司享有高标准的保护(high level of protection),相关约定应当体现欧盟在2015年开始实施的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措施(Reformed approach to investor-to-state dispute settlement),而如上所述,上诉机制正是欧盟对ISDS机制改革的重点措施之一,但这是否意味着上诉机制一定会出现在最终的文本之中?我们注意到中国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投资仲裁改革议题提交的立场文件中[15],中国已经将引入上诉机制作为了完善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措施之一。此外,2015年6月中国与澳大利亚签订的《中澳自贸协定》第9章[16]已经引入了仲裁裁决上诉审查制度。因此,中国与欧盟似乎就建立上诉机制并无分歧,接下来的问题将集中在采用欧盟提议的常设投资法院模式还是中国提出的常设上诉机制[17]。实际上,据新闻报道,欧盟方面曾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中提议建立包含上诉机制的投资者法院系统,以利于投资者在对方市场针对对方政府起诉,但中国政府并未同意这一提议[18]。无论如何,上诉机制最终所呈现的形式取决于欧盟与中国之间的谈判,存在不确定性,但至少在中欧协定ISDS条款中引入一定程度的上诉机制是值得期待的。
4. 对《中欧投资协定》ISDS上诉机制的展望-以《北仲投资仲裁规则》为范例
相比于欧盟提出的通过设立常设仲裁法庭引入上诉机制的提议,中国政府提出的常设上诉机制从目前来看可能更为切实可行和灵活,在设计相关条款时,或许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北仲)于2019年制定的《北仲投资仲裁规则》中所包含的上诉机制可以作为重要参考。
首先,《北仲投资仲裁规则》上诉机制采取选择性适用的原则,即上诉应当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因此,除非当事人明确同意适用上诉程序,否则附录5的上诉程序不能自动适用[19]。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当事人滥用上诉制度拖延程序的问题,也能够提高当事人对于仲裁程序时间和成本的可预期性。
其次,关于上诉的事由,《北仲投资仲裁规则》附录5第三条规定,上诉可基于三类事由提起:(1)仲裁裁决对于适用法律或法律规则的适用或解释存在错误;(2)仲裁裁决对于事实的认定存在明显且严重错误;(3)北仲或仲裁庭对于案件缺乏管辖权,或仲裁庭超越其权限。但同时《北仲投资仲裁规则》第四十六条第(四)规定,当事人可以对于上诉事由另行约定。如此一来,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的方式排除或增加上诉事由,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思想,也可以解决欧盟方案中上诉庭将重新审理案件的弊端。
再次,相比于建立一个新的常设仲裁法庭,建立常设上诉机制,其人力、设备和场所需要的成本相对可控,行政管理制度相对简单,相关规则也均可以借鉴《北仲投资仲裁规则》加以约定。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中国可以考虑参考《北仲投资仲裁规则》的规定,设计中欧投资协定ISDS条款。具体建议如下:
首先,上诉机制可以设计为常设上诉机制[20],但就具体案件是否适用上诉机制则将选择权交给当事人。即当投资者针对东道国发出仲裁通知后,如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就该具体案件达成适用上诉机制的合意并提交书面同意函的,则该案件适用上诉机制,否则仲裁仍然遵循一裁终局的制度。其次,关于可以上诉的事由,可以将选择权交给当事人。即ISDS条款可以将(1)仲裁裁决对于适用法律或法律规则的适用或解释存在错误;(2)仲裁裁决对于事实的认定存在明显且严重错误;(3)仲裁程序严重错误作为上诉事由,但同时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增减上述上诉事由达成一致意见,并在同意适用上诉机制的同意函中一并列明。在此环节东道国既可以控制上诉庭对本国法律进行解释的权限,而投资者也可以通过限制上诉事由对成本进行控制。再次,关于常设上诉机制的仲裁员选任问题,可以考虑建立首席仲裁员名单,双方均有权定期补充或者调整名单中的人选,并就具体案件从名单中选择上诉庭的首席仲裁员。同时,双方仍然可以在名单之外各自选择“边裁”,共同组成上诉庭。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欧盟固定上诉仲裁员的诉求,并尽可能解决投资仲裁“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实现中国政府希望保留自行选择“边裁”的诉求。
上述内容仅为笔者目前就设计ISDS条款粗略的想法。无论如何,此次中欧投资协定是中国提高在投资争端解决规则制定方面话语权的机会,也是中国将中国仲裁机构和规则推广到世界的机会,中国政府应对相关条款的设计慎之又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几经受挫,最终双方能够完成谈判实属不易。作为中国近年来达成的标志性投资协定,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其中的ISDS条款会带给大家惊喜,值得期待。
注释:
[1]《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财新网,2020年12月30日。
[2]《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财新网,2020年12月29日。
[3]IA Reporter: EU and China agree on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 but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will be negotiated at a later stage。
[4]见商务部条法司网站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
[5]黄世席:《欧盟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6]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处理国际商事仲裁的专门机构,如国际商会仲裁院(ICC)、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以及北京国际仲裁中心(BIAC)等均制定了自己的投资仲裁规则供缔约国选择适用。虽然目前中国对外签订的投资协定中尚未将前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引入ISDS条款中,但对于中国未来对外签订ISDS条款而言,也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
[7]见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115。
[8]陶立峰:中欧BIT谈判中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的模式选择,载《法学》,2017年第10期。
[9]同注5。
[10]《ICSID》公约第52条。
[11]参见CME(Netherlands) v. Czech Republic (Partial Award) 以及 Lauder (US) v. Czech Republic (FinalAward)。
[12]参见Cecilia Malmstrom: Investment in TTIP and Beyond-the Path for Reform: Enhancing the Right to Regulate and Moving from Current ad hoc Arbitration towards anInvestment Court。
[13]如《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第8.28条。
[14]根据2019年ICSID统计,在ICSID管理的投资仲裁案件中,东南亚及太平地区仲裁员被选任为案件仲裁员的比例仅为11%,其中越南仲裁员从未被选定为任何一起案件的仲裁员。
[15]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wp177c.pdf
[16]《中澳自贸协定》第9章第23条: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3年内,双方应启动谈判,以期建立上诉审查机制,审查在此上诉审查机制建立后依据本章第22条所作出的仲裁裁决。
[17]中国政府在向贸法会提交的建议书中,就设立上诉机制的具体意见为:为解决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支持对常设上诉机制改革方案开展研究。设立基于国际条约的常设上诉机制,明确相应程序、机构、人员,对推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的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完善纠错机制,增强投资争端解决的法律预期,约束裁判人员的行为,也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和澄清程序,减少当事方滥用权利的行为。近期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中国签署的投资协定)已经开始尝试对上诉机制作出规定,或制定与潜在上诉机制进行对接的条款。但相比较双边投资协定,通过制定多边规则规范上诉机制是更有效率的做法,能够最大程度降低制度性成本。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经验看,其上诉机制的效率较高,且运转成本适中。
[18]《7年马拉松式谈判,跨过了哪些坎》,财新,2020年12月31日。但是目前尚未披露任何关于这一方面谈判的具体细节。
[19]根据北仲《投资仲裁规则》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双方当事人书面同意,裁决可以依照本规则附录5上诉。”
[20]从中国政府提交的意见书来看,其关于常设上诉机制的设想为多边常设上诉机制,但是考虑多边常设上诉机制不仅需要中欧达成一致意见,也需要其他国家参与并制定规则,目前尚不具备可操作性。

“跨境顾释”栏目由顾嘉律师主笔/主持,每周五与“巡回观旨”栏目交替发布。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栏目,关注中国法下重大涉外法律问题,分享跨境争议解决的实务经验,介绍外国先进司法区内的最新法律发展和动态以及搭建一个中外法律界和商界的互动平台。如您有任何想法、意见、建议,欢迎点击文末留言.
向“跨境顾释”栏目投稿,欢迎发送邮件至:
david.gu@tiantong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