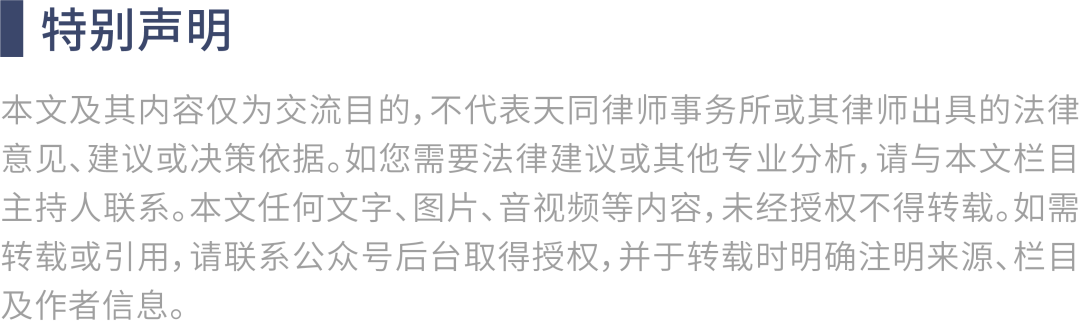注:本文曾发表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82-93页。

目录
导言:《民法典》评注语境下的历史解释方法
一、当代理论中历史解释方法的沉浮及其“中国运用”
(一)历史解释方法的产生背景
(二)历史解释方法的评注适用与中国民法评注
二、我国《民法典》历史解释所依据的材料
(一)《民法典》的历次草案及立法理由
(二)民事单行法时代的法律渊源和释明性资料
(三)习惯法与民法教义学资料
三、我国民法典评注中历史解释方法的适用
(一)历史渊源辨识的规则
(二)历史解释的目标:查明法条的客观规范目的
结论
摘要:我国民法的评注工作应当综合运用文义、体系、目的和历史的解释方法。对于历史解释方法的内涵,我国学界应当摆脱传统理论将其限制为查明规范主观目的这一高度实证化的理解方法,而是将查明规范的客观目的作为主要目标。我国民法评注作品所依据的历史解释材料主要包括民法典历次草案及理由、单行法时代的法律渊源及其释明性材料,以及民法教义学文献。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应当以立法资料中明确可查或通过立法资料之外的文献可佐证的承继关系、并兼顾比较法上的考查来确定条文的历史渊源。通过对单行法既有条文和新设条文的历史解释,评注作品可以查明其客观的规范目的,以实现《民法典》体系下的整合与本土化工作。
关键词:民法典;评注;法律解释;规范目的;立法资料
导言:《民法典》评注语境下的历史解释方法
自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正式颁布生效以来,围绕我国民法典规范适用与解释的法律注释类丛书已然蔚为大观。在数量仍在不断攀升的民法典注释文献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近年来颇受理论界与实务界重视、以民法学者而非官员或法官为主导的“法律评注”系列著作。[1]与民事单行法时代占据市场主流地位的立法机关释义书和司法机关的理解与适用系列丛书相比,[2]法律评注这一在我国方兴未艾的制定法注释体裁,正乘着民法典实施的东风扶摇而起,在民法典时代里牢牢占据了法律解释资料市场中的一方领地。[3]与传统的法律释义书注重阐释法条本身含义不同,民法典评注力图实现立法、司法与学术的沟通,尤其着力于对制定法进行逐条、全面及体系化的解释。[4]学界为逐步建构起我国民法典评注的统一体例已有较充分的讨论,评注的撰写者亦必须遵循法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综合运用传统法律解释的一般方法即文义、体系、目的和历史等解释方法,对法条进行以适用为导向的正当解释。[5]
然而在我国民法典评注的语境下运用上述法律解释方法时,历史解释似乎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在舶自欧陆且已高度实证化的当代解释理论看来,历史解释被降格为目的解释的下位概念或材料基础,其意义仅在于通过展示立法资料而查明立法者的真实意图,[6]但我国立法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缺陷甚至缺位却又使得历史解释在这方面的意义受到极大削弱。[7]另一方面,即令我国民法的评注者暂时摆脱严格实证化方法论的桎梏,内含于《民法典》规范体系中的继受多元性、我国民法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的客观现实也都使得历史渊源的确定与历史解释工作面临重重困难,以至于评注在查明规范客观目的的过程中不得不暂时承担理论继受的工作。[8]
前述尴尬处境并非为我国民法评注所独有。事实上,就作为欧洲法律与法学的继受国而言,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拉丁美洲诸国,[9]制定法的评注工作均须经历通过历史解释方法回溯条文在母国法律体系或“比较法”中的规范目的(ratio legis)的理论继受阶段,才能为制度的本土化或实践继受打下坚实的智识基础。诚然这类历史解释工作不能满足于类似我国既有法律释义书中对“规范史略”或“立法史”寥寥数言的介绍,而是在必要时不得不打破实证化民法教义学与私法制度史之间的隔阂,这对于评注所追求的法条体系化适用之目标而言是必要的。本文将从法学方法论中历史解释的内涵与界限出发,首先简要回顾历史解释方法的原初意义,再通过对我国民法评注工作中适用历史解释方法之必要性的阐述,尝试提出对我国法进行历史解释的方式与具体进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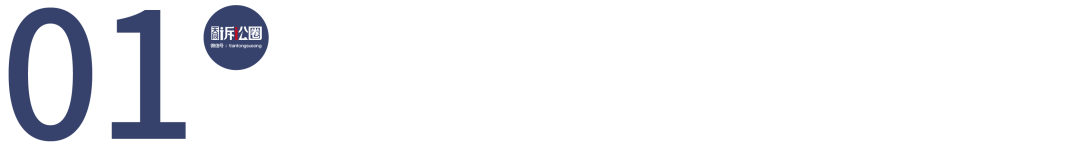
当代理论中历史解释方法的沉浮及其“中国运用”
在我国学界的一般认识中,法律解释方法主要包括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10]这种方法论上的四分法有着悠长的欧陆法学发展背景,可以追溯至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是其根据罗马法继受以来、尤其是为欧洲共同法时期民法学者所惯常采用的解释方法所做的经验性概括,并为法学方法论叙事所延续。[11]尽管在当代方法论的语境里,历史解释似乎具有当然的存在地位,但倘若把观察的视野加以延伸就不难发现,历史解释并非在法律解释中先天(a priori)占据一席之地,在贡献了当今主要教义学方法的罗马法学中并不存在历史解释,而当代意义上的历史解释直到18世纪中叶才获得独立地位,由此应当首先对这一历史经纬进行简要考察。[12]
(一)历史解释方法的产生背景
历史解释方法在欧陆的兴起有着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18世纪以降主权-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立法权成为民族国家内部由主权者所垄断的权力,法律尤其是罗马法被实证化为立法者的命令,[13]成为“君主们做出的规定,臣民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自由行动”。[14]这种法律观念的变迁,导致原本在欧陆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受时空要素拘束的共同法(ius commune)降格为一种“习惯法”或“学者法”,要么在制定法存在漏洞时起到补充适用的效果,[15]要么必须经由民族国家内部的立法过程被转化为实定法才可以具有效力。然而欧陆既有的罗马共同法有着历时悠久的继受特征,并且在民族国家的法典化过程中实际上未被全盘接纳。[16]如在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11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均保留了本民族的特别法和本国习惯法要素。[17]当罗马共同法与实定法规则发生冲突时,人们不再诉诸罗马法背后所代表的、抽象的自然法或理性,而是直接寻求查明实定法的立法者所欲达到的目的或规范意旨。
由此便引出历史解释兴起的第二个因素,即法律的规范目的随共同法一起历经了实证化的过程。面对当时各国内部驳杂混乱的实定法规范,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开始有意识地在实定法中辨识并区分继受要素和本国制定法要素,[18]并在区分相应要素之规范目的的基础上进行制定法解释。对实定法的历史解释由此具有了双重含义:就其继受要素而言,历史解释旨在查明某个条文或制度在罗马法及其不同继受阶段中的客观规范目的(例如罗马法为何不承认直接代理和利他合同而受自然法影响的法典却承认);就其制定要素而言,历史解释旨在查明本国立法者制定该条文时的主观立场(例如《普鲁士一般邦法》的立法者为何忽略规定罗马法上的遗产返还之诉hereditatis petitio)。与早期历史法学派对继受要素的偏爱态度不同,民法教义学者意识到历史解释的意义实际上植根于“立法过程成为历史”这一客观事实,亦即立法者相对于法律适用而言总是处于“历史”中,而为探求立法者目的就必须深入立法资料内部,因此历史解释便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解释工具而在法学方法论中获得重要的存在价值。[19]
尽管历史解释的兴起与法律的实证化过程密不可分,然而随着法律实证化经由19世纪至20世纪的法典化运动并在各国的法典化完成之时到达其顶峰,作为继受成果的罗马共同法正式丧失法律渊源地位,对其规范目的之查明逐渐被划归法律史或广义的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民法学者开始只关注具体制度的建构与体系化适用,这成为从历史法学派到潘德克顿学派方法论转变的决定性因素,[20]最终体现为民法教义学与私法史研究在20世纪初的彻底分离。[21]在当代发展完善的实证民法教义学中,历史解释方法逐步沦为目的解释的附庸,甚至被极端实证主义者认为在现行法的解释中毫无价值。[22]下文将从历史解释方法的适用角度出发,对其在评注中的独立地位进行简单考察。
(二)历史解释方法的评注适用与中国民法评注
在前述当代方法论叙事中,人们为采取历史解释方法进行制定法解释设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首先,就历史解释所依据的材料而言,必须存在由立法机关主持或委托编纂的、权威且翔实的立法资料。立法资料是指“立法过程中的一切记录、文件”,[23]包括法律的历次草案、会议记录、法典起草者对于法律条文的理由与动机说明,必须完整保存并能够充分反映立法者对于制定具体规范之时所持有的观点。其次,就历史解释所欲查明的立法者意图而言,解释者必须假定历史上的立法者对于具体规范的设置有着充分合理的理由,并且是在对既有法律体系做通盘考虑的基础上制定某个条文的,也就是所谓的“合理性预设”(Rationalitätsunterstellung)理论。[24]只有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历史解释才可能在评注作品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这两个条件之间也在事实上存在着相互证成的关系:翔实的立法资料往往意味着立法者的理性与审慎。
在实证主义的民法学者看来,虽然历史解释可以通过完备详实的立法资料来展现立法者的主观目的,但教义学的实务导向要求法律解释工作直面条文在当下的适用,解释者不必受制于历史上立法者的真实意思。[25]当某个条文经体系解释所得到的结论符合实践需求却与立法者的意图不符时,应当依照利益或效用的考量而舍弃历史解释所得到的结果。[26]而对存在于历史中的立法者真实意思的考察反倒因其“历史性”而成为法律史或制度史研究的对象,[27]因为历史上的立法者“也并不是自始就意识到这些内涵,它有时是嗣后由学术整理出来的”。[28]
因此可以看到,欧陆高度实证化的评注在对规范目的进行介绍时极为关注条文的体系性理解及其在既有判例中的体现,对于条文在立法时的目的或制定史则仅在与适用相关的谱系内加以关注,即便大型评注也往往不会针对具体条文的立法史进行逐一阐释,而只是在序言部分对法典编纂史进行简单的综述,[29]除非某条文在制定时存在争议、新近被修正或其适用已偏离最初的立法目的等情况需要说明,[30]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条关于姓名权的规定与一般人格权的衔接问题、[31]第313条关于交易基础丧失制度从学说到债法现代化的发展过程。[32]
然而与欧陆民法评注对历史解释方法的相对轻视相比,我国《民法典》的解释与评注作品显然不能照搬这种态度。根本原因在于,欧陆民法学有着如前所述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当代评注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摆脱历史上的立法者目的和立法资料的束缚,依托高度实证化的民法教义学和既有司法判例进行工作。反观我国民法理论和实践则受制于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有着起步较晚和研究相对薄弱的客观弱点,实证化与本土化工作仍有待加强,[33]《民法典》内条文的多元继受特征更是提高了评注工作的难度,[34]有时不得不经由历史渊源的追溯而进入比较法或法律史的研究,以查明某个条文在作为继受母国的域外立法例中的客观规范目的和演变过程。
尽管从法律渊源的整合角度来看,我国《民法典》的颁行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但我国民法学和实践的发展不应当另起炉灶,反而应当警惕《民法典》评注的撰写工作过早陷入上述实证主义导致的历史与现实的断裂局面。事实上,即便在高度实证化的德国民法学界,仍有不少学者注意到法典化所带来的实证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历史与当下之间的断裂,试图唤起条文背后的历史语境,或至少在实定法解释论中起到澄清规范之原初意义的效果,[35]这部分学者的努力体现为《德国民法典》的“历史批判评注”,[36]该评注尤其关注条文在罗马法以降的制度史过程中的演变及其在欧洲法秩序中的不同呈现形态。我国民法的评注工作诚然无需像“历史批判评注”那样集中关注历史解释,而是应当以评注为契机,通过历史解释方法对《民法典》条文自单行法时代以来的演变或继受域外立法例的过程加以系统性的逐条梳理,从而为进一步的实证化教义学工作打下基础。[37]这一工作将首先面临单行法时代数量庞大且内容驳杂的文献困境,因而下文将从历史解释的材料出发,对我国民法评注的历史解释方法展开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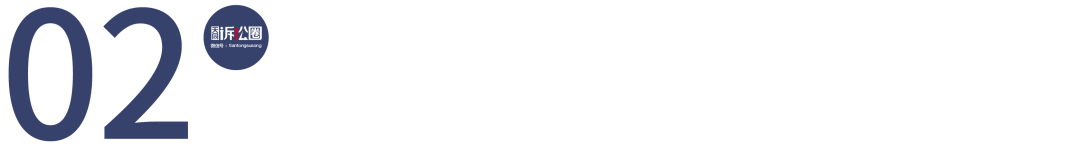
我国《民法典》历史解释所依据的材料
作为在法律渊源上具有断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将把我国民法史划分为民事单行法时代与民法典时代。从一般法律史的角度来看,民事单行法时代起步于新中国对旧“六法全书”体系的全盘否定和1950年《婚姻法》颁布,[38]但与其后的民法典时代之间并非截然割裂,而是在体系和理论发展上均具有延续性。[39]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历程贯穿于整个民事单行法时代,呈现于《民法典》中的大量规范与单行法时代的理论与实务发展经验具有共时性,因此评注的历史解释所依据的材料基本来自于民事单行法时代。[40]这部分材料可以大致类型化为三种:与历次法典草案相关的资料、民事单行法时代的法律渊源等资料、习惯法与教义学资料。
(一)《民法典》的历次草案及立法理由
在1950年新中国首部民事法律《婚姻法》以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历经数次启动与搁置,总计有1950年代、1960年代、1980年代和2002年的4次、包括各种“室内稿”、“试拟稿”、“征求意见稿”等在内的数十余稿草案。遗憾的是,对于这些草案及其制定理由,迄今并无官方主持或委托编纂的全面性、系统性汇编,而仅部分散见于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之中。尽管已有法律史学者对上述资料进行了整理出版,但这种整理工作并未受到立法机关委托,仍属于私人汇编性质,虽亦获得曾亲自参与立法过程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并“尽可能完整地收录”立法草案,但在非公开资料搜集的全面性上具有不可避免的劣势,且有可能出现错讹,[41]无法取代官方机构的权威汇编资料。虽然这种私人汇编有时被评注作品用于具体条文的历史解释,[42]但只能被视作在官方汇编资料缺位情况下,为进行学术研究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的举措,无法作为正式的立法资料而适用于裁判说理。
与前四次民法典编纂时期的立法资料欠缺相比,本次《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资料则相对充足。就公开资料而言,[43]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相关官员所主编的释义、解读以及“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44]尽管并非原始立法资料且较为简明扼要,也未收集总结立法过程中各单位和专家就具体规范的不同意见和论争过程,[45]但均可视为立法机关对于《民法典》立法目的所做出的权威说明。由参与立法工作的同志所撰写的回忆录或相关年谱类著作仅能片面的反映立法过程,虽在可靠性上不具有疑问,但仍需在综合不同资料的基础上加以使用。[46]此外,在《民法典》颁布以来亦存在若干“新旧法对照”等私人资料汇编,但这些汇编主要利用公开资料进行条文和语句上的对比,与前述私人立法资料汇编一样在准确性和全面性上可能存在疑问,对于历史解释的价值不高。[47]
(二)民事单行法时代的法律渊源和释明性资料
在历次法典草案及立法理由之外,民事单行法时代的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的实体规范对于民法典评注作品中的历史解释具有重要意义。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党中央确立法典化与制定民事单行法同时并进的方针以来,[48]在长达70余年的民事单行法时代里,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民事单行法律和其它具有法律渊源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如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由于在本次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立法机关已经对包括民法通则、物权法和合同法等在内的九部民事法律规范进行了全面的编订纂修工作,将大量单行法时代的规范吸收进《民法典》中,因此这些单行法的立法理由、立法机关释义书等立法资料也应当被归入《民法典》历史解释的资料范畴,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主编的“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和“立法资料选”等。[49]但与《民法典》具体条文的立法史考证稍有不同,评注作品中对于条文的历史解释应当以该条文在单行法时代里具有可明确辨识的承继脉络为原则,例如《民法典》第151条关于显失公平行为的规定有着从《民法通则》第59条到《合同法》第54条再到《民法总则》第151条的承继脉络,但关于显失公平的最早规定似乎来自于1951年《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解答房屋纠纷及诉讼程序等问题的批复》第4条,因此在本条评注的历史解释中仅需予以提及。[50]
除立法机关对于民事单行法的立法理由和立法背景资料汇编外,最高人民法院围绕民事单行法的实施与适用也制定了大量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它们在单行法时代已被普遍承认具有法律渊源的效力。[51]在我国的法典化过程中,这部分法律渊源被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废改留),[52]有的被《民法典》吸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被《民法典》第533条吸收;[53]有的则被《民法典》修改,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第35条关于所有权保留出卖人取回权的规定被修改后吸收进《民法典》第642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单行法时代针对法律和司法解释所撰写的“理解与适用”丛书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但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所着力推动以适用为导向的释明性资料,不仅充分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规范目的的理解,而且对于指导全国法院“正确、统一适用法律”[54]和“尽可能简洁准确全面地诠释条文的精神”[55]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单行法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进入《民法典》,[56]此类“理解与适用”也应当一并纳入历史解释的辅助材料之中,如在上例中,《民法典》第533条和第642条的评注作品亦应参考相关“理解与适用”中的内容。[57]
目前民法学界针对单行法时代司法解释效力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些司法解释中的具体规则如何向民法典时代过渡或衔接的问题,[58]然而无论单行法司法解释在民法典时代被吸收、或被废止、抑或被修改,都应作为历史解释的辅助材料而在评注中被考察。恰恰在查明单行法时代的法律渊源和其他释明性资料因何理由而没有被《民法典》吸收,又或出于何种体系性还是政策性考量而被《民法典》保留或修改的过程中,立法机关的规范目的和指导思想能够借助历史解释得到清晰的呈现。[59]
(三)习惯法与民法教义学资料
除前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整理撰写的官方或半官方资料外,我国民法评注的历史解释资料还包括民法教义学,尤其是在本土化语境下、由我国学者针对司法实务中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的教义学研究。尽管在前述当代法律解释方法理论里,立法资料的范围被限定为立法机关主持汇编的权威材料,并不包括教义学文献。但如前所述,当代解释方法论有着强烈的实证主义底色,更加适合于法律相对稳定、理论研究相对充分的社会和地区,[60]我国《民法典》制定历史的独特性使得我们必须把民事法律中的具体规范演变放到立法与民法理论发展的宏观视野下进行审视。[61]具体而言即一方面,我国理论界在民事单行法时期积累了大量了教义学讨论,这部分理论成果有的被《民法典》所明确吸收,有的被司法解释所采纳。例如《民法典》第40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56条关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规定采纳了学界关于美国《统一商法典》浮动抵押规则的理论研究,[62]通过对这部分教义学理论进行回溯,历史解释能够查明相关规范在继受母国中的体系定位和客观规范目的,避免出现未来在我国实务适用上出现体系扰动的问题。[63]
另一方面,我国民法理论与实践仍处在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使得成文法典所固有的滞后性缺陷与我国实践需求之间的矛盾可能被放大。因此在《民法典》的条文规定不绵密或对某些制度刻意留白之处,评注作品可以采取历史解释方法查明此类条文在发生学上的原因,以及该制度在教义学或习惯法上的“应然”状态,从而为规范适用提供依据。例如对于我国《民法典》第231条所规定的设立或消灭物权的“事实行为”,在评注作品的解释论中应当包括对无主物的先占,[64]这是由于《民法典》延续了《物权法》、《民法通则》和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有权篇(草稿)》的苏联式立法思路,出于价值选择等因素而拒绝了无主物概念入典。[65]因此面对实践中出现的动产抛弃后的所有权、拾荒者的所有权取得等问题,可以通过对《民法典》第231条进行扩张而解决。[66]
与民法典及民事单行法时代的立法资料与法律渊源相比,习惯法和民法教义学的资料具有内容驳杂难以把握的特点,且未必总是以具体规范的实践适用为导向。为避免历史解释陷入对具体条文进行纯粹的制定史乃至继受史的“空泛”研究,评注作品不应当涉及那些对于规范之正确理解不具有直接意义的历史过往。[67]下文将结合具体实例对我国民法典评注中对历史解释方法的适用进行简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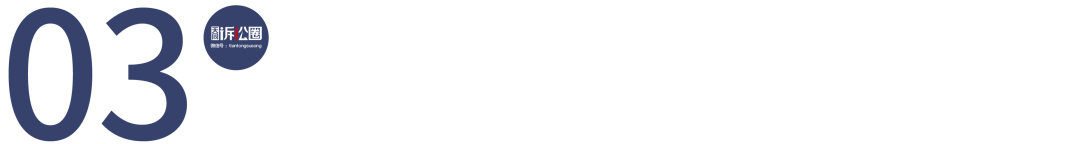
我国民法典评注中历史解释方法的适用
对于民法典评注作品而言,历史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将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一并旨在查明、澄清某个条文的意义或规范目的。[68]一方面,纯粹为揭示历史发生过程且不具有实践指涉的考证应属法律史研究的范畴,不应在评注作品中出现。然而另一方面,在前述我国《民法典》立法资料保存和公开的客观背景下,以及就我国正处于民法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我国民法典评注作品中的历史解释工作不应当延续欧陆实证化理论对于历史解释的狭义认知,亦即不应满足于查明规范的主观目的,而是以查明规范的客观目的、避免采取单一的解释方法导致规范体系外溢或扰动问题为主要目标,其适用的前提则是对条文历史渊源的准确辨识。
(一)历史渊源辨识的规则
尽管就宏观而言,我国民法典是在吸收并整合九部民事单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工作基础上制定的,但在具体条文的微观层面,民法典仍在历史渊源上具有多元性。在对此进行辨识时,应当以立法资料中明确可查的承继关系为原则,以通过立法资料之外的文献可佐证的承继关系为辅助,最后兼顾比较法上的渊源考查。
1. 立法资料中明确可查的承继关系
借助对前文所列举的民法典立法资料和民事单行法立法资料的追溯,通常可以对《民法典》中条文渊源进行整理爬梳。但评注作品在进行历史解释时仍须注意,仅在前述资料中对此类继承关系有明确提及的情况下,才可以确定该条文的历史渊源,法条字面上的相似性并不构成明确的承继关系。例如《民法典》第499条规定悬赏广告合同,本条虽在1999年《合同法》中没有出现,但明确来自于2009年《合同法解释(二)》第3条,在评注作品中可对该司法解释及其“理解与适用”进行回溯。[69]
又如《民法典》第641条第1款关于买卖合同约定所有权保留的规定在立法机关释义书中具有功能主义的担保物权性质,[70]其历史渊源则来自于《合同法》第134条,在合同编体系上属于特种买卖而易与大陆法系传统的买回买卖相对照。[71]根据《合同法》的立法资料,该条“应当说只是确立了一个原则”,[72]因此在解释论上可能出现德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路径,不同路径所分别代表的所有权构造与担保物权构造均对本条的“暧昧立场”具有解释空间,从而为本条评注作品的撰写工作带来困扰。[73]但根据历史解释,《合同法》第134条在1995年1月《合同法(试拟稿)》中并不存在,试拟稿第186条以下所规定的“买回买卖”却与《德国民法典》第456条以下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79条以下有着相当近似的构造,[74]不过试拟稿中的规定到了1997年5月《合同法(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在1998年8月的《合同法(草案)》中,又同时出现第131条所有权保留(即《合同法》第134条)和第169条买回买卖,[75]后者在1999年《合同法》的最终版本中被删除。这一历史渊源的考证似乎说明《合同法》立法者对于德式路径的否定,从而至少可以认为《民法典》第641条在历史渊源上与德国法关系不大。
2. 立法资料之外的文献可佐证的承继关系
出于前述我国立法资料保存整理和公开的客观情况,我国《民法典》中并非全部条文均在民法典或单行法立法资料中有明确可查的承继脉络。在这类法条评注作品的历史解释中,不妨尽可能根据本条文制定之时的理论发展与立法背景,在一个较宽泛的文献范围里加以查明。例如《民法典》第637条所规定的试用买卖虽然承继自《合同法》第170条,根据立法机关释义的明确说明,系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26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384条的规定。[76]尽管《德国民法典》第454条也对作为特种买卖的试用买卖合同进行规定,但其结构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的规范体系存在差异,评注作品应当根据准确的历史渊源对其区别进行梳理。[77]
又如《民法典》第590条关于合同履行时不可抗力的规定,系整合自《合同法》第117条和第118条。[78]对于本条所称合同“不能履行”在解释论上素有是否可以对标德国式“给付不能”并继受该国理论的争议。[79]根据历史解释,本条第1款第1句关于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规定,来自于《合同法》第117条第1款第1句,对于后者的制定历史,则必须从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32条第1款所规定的相似条文表述中寻找,再结合考察1980年代的三部合同法的立法资料,可以认为本条所称的“不能履行”与德国法并非同一事物,而是受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救济进路”影响。[80]
3. 兼顾比较法上的渊源考察
一般而言,评注作品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回溯至现行法典条文在单行法时代的渊源即可,当《民法典》的某些条文与比较法上的规定存在类似之处时,仅在立法机关做出明确说明的情况下才可将比较法作为历史解释所考查的对象(如前述《民法典》第637条),我国民法典与域外立法例之间在语词表述上单纯的近似关系并不能证成此种承继关系。然而考虑到我国官方立法资料中缺乏详尽记载的客观情况,对于《民法典》中的部分条文在采取上述两种方法仍不能辨识其历史渊源时,只能利用比较法文献对本条在该国法体系中的规范目的和体系意义进行查明,再将所获得的成果与《民法典》的固有规范体系进行比较适用,实现以实务为导向的制度本土化。
在当下我国民法理论发展仍处于继受阶段的总体背景中,《民法典》中属此情况的条文不在少数。例如第1127条关于配偶法定继承固定顺序的规定来自于1985年《继承法》第10条,后者则可经由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案)》第15条而追溯至前苏联民法的相关规定;[81]而关于物权编中登记对抗原则的理解应经由单行法时代尤其是《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回溯至《日本民法典》中规范目的之研究;[82]前述对第403条以下动产担保规则的理解应关注美国理论和实践;而又如第984条关于无因管理受益人对管理事务追认的规定,首次出现于《民法典合同编(草案)》(征求意见稿)第542条,属于民法典新加入的条款,在单行法和《民法典》的立法资料中均无法找到历史渊源。由于英美法中不存在独立的无因管理制度,而在大陆法系传统的无因管理之债中,对受益人追认有着德国和瑞士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式,分别适用于正当无因管理和真正无因管理内,在解释论上可能产生不同的体系影响。[83]由于本条无论在构造和语词表述上都与《瑞士债法典》第424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相接近,因此评注作品可能直接参照比较法上的学说对《民法典》第984条进行解释,但应当着重研究比较法理论与我国法体系的衔接问题。[84]
(二)历史解释的目标:查明法条的客观规范目的
通过对《民法典》具体条文历史渊源的准确辨识和回溯,通常可以锚定该条文的规范目的和适用领域。尽管在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一般性讨论中,关于查明规范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之位阶与适用层次的争论自始不休。[85]但就面向实践需求的评注作品而言,在查明法条的规范目的时无论主观目的(立法原意)和客观目的(客观意旨)均应被关注并综合考量,两者皆非“唯一或决定性标准”,历史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应当再接受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等方法的综合验证。[86]在当下我国民事立法活动仍不断发展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历史解释所追求的结论或目标为查明条文的客观规范目的,主要包括承继自单行法时代的“既有”条文,以及《民法典》中的新设条文。
首先,对于承继自单行法时代的“既有”条文而言,查明其客观规范目的有助于厘清该条文在原单行法体系中的体系定位,为其在民法典中的融入与衔接做好准备,避免某些原本居于单行法内部的规范在法典内部产生体系联动从而导致超越原单行法适用领域的“外溢”效果。例如《民法典》第157条吸收了原《民法通则》第61条和原《合同法》第58条并置于总则编,成为法律行为无效之后果的一般性规定,因而本条将产生适用于所有分则编领域的逻辑结果,进而在体系解释中发生与诸如遗嘱等非合同之法律行为无效时的适用问题。[87]又如《民法典》第491条第2款吸收《电子商务法》第49条第1款关于电子商务合同成立时间的规定,将原本限于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规范主体扩张至全部民事主体,在适用时将产生是否应当对主题进行限缩的疑问,评注作品可以依照历史解释在查明原有单行法条文的客观规范目的的基础上,讨论本条与《民法典》体系的衔接问题。[88]
对于单行法时代“既有”条文的历史解释而言,更多的困难或许出现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里,原因首先在于婚姻家庭立法具有较强的身份和伦理属性,并且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迁而容易产生对规范客观目的的差异性理解;其次是在立法技术上,婚姻家庭编立法回归民法典之后的诸多问题仍有待学界和实务界共同解决。[89]例如《民法典》第1089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共同债务时协议偿还的规定延续了2001年《婚姻法》第39条第1款、1980年《婚姻法》第32条的客观规范目的,但在立法精神上已经脱离1950年《婚姻法》第24条前半句关于男方清偿的规定(“如无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或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不足清偿时,由男方清偿。”),后者又可以追溯至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17、18条,是在根据地妇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正确规定。[90]在《民法典》第1089条的评注作品中若涉及对此前几部婚姻法条文的追溯,应当对此种社会思想背景的变迁加以简要介绍。
对于《民法典》新设条文的评注作品中,对其历史渊源进行查明有助于厘清该条文在既有民法典规范体系内的适用空间。这一方面表现在某些具有较强本土化色彩的条文之上,例如《民法典》第183条关于见义勇为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义务、第184条关于紧急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与合同编第979条以下无因管理部分的衔接问题早在《民法总则》时代便已存在大量讨论,[91]《民法典》无因管理部分的评注作品应当在查明第183条和第184条的客观规范目的之基础上,进一步对其与第979条无因管理受益人的适当补偿义务进行解释论上的讨论。[92]
新设条文的另一方面表现则是部分具有显著继受色彩的制度。受我国民法制度多元继受的现实因素影响,参考不同体系而制定的规范之间也可能发生相互扰动的问题,为此,历史解释应当以查明这部分条文在继受母国法体系中的规范目的为目标,为这类制度在我国的“实践继受”[93]创造条件。例如《民法典》第403条关于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对抗效力的规定,尽管有着从《担保法》到《物权法》的本土发展脉络,但也涉及我国民法对动产担保物权的德国模式和英美普通法模式的混合继受问题,[94]因此本条评注作品在进行历史解释时有必要对于各自模式的规范目的进行简要介绍或比较。[95]当然,此种历史解释应当时刻关注我国《民法典》的体系适用问题,否则历史解释将流于法律史甚至历史研究的宽泛范畴,丧失其教义学价值。
结论
作为欧陆传统法律解释学的重要载体乃至“法教义学的巅峰”,评注体裁在欧洲有着自罗马法以降长达数千年的传承历史,[96]甚至随着14世纪罗马法在西欧的复兴之后一度形成以评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而著称的评注法学派。[97]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欧陆评注的演变历史同时也是欧陆对罗马法从理论继受经由实践继受再到体系化、法典化建构的民法理论与方法论的发展史。
与具有悠久传统的欧陆法律评注相比,我国民法典时代的评注事业显然承担了更加艰巨的任务。我国民法的评注者要在民事单行法时代的研究基础上,依托《民法典》的体系框架对既有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以适用为导向的全面整合。就此而言,评注至少在现阶段的解释工作不应当延续当代理论对于历史解释的狭义认知,而是应当一方面不满足于查明规范的主观目的、甚至在必要时以查明规范的客观目的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打破固有学科壁垒,将规范的继受史或制度史纳入历史解释之中,避免在制定法解释与规范的继受史研究之间人为地制造出紧张关系,进而不加辨识地将我国民事实定法中部分制度的客观目的划归比较法或法律史研究的范畴。
历史解释诚然仅仅是制定法解释方法的一种,在适用位阶上居于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之后的次要位置。经由历史解释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具有必然的正确性,而是必须得到其它解释方法的验证且不能超越于条文所确定的文义。然而历史解释对于我国评注工作的价值在于经由其所查明的规范客观目的,使解释者对相关条文的制定过程或继受背景有所了解,以此进行不同法律体系间的整合。这恰恰是属于我国民法研习者的历史性任务,或许也将推动我国本土评注法学派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民法学研究的“中国风格”(mos Sinicus)。
注释:
[1] 参见张双根、朱芒、朱庆育、黄卉:《对话:中国法律评注的现状与未来》,《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2期;贺剑:《法教义学的巅峰:德国法律评注文化及其中国前景考察》,《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
[2] 关于1980年以来我国民法注释文献的概览与整体分析,参见韩世远:《法律评注在中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3] 据笔者统计,至2022年1月我国市面上可见的民法典评注丛书系列包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相关学者主编的《民法典评注》(共15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杨立新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与案例评注》(共7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王利明教授总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评注》(共12册,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由朱庆育教授和高圣平教授总编的《中国民法典评注》丛书也以“条文选注”的形式陆续出版(至2022年1月已出版2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4] 参见朱庆育:“法律评注是什么?(代序)”,载朱庆育、高圣平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条文选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5] 参见朱庆育:《<中国民法典评注>写作指南(第2版)》,载朱庆育、高圣平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条文选注》,附录二,第6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6]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13页。[7] 参见刘志阳:《<民法典>立法资料的法治意义与实践方式》,《法治研究》2021年第1期。[8] 参见姚明斌:《论中国民法评注之本土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9] 关于日本的情况参见程坦:《日本民法评注的方法论演变与结构内容》,《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0年第2期;拉丁美洲的总体情况参见Jakob Fortunat Stagl, Juristische Kommentare in Lateinamerika, in: Juristische Kommentare, Tübingen 2020, S. 123 ff.[10] 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页。[11] 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页。[12] 关于历史解释的历史,参见Jan Schröder, Zur Geschichte der historischen Gesetzesauslegung, in: Festschrift-Hattenhauer, Heidelberg 2003, S. 481 ff.[13] 参见雷磊:《什么是法教义学?》,《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4期,第102页。[14] Christian Friedrich Glück, Ausführliche Erläuterung der Pandecten nach Hellfeld, Th. 1, 2. Aufl., Erlangen 1797, S. 45.[15] Vgl. Andreas Daniel, Gemeines Recht, Berlin 2003, S. 61.[16] 参见薛军:《“民法-宪法”关系的演变与民法的转型》,《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17] 参见[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1页。[18] 参见舒国滢:《19世纪德国“学说汇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外法学》2016年第1期。[19] 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15页。[20] Vgl. Hans-Peter Haferkamp, Die Historische Rechtsschule, Fankfurt am Main 2018, S. 218.[21] Vgl. Eduard Picker, Rechtsdogmatik und Rechtsgeschichte, in: AcP 201 (2001), S. 767.[22] Vgl. Jan Thiessen, Die Wertlosigkeit der Gesetzesmaterialien für die Rechtsfindung, in: Holger Fleischer (Hrsg.), Mysterium „Gesetzesmaterialien“, Tübingen 2013, S. 50.[23]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2020年自刊第7版,第616页。[24] Vgl. Jan Schröder, Recht als Wissenschaft, Bd. 1, 2. Aufl., 2020, S. 371.[25] 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1页。[26] Vgl. Philipp Heck, Gesetzesauslegung und Interessenjurisprudenz, in: AcP 112 (1914), S. 111.[27] Vgl. Heinz Holzhauer, Erfahrungen mit dem „praktischen Nutzen“ der Rechtsgeschichte und Überlegungen zum Sinn rechtsgeschichtlichen Unterrichts, in: Festschrift-Hattenhauer, Heidelberg 2003, S. 215.[28] [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424页。[29] Vgl. Gottlieb Planck,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nebst Einführungsgesetz, 3. Aufl., Berlin 1903, Bd. I, S. 1 ff.; [德]弗朗茨·赛克尔:《<慕尼黑民法典评注>(第五版)编辑指南》,黄卉译,《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2期。[30] Staudinger/Honsell, Einleitung BGB, 2018, Rn. 161.[31] Vgl. Erman/Klass, Anhang § 12, Rn. 8 ff.[32] Vgl. MüKo/Finkenauer, § 313, Rn. 20 ff.[33] 参见汤文平:《论中国民法的法学实证主义道路》,《法学家》2020年第1期。[34] 参见姚明斌:《论中国民法评注之本土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35] 参见[德]索尼娅·梅耶:《历史批判性评注》,余翛然译,载宋晓主编:《中德法学论坛》第17辑(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页。[36] 参见卜元石:《德国法律评注文化的特点与成因》,《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37] 参见田士永:《私法的历史比较研究:评〈《德国民法典》历史批评注释书〉》,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7页。[38] 参见何勤华:《论新中国法和法学的起步》,《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39] 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编纂与中国民法学体系的发展》,《法学家》2019年第3期。[40] 对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央苏区或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如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贷暂行条例》,其时代背景和立法宗旨与现行《民法典》有着较大差异,因此一般不做为历史解释所依据的辅助材料,除非对于反映现行制定法条文中规范目的的变迁有所助益。参见张希坡编著:《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41] 参见何勤华、李秀清、陈颐:“增订版序”,载何勤华、李秀清、陈颐编:《新中国民法典草案总览》(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42] 参见姚明斌:《<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违约损害的赔偿范围)评注》,《法学家》2020年第3期。[43] 立法资料之“公开性”的重要作用已经被我国学者所强调,参见薛军:《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组织体制问题》,《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第43页。[44]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石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 年版;《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典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45] 参见刘志阳:《<民法典>立法资料的法治意义与实践方式》,《法治研究》2021年第1期,第154页。[46] 这部分文献如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参见朱庆育:《第三种体例:从<民法通则>到<民法典>总则编》,《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47] 这部分文献如李昊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与既有民事法律对照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石冠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立法演进与新旧法对照》,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48] 参见彭真:《在民法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5月27日),载《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49]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主编:《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主编:《侵权责任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编写组编:《民法总则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50] 参见朱庆育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条文选注(第1册)》,第151条(显失公平行为),贺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边码5。[5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2021修正)》(法发〔2021〕20号)第5条;雷磊:《重构“法的渊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64页。[5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为确保民法典实施进行司法解释全面清理的工作情况报告》(202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26次会议通过)。[53] 参见黄忠:《论民法典后司法解释之命运》,《中国法学》2020年第6期,第52页。[54] 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前言”部分,第3页。[5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人民法院出版社2019年版,“后记”部分,第660页。[56] 参见周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确保民法典正确贯彻实施》,《求是》2020年第12期。[57] 参见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29页。[58] 参见王雷:《民法典适用衔接问题研究》,《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94页以下。[59] 参见薛军:《民法典编纂如何对待司法解释》,《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4期,第51页。[60] 参见张双根、朱芒、朱庆育、黄卉:《对话:中国法律评注的现状与未来》,《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2期。[61] 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编纂与中国民法学体系的发展》,《法学家》2019年第3期,第71页。[62] 参见高圣平:《民法典动产担保登记对抗规则的解释论》,《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952页;龙俊:《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32页。[63] 参见纪海龙、张玉涛:《<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中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云南社会科学》2019年5期。[64] 参见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一)》,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99页。[65] 参见朱岩、高圣平、陈鑫:《中国物权法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9页。[66] 参见金可可:《论“狗头金”、野生植物及陨石之所有权归属》,《东方法学》2015年第4期;张力:《先占取得的正当性缺陷及其法律规制》,《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67] 参见朱庆育:《<中国民法典评注>写作指南(第2版)》,载朱庆育、高圣平总编:《中国民法典评注·条文选注》,附录二,第6.3.2项,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68] 参见[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以下。[69] 参见姚明斌:《<民法典>第499条(悬赏广告)评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值得注意的是,悬赏广告曾在《合同法(试拟稿)》第13条有规定,但因立法机关意见不一和问题研究不足等原因而在随后的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70]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05页。[71]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2页。[72] 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73] 参见王立栋:《<民法典>第641条(所有权保留买卖)评注》,《法学家》2021年第3期。[74]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75]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重要草稿介绍》,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6页。[76]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396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603页。[77] 参见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一)》,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12页;Vgl. HKK/Thiessen, §§ 454-473, Rn. 98.[78]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59页。[79]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28页。[80] 这方面的研究参见柯伟才:《我国合同法上的“不能履行”》,《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81] 参见杨立新:《编纂民法典必须肃清前苏联民法的影响》,《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82] 参见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83] 参见吴训祥:《<民法典>中准合同制度的历史演变与体系效应》,《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1期。[84] 参见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四)》,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610页。[85] 最近的法理学研究参见焦宝乾:《历史解释与目的解释的区分难题及其破解》,《法商研究》2021年第5期。[86] 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2页。[87] 参见叶名怡:《<民法典>第157条(法律行为无效之法律后果)评注》,《法学家》2022年第1期。[88] 参见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通则(一)》,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11页。[89] 参见贺剑:《论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基本思路》,《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夏江皓:《家庭法介入家庭关系的界限及其对婚姻家庭编实施的启示》,《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90]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17条:“男女各得田地、财产债务各自处理。在结婚满一年,男女共同经管所增加的财产,男女平分,如有小孩则按人口平分。”、第18条:“男女同居所负的公共债务,归男子负责清偿。”中央负责同志该规定的说明为:“…三、离婚后的债务问题。现在女子虽取得了经济上的地位,但男子经济地位还优于女子,最主要的还是使女子不受经济上的束缚,而得真实的解放,所以应归男子担负。至于男子“担负过重”,正因此限制男子不要轻易乱结婚离婚。因为结婚是男女双方问题,不是女子一方面。”项英:《关于婚姻条例的质疑与解答》,载张希坡编著:《革命根据地法律文献选辑》(第二辑·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51页。[91] 参见冯德淦:《见义勇为中救助人损害救济解释论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92] 参见朱广新、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四)》,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82页。[93] 参见[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上),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5-112页。[94] 参见庄加园:《动产抵押的登记对抗原理》,《法学研究》2018年第5期。[95] 参见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四)》,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41页。[96] 评注的拉丁文名称(commentarius, commentari)可追溯至罗马法学家对于十二表法和裁判官告示的解释。Vgl. Okko Behrends, Der Kommentar in der römischen Rechtsliteratur, in: Institut und Prinzip, Bd. 1, Göttingen 2004, S. 314. 关于作为整体法域的欧洲评注历史可参见David Kästle-Lamparter, Welt der Kommentare, Tübingen 2016, S. 20 ff.[97] 参见舒国滢:《评注法学派的兴盛与危机》,《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